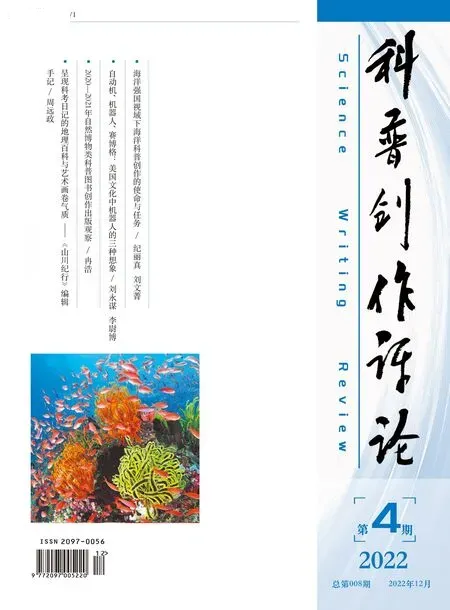別利亞耶夫科幻小說中的科技倫理之思
楊 朵 武曉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191)
亞·羅·別利亞耶夫(А.Р.Беляев,1884—1942)是蘇聯時期科幻小說的奠基人之一,有“蘇聯科幻之父”和“俄羅斯的儒勒·凡爾納”之稱。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科幻小說,著名的科幻小說如《陶威爾教授的頭顱》(Голова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оуэля)、《沉船島》(Остров погибших кораблей)、《水陸兩棲人》(Человекамфибия)、《世界主宰》(Властелин мира)、《躍入蒼穹》(Прыжок в ничто)、《太空飛船》(Воздушный корабль)、《康愛齊星》(Звезда КЭЦ)和《會飛的人》(Ариэль)等。他的作品在國內外多次再版,并受到了讀者們的廣泛歡迎。據保守統計,早在1956 年到1959 年,他的作品在蘇聯的總出版量已超過400 萬冊[1]。
別利亞耶夫的科幻小說中充滿了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如果說阿·尼·托爾斯泰(А.Н.Толстой)感興趣的是科幻小說揭示社會問題的可能性,而弗·阿·奧勃魯喬夫(В.А.Обручев)則首先將科幻小說視為科學宣傳的手段,那么得益于亞·羅·別利亞耶夫,一種科幻問題和社會問題緊密結合、相互補充的新型蘇聯科幻小說,開始在我們的文學中傳播”[2]。蘇聯著名學者謝·阿·伊萬諾夫(С.А.Иванов)也曾指出,蘇聯科幻文學與西方科幻文學有著根本不同,即前者對國家國情和具體現實的關注要遠多于后者。正是蘇聯科幻小說對社會主題的關注,才賦予了這一文學題材以真實性和強大的藝術力量[3]。別利亞耶夫尤其對科技倫理問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主要體現在作家對“科學狂人”倫理失序的批判,對“他者”身份問題和倫理困境的預測,以及對人道主義精神在科學選擇中導向作用的肯定三個方面。
一、“科學狂人”帶來的個人悲劇與社會悲劇
1818 年,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創作了長篇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又譯《科學怪人》),這本書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率先塑造了“科學狂人”的形象——弗蘭肯斯坦。弗蘭肯斯坦“表征著以生命的創造者自居而濫用生命科學技術的‘科學狂人’,這種濫用帶來了嚴重的科學倫理和生命倫理問題,給人類生存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4]。科幻小說自此始終把對科技倫理與生命倫理問題的探討和擔憂作為自己的重要主題。同樣地,別利亞耶夫也從個人悲劇和社會悲劇兩個方面對“科學狂人”進行了批判。
首先,別利亞耶夫筆下的“科學狂人”一味追求科學理性的巨大創造力量,忽略了創造物的基本生命倫理問題,從而引發了造物者與創造物個人層面的悲劇。
在《陶威爾教授的頭顱》中,作家“更下功夫的仍然是展示強烈個人主義所產生的科研道德墮落,展示在經濟利益決定一切的社會狀態下導師和助手關系的緊張,展示不良社會中反人性罪行的血淋淋的事實”[5]。小說講述了克爾恩教授為謀取私利名譽,私自復活陶威爾教授、工人托馬和酒吧歌女勃麗克的頭顱,進行人體復活實驗的故事。一方面,克爾恩恩將仇報,盜取了自己的導師陶威爾教授的思想成果,走上了科研道德墮落的道路,最終被名利燒紅了眼的克爾恩落得羞愧自盡的下場,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了代價。另一方面,克爾恩漠視生命倫理,私自非法購買尸體進行實驗,他的實驗對象也因自身怪異的生命形態而陷入無盡的肉體折磨和精神痛苦中,在絕望中經歷了二次死亡。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小說《世界主宰》中。德國科學家施蒂涅爾發明了一臺可以操縱、奴役他人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思想發射機”,借此盜取銀行家的財富和隨意操控他人的感情,并妄圖稱霸世界。故事同樣以“科學狂人”施蒂涅爾的失敗告終,他最終淪落為一個改名換姓、失去自我身份的“流浪者”,慘淡收場。而小說中被施蒂涅爾的思想射線控制的人們也失去了自我意識,成為被操控的工具,度過了不受自我意識主導的錯位人生。
其次,從社會層面上來講,脫離倫理道德束縛的“科學狂人”從事科學研究,濫用科技成果,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世界主宰》中“科學狂人”施蒂涅爾的科學陰謀不但造成了多人的情感和生活悲劇,而且給社會帶來了大范圍的動蕩不安。此外,《永生糧》中引起巨大精神恐慌的糧食洪流也對人類的科學理性和倫理道德提出了考驗。科學家布羅依爾教授發明了一種可以無限生長的食物,用以解決全人類的糧食危機。但由于小鎮居民人性貪婪、瘋狂追求金錢利益,造成了“永生糧”的泛濫,最終嚴重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原本平靜的海邊小鎮也開始變得混亂,賭博、殺人事件頻頻發生,強烈的末世氛圍由此在原本平靜的海邊小鎮蔓延開來。永生糧的出現給人們帶來了人性與精神的考驗,濫用科技發明最終給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總之,科技倫理是“科技創新活動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思想與行為準則,它規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體應恪守的價值觀念、社會責任和行為規范”[5]。從科技工作者的角度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初衷應該是服務和造福人類,但如果科學技術受到名利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甚至主導,便極易偏離正確的發展軌道、違背自然法規和客觀規律,會給個人、社會和全人類帶來不利后果和災難。此外,為減少和避免實驗對象的悲劇,必須完善相應的倫理道德規范。當下興起的克隆技術、基因工程、生命工程等科學活動,以及以人體為實驗對象的各類醫學臨床試驗等,都涉及生命倫理問題和人體倫理道德規范問題。可以說,別利亞耶夫早已通過科幻小說多次引導我們對相關的科技倫理問題進行預見和思考。
二、人類與他者的主仆地位與倫理困境
自科幻小說誕生之日起,“他者”形象便深入人心,隨后“人造人”“合成人”“異形”等形象反復出現在諸如《莫羅博士的島》等各類科幻作品中。現今的生物技術、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克隆人、機器人這些潛在的可能成為異于人類生命形式的異類生命體在科幻小說中早已是典型的幻想題材了[6]。別利亞耶夫同樣以豐富的想象力和超前的預見力,塑造了諸如“飛人”“人魚”“換臉的人”“會說話的頭顱”“復活的尸體”等一系列他者形象,預見并思考了他者可能引發的倫理道德問題:1.他者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導致其自身陷入倫理困境;2.他者極大地沖擊著人類傳統道德規范和倫理體系,從而引發人類對自我地位以及他者生命形式的再認識。
一方面,作為人類科學實驗產物的他者自誕生以來就具有極強的目的性和工具性,在人類中心主義難以逾越的大環境下,他者始終難逃被工具化的結局。
別利亞耶夫筆下的“海怪”作為科學實驗的產物,從誕生之日起就被人類不自覺地工具化。以朱利達為首的采珠人,為了將“海怪”伊赫江德爾收為己用,多次設陷阱捕捉他。在他們看來,人類與人魚始終處于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主奴關系。而當人類試圖利用海怪的能力獲取利益、將“他者”工具化而不得時,便開始借助宗教和世俗法庭的力量對海怪進行囚禁和審判。在世俗法庭的審判和宗教勢力的審判下,“人魚”由于自身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沒能在人類社會找到自身的身份定位,最后只能消失在大海深處,成為人類傳統倫理道德的驅逐物。
同時,作家借陶威爾教授之口對人類和他者的身份及關系提出了更為深沉的發問和思考。
口碑雖然說是讀者使用服務以后的體驗而自發產生,但是圖書館可以通過尋找一些有價值的口碑點去擴大、培育和傳播口碑。比如,高校閱讀推廣活動可以幫助大學生通過閱讀解決生活、情感以及對自己未來定位的困惑和價值觀問題,讓讀者感到“讀”有所獲,這種符合大學生需求的口碑可以通過讀者交流活動、媒體平臺、新聞稿等方式來擴大,以加快其傳播。
陶威爾教授的頭顱在被復活之后也對自己的存在表示不滿和氣憤,他毫不掩飾地表達:
失去了身體,我就失去了整個世界,這些物質的東西可以拿起來,可以觸摸,同時還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自己本身的存在。啊,光為了能在手里掂一掂一塊普通的小鵝卵石的分量,我心甘意樂付出我這畸形的生命![7]11
于陶威爾教授而言,頭顱的復活并不是真的復活,通過醫學手段再次復活后的“死人”并未獲得像正常人一樣的生活權利和社會身份。頭顱移植也沒能讓托馬和勃麗克獲得常人一樣的生活權利。托馬的頭顱在對正常人生活的強烈渴望和對農村生活的懷念中漸漸枯竭、死去。獲得新身體的勃麗克在出逃后開始用謊言來掩飾自己的新身份,尋求社會身份認同,以求回歸正常生活,但最終也以失敗告終——先是其謊言被拆穿,接著身體開始腐爛,最后在煎熬中死去。作為科學實驗的產物,無論是處于頭顱形態的陶威爾教授和托馬,還是之后成功復活的勃麗克,都只是克爾恩的實驗品,他們的出現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強的目的性和工具性。與此同時,別利亞耶夫用他們的死亡結束了對器官移植實驗中倫理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從中不難看出作家對這一實驗的期待性預測和警示性憂慮,科學倫理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才是杜絕這一實驗悲劇的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他者的出現極大地沖擊了人類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人類作為新的造物主開始真正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正是人類親手創造的他者消解了人類自身的主體地位,對人類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倫理觀念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已有的倫理環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家庭倫理關系、社會倫理關系等對于新出現的他者而言已經不再適用。在舊的倫理環境下,他者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行為往往以失敗告終。
別利亞耶夫在《水陸兩棲人》中塑造了“人魚”形象。薩列瓦托醫生通過醫學實驗創造了“人魚”伊赫江德爾,但后者在尋求愛情倫理、家庭身份、社會認同的過程中不斷碰壁,最終只能獨自遠去。伊赫江德爾作為小說中的他者,雖然獲得了在海洋中生存的能力,但卻失去了在世俗社會生存的權利。“人魚”成了采珠人口中的“海怪”,被朱利達等人追捕。面對自己喜歡的女孩古蒂艾萊時,伊赫江德爾也由于自己異于常人的外表而不敢與她相認。隨后主人公伊赫江德爾便遭受法庭的拘捕,成為世人眼中的怪胎。至此,伊赫江德爾成了人類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犧牲品和不被接納的他者,他在人類社會中的身份尋找以失敗而終。
《會飛的人》同樣講述了一個醫學技術賦予人類以動物能力的故事。主人公阿里埃爾在一場實驗中獲得了鳥類的飛行能力。他的外表與常人無異,但他的超能力卻引起了宗教界的恐慌和人類世界的追捕,甚至親人的排斥。在受到科學實驗的干預后,阿里埃爾原本的社會身份開始解體,成了異于常人的“他者”:他是尼茲馬特老爹眼中毗濕奴的化身,是洛麗塔和沙拉特眼中無所不能的神,是皮爾斯和布朗勞等人眼中的展覽品和營利工具,是仆人莫希塔用來討好主人的稀奇怪物,是“無人保護的飛人”“命運的玩具”和“惡人獵取的對象”。主人公通過醫學手段獲得了飛行能力,打破了人與鳥的能力界限,但同時這一能力也將主人公與人類區分開來,在他與常人之間立起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高墻,成為一個游離于正常人群之外的“他者”。最終,在世俗社會的驅逐下,阿里埃爾乘坐輪船消失在人類世界之外。由此可見,在傳統世俗倫理道德的壓制下,他者很難走出倫理困境。尤其是隨著克隆人、器官移植、AI 技術等的出現,也迫使人類開始審視已有的倫理道德體系。
綜上,人體改造對人類傳統的倫理規范提出了挑戰,這種“他者”的生理屬性暗示著傳統意義上的“人”的解體。隨著一系列“他者”形象的出現,人類的主體地位面臨著來自科學技術的挑戰,他者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也導致了自身嚴重的身份危機和社會認同。因此,在新的科學階段,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已有的倫理體系和道德規范。
三、人道主義引導正確的科學選擇
早在科技發展的初期,別利亞耶夫便已意識到科學選擇的重要意義。他的許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必須符合人類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則就是災難[9]。在別利亞耶夫看來,科學家身上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保證科研方向正確性的重要因素,正確的科學選擇需要以人類的整體利益為導向。在他的作品中,科學家們應當堅持人道主義的精神,以全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做出正確的科學選擇。
例如,陶威爾教授有著崇高的科學理想和人道主義精神,于他而言,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永遠排在第一位。身殘但“坦率、要求嚴格、富于自信”的陶威爾教授仍用自己的頭顱繼續思考,為科技進步做出貢獻。在明知被克爾恩利用的情況下,陶威爾教授堅持以科技工作先行,他堅定地表明:歸根結底,作者的名字有什么意義呢?重要的是讓我的思想傳布到全世界,在那兒開花結果[7]10-11。他代表了無私奉獻、全身心投入科學的科研人員,他們時刻恪守著自己的職業道德,以造福人類和維護正義為己任,以全人類的健康和幸福為出發點,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動中要有做人的良心,要對自己的科技研究活動有支配能力,確保自己的科技研究成果不會給人類帶來災難”[10]。科學家作為科研活動的主體,必須遵守職業道德規范和承擔社會責任,對自己的科研活動負責,擁有科學良心,承擔公民義務。別利亞耶夫塑造了許多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科學家形象,他們對崇高科學理想的追求和對全人類事業的貢獻為科學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此外,作家還不吝筆墨地塑造了其他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崇尚人道主義精神的科學家形象。例如,《永生糧》中兢兢業業為人類做貢獻的布羅依爾教授,他一輩子都在研究和發明永生糧,以使全人類免于饑餓。當他發明的“面團”被資本家利用,最終泛濫成災時,他并未作壁上觀,而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為幫助人類克服當前的災難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從全人類的立場出發,發明面團和消滅面團都是出于造福全人類的崇高科學理想。布羅依爾教授在這一充滿人道精神的科學活動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成了“末世”情緒下人類的救世主。作家在這一人物形象身上傾注了自己對科學家高尚品德和崇高理想的希望和寄托。再如,《神奇的眼睛》中基里洛夫秉持踏實嚴謹的科研精神推進了人類對海底世界的探索腳步。《水陸兩棲人》中印第安人把科學家薩列瓦托稱為天神、救星,他拯救弱小病殘,幫助病人恢復健康、重獲新生等。總之,這些具有崇高人道主義精神的科學家們承載了別利亞耶夫對人類科學發展的美好期望和預想,他們在人道主義的指引下做出了正確的科學選擇。
由此可見,科學選擇作為解決人和科學間問題的關鍵步驟,需要以人道主義為指引和規范,其中科學家們作為科研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在科學選擇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需要對科研人員進行嚴格的道德規范和倫理考量。“科技人員在科研活動中涉及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時,要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并把能否為人類造福作為評價自己科技事件善惡、正邪的最高道德標準”[11]。一個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不但要有遠大的科學理想,還要助力于人類科學事業的發展,以人為本,尊重與關心人類自身,只有以全人類利益為根本開展科學事業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和有益于時代進步的。
四、結語
別利亞耶夫將科技倫理問題擺到讀者眼前,講述了“科學狂人”倫理道德失序造成的個人悲劇和社會災難,從而引發人們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思考和重視。與此同時,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機器人、克隆人等超越傳統生理意義上的“人”的出現導致人類主體地位受到來自“他者”的挑戰。因而必須在倫理層面重新審視和匡正技術發展的大方向,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對人類和他者進行界定,以謀求長遠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得不進行科學選擇的時代里,人道主義精神的指引成為科學選擇的重要導向。總之,當下人類正處于科學選擇的關鍵路口,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科技倫理在人類未來發展中的地位。就這一問題的探討而言,別利亞耶夫的科幻小說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義和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