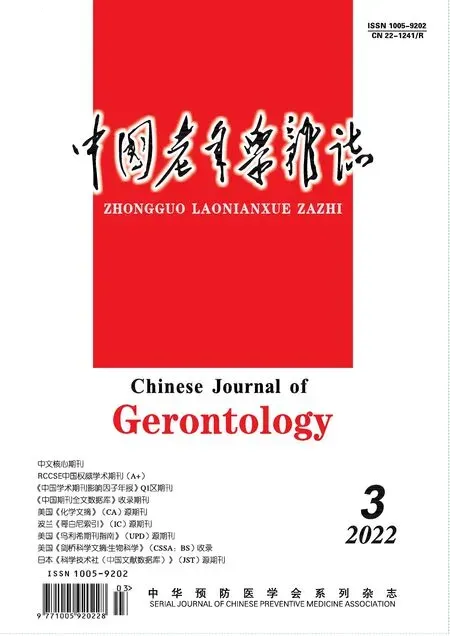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血清脂聯素與骨密度及骨轉換生化指標的相關性
楊帆 陳銘 張強 范海泉
(成都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核工業四一六醫院脊柱骨科,四川 成都 610051)
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主要發生于老年患者,由于年齡增長,體內有機物及無機物的成分發生變化導致鈣離子嚴重流失,骨密度(BMD)降低,骨代謝生化指標發生改變,導致骨質疏松形成,極易發生骨折等突發事件,且骨折后愈合緩慢,對老年人生活造成嚴重影響〔1,2〕。常用的骨轉換生化指標分為2類,其中代表骨形成標志物有Ⅰ型前膠原N-端前肽(PⅠNP)、骨鈣素(OC)、骨性堿性磷酸酶(BAP)和骨鈣素N端分子片段(N-MID),而骨吸收標志物包括Ⅰ型膠原β降解產物(β-CTX),反映了整個骨框架代謝活動,骨轉換標志物水平尤其是骨吸收標志物,在一定程度上可預測骨折風險〔3~5〕。脂聯素(APN)為脂肪細胞分泌的脂肪因子,與肥胖呈反比,有抗炎、抗動脈粥樣硬化及胰島素增敏作用,被認為與年輕成人出生隊列的BMD有關〔6〕。本文主要分析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血清APN與BMD及骨轉換生化指標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3月至2021年4月成都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收治的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134例(觀察組)。納入標準:①經X線顯示椎體內裂隙或邊緣硬化,動力椎體內裂隙磁共振成像(MRI)T1加權成像呈低信號,T2加權成像及脂肪抑制序列呈高信號,且和周圍信號界線明顯,結合CT確診為胸腰椎骨折〔7〕,記錄骨折時間,并在48 h內入院,術前評估可耐受手術;②未出現脊髓或神經受損,依從性良好;③均對本研究內容知情且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獲得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排除標準:①曾接受過影響骨代謝的藥物治療,如活性維生素D或類固醇激素等;②合并畸形性骨炎、成骨不全、骨軟化癥等骨礦疾病或由車禍、高處跌落等嚴重外傷所致的胸腰椎壓縮性骨折;③合并庫欣綜合征、甲狀旁腺功能減退癥或亢進癥等內分泌疾病者;④合并消化系統疾病、免疫系統疾病、惡性腫瘤、糖尿病或精神性疾患者。另選擇100例老年骨質疏松無骨折患者為對照組,均診斷為骨質疏松,未接受骨質疏松治療,X線、CT、MRI證實無骨折。
1.2臨床資料收集 收集所有入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身高、體重指數(BMI)、骨質疏松病程、骨質疏松分級、血鈣、血磷、甲狀旁腺激素(PTH)和促甲狀腺激素(TSH)等。
1.3血清APN測定 抽血前隔夜空腹8 h,在第2天清晨抽取空腹靜脈血6 ml,血液凝固后3 000 r/min離心10 min分離血清,將分離得到的血清分為若干份并置于-70℃保存備用。取一份血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8〕測定APN,試劑盒購自九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儀器為貝克曼AU27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嚴格依據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
1.4BMD檢測 采用美國GE公司雙能X線骨密度儀以雙能X線骨吸收測定法(DXA)測定股骨頸、全髖及腰椎L1~4部位的BMD。
1.5骨轉換生化指標測定 取1.2中分離的余下血清。經羅氏Cobas 8000型酶標儀測定β-CTX、PⅠNP、OC、BAP和25-羥基維生素D3〔25-(OH)D3〕水平,其中β-CTX、PⅠNP、OC、25-(OH)D3測定采用鄰甲酚酞絡合酮法〔9〕,BAP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16〕,試劑盒均購自美國羅氏公司,測定時嚴格依據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
1.6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3.0軟件進行t檢驗、χ2檢驗、Pearson相關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 結 果
2.1兩組血清APN、BMD和骨轉換生化指標比較 觀察組β-CTX、PⅠNP和BAP水平高于對照組,血清APN、股骨頸BMD、全髖BMD、腰椎BMD、OC和25(OH)D3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P<0.001)。見表1。

表1 兩組血清APN、BMD、骨轉換生化指標比較
2.2血清APN與BMD、骨轉換生化指標的相關性 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血清APN與全髖BMD、腰椎BMD、OC及25(OH)D3呈正相關(r=0.426、0.478、0.457、0.412,P=0.008、0.004、0.005、0.010),APN與β-CTX、PⅠNP及BAP呈負相關(r=-0.542、-0.389、-0.366;P<0.001、0.012、0.015)。
2.3影響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單因素分析 觀察組年齡、骨質疏松病程、骨質疏松分級和PTH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TSH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兩組其他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影響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單因素分析
2.4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多因素分析 以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為自變量(骨折=1,無骨折=0),將上述有統計學意義的因變量進行賦值,其中骨質疏松分級:1級=0,Ⅱ級=1,Ⅲ級=2,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血清APN、全髖BMD、腰椎BMD、OC及25(OH)D3為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保護因素,而β-CTX、PⅠNP和BAP為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多因素分析
3 討 論
近年來骨質疏松所導致的病理性骨折不斷增多,尤其是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等椎體壓縮性骨折,有較高致殘率與病死率〔8〕。正常人群的不同年齡階段或患有代謝性骨病時,骨轉換標志物在血液循環或尿液中會出現不同水平變化,可用于反映全身骨骼的動態變化,骨代謝相關指標β-CTX、PⅠNP、BAP和OC等可更敏感地反映絕經后2型糖尿病(T2DM)患者骨代謝情況〔9,10〕。內臟脂肪增多比皮下脂肪多更易加劇心腦血管疾病風險,而APN屬于脂肪細胞分泌的內源性生物活性多肽或蛋白質〔11〕,有研究〔12〕發現,APN降低參與骨質疏松,對于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調節APN水平可改善骨質疏松骨折風險,但目前關于APN與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關系研究較少。
細胞因子可通過自分泌和旁分泌形式作用于骨組織中成骨細胞、破骨細胞和髓腔未分化間充質細胞,以調節骨形成與骨吸收,APN為新近發現的由脂肪細胞特異性分泌的細胞因子,APN受體(AdipoRs)廣泛存在于全身多種組織,其中AdipoR1分布廣泛,在骨骼肌中含量最多,而AdipoR2則以肝臟中分布為主。王景等〔13〕發現,絕經后老年骨質疏松患者(實驗組)各部位BMD與絕經后健康老年婦女(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實驗組APN和BAP高于對照組,25(OH)D3低于對照組,本研究與上述研究不一致,可能與疾病類型、地域、遺傳因素、年齡和個體差異等因素有關,APN可直接作用于骨,誘導人成骨細胞增殖分化和直接刺激細胞核因子κB受體活化因子配體(RANKL)而抑制骨保護素(OPG)生成〔14〕,其具體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骨質疏松的診斷以BMD為基礎,但由于其無法反映短期內骨改變的局限性,完全依賴BMD預測骨折絕對風險會有失偏頗,相比于BMD,骨轉換標志物可較敏感地反映短期內患者體內骨代謝情況,因骨組織一直處于不斷新陳代謝中,經監測骨形成與骨吸收的動態平衡是否發生變化而提高預測骨折的敏感度與特異度。其中β-CTX為Ⅰ型膠原降解的特異性產物,在破骨細胞活性增強情況下,會明顯促進Ⅰ膠原降解,β-CTX增高;PⅠNP是骨形成的特異性標志物,由成骨細胞合成分泌,在造骨細胞功能減弱時,PⅠNP水平就下降,因此PⅠNP能較特異、敏感地反映骨形成〔15〕。OC是由成骨細胞產生和分泌的γ-羧谷氨酸包含蛋白類激素,可反映新形成的成骨細胞活動狀態,維持骨正常礦化速度,是較敏感的骨形成指標;BAP為重要的標志性酶類,標志著細胞向成骨細胞分化過程,為成骨活性重要指標〔16〕;維生素D為固醇類衍生物,其主要功能為調節體內鈣磷代謝,維持血漿鈣磷水平,對促進牙齒、骨骼發育及維持正常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且可減少骨質疏松骨折發生風險〔17〕。本研究結果表明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骨轉換生化指標發生改變,對其進行監測有重要意義。
APN被認為可通過刺激RANKL及抑制OPG產生誘導破骨細胞形成,此外其APN也被證明可誘導成骨細胞增殖與分化,并經破骨細胞生成抑制和成骨細胞生成激活而增加骨量〔18,19〕。本次相關分析結果與王文怡等〔20〕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因此血清APN可能在老年骨質疏松性骨折發病中發揮重要作用,血清APN與骨轉換生化指標密切相關。APN為由脂肪細胞分泌的內源性生物活性多肽或蛋白質,其受體存在兩種異構體,即AdipoR1和AdipoR2,AdipoR1主要在骨骼肌表達,APN可作用于骨組織AdipoR1,繼而對骨代謝進行調節,研究〔21〕表明成骨細胞中受體均有表達,APN通過AdipoR1/p38MAPK-STAT5路徑誘導人類成骨細胞RANKL,抑制護骨素的表達,以誘導破骨細胞分化;另一方面APN可增加MC3T 3-E1成骨細胞堿性磷酸酶mRNA表達水平和骨基質礦化。
姚穎等〔22〕發現,BAP、PINP和25(OH)D3與絕經后骨質疏松性腰椎骨折發生關聯密切,其中BALP和PINP為危險因素,25(OH)D3為保護因素。屈曉龍等〔23〕發現,高β-CTX的骨質疏松老年女性更易發生骨折,β-CTX較BMD預測骨質疏松性骨折的能力更強,可適時對高危人群進行相關干預管理。本研究結果表明APN與BMD、骨轉換生化指標可同時作為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標志物,其中APN可通過促進成骨細胞增殖及活性,抑制破骨細胞,促進骨形成,可作為反映骨代謝狀態的新型預測因子〔24〕。既往Stojanovic等〔25〕也發現APN可作為代謝綜合征絕經后婦女低BMD的潛在生物標志物。
綜上,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血清APN、BMD及骨轉化生化指標發生明顯改變,且APN與BMD、骨轉換生化指標有一定關系,可作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新型預測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