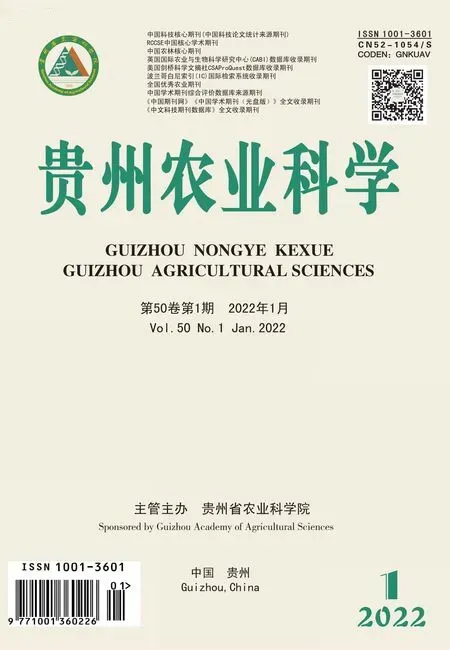小麥秸稈還田模式對秸稈腐解及土壤性質的影響
李 祥, 柯希恒, 王樹星, 曹山朝, 張養利, 曾 橋, 王永平
(1.陜西科技大學 化學與化工學院,中國輕工業輕化工助劑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 710021; 2.陜西農產品加工技術研究院,陜西科技大學 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陜西 西安 710021; 3.渭南市農業科學研究所 蒲城試驗站,陜西 渭南 715501)
0 引言
【研究意義】由于農藥、化肥的超量使用,我國糧食在實現“12連增”的同時,土壤問題越來越嚴重,土壤中有機質含量僅為0.8%~1.5%,較20世紀90年代初下降0.35%[1],耕作層僅為8~10 cm,碳饑餓成為我國土壤面臨的主要問題[2]。2015年糧食產量不再隨化肥使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多地還出現減產現象[3]。秸稈是補充土壤有機碳的主要原料,據測算,100 g秸稈中含碳44.2 g、氮0.62 g、磷0.25 g(五氧化二磷)、鉀1.44 g(氧化鉀),以及鈣、鎂、硫、硅、鐵、鋅、錳、鉬等中、微量元素[4],是十分理想的肥料資源。秸稈還田被認為是培肥地力的好方法[5]。【前人研究進展】研究表明,我國秸稈還田主要采用傳統的秸稈原位直接還田,還田后存在秸稈腐解較慢、對土壤營養成分提升不明顯等現象[6]。【研究切入點】目前,我國農業上秸稈還田技術應用范圍窄、力度弱,大面積推廣還存在一定難度,究其原因與秸稈還田的措施不到位有關[7]。【擬解決的關鍵問題】開展秸稈還田措施對秸稈腐解率與土壤性質的影響研究,比較秸稈還田模式對秸稈腐解、土壤有機質含量及土壤理化性質(溫度、濕度與容重孔隙率)的影響,旨在為高質量秸稈還田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試驗在渭南市農業科學研究所孫鎮試驗站旱地作物試驗田進行,試驗田為小麥-玉米一年兩季連作種植,收獲的小麥秸稈作為還田材料。自制農用微生物菌劑,陜西科技大學農林技術推廣中心提供;土壤調理劑,陜西農產品加工技術研究院提供;尿素,蒲城縣農資市場購買;畜禽有機肥,蒲城縣孫鎮養豬場提供。
1.2 試驗方法
1.2.1 輔助劑添加模式 試驗于2018年5月中旬開始。以添加不同輔助劑小麥秸稈還田模式為對象,設4個處理,每處理3次重復,小區面積30 m2。處理1:微生物菌劑(哈茨木霉)2 kg/667m2;處理2:微生物菌劑(哈茨木霉)2 kg/667m2+尿素10 kg/667m2(或等量氮豬糞);處理3:微生物菌劑(哈茨木霉)2 kg/667m2+尿素(或等量氮豬糞)10 kg/667m2+土壤調理劑12 kg/667m2;處理4(CK),秸稈直接還田,不添加輔助劑。小麥成熟期采用人工收獲后,根據試驗設計將輔助劑均勻撒入試驗田,用旋耕機旋耕,旋耕深度不低于12 cm,之后播種玉米。考察不同輔助劑添加模式秸稈腐解率及土壤有機質含量的變化。
1.2.2 耕作模式 試驗于2019年5月中旬開始,選擇地力條件基本相同的地塊,小麥成熟期采用人工收獲后,按照最佳輔助劑添加模式(處理3)進行還田,以不同耕作模式為處理對象,設置3個處理,3次重復,試驗區面積約3 000 m2。處理1,小麥秸稈深翻后進行玉米播種,深翻深度不低于20 cm;處理2,利用深松免耕技術播種玉米;處理3,硬茬播種玉米。研究不同耕作模式對秸稈腐解率及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影響。
1.2.3 小麥機械收獲模式 試驗于2020年5月中旬開始,選擇地力條件基本相同的2片小麥田,每片約1 hm2,以小麥收獲機械為處理對象,選擇日本洋馬聯合收獲機和國產雷沃谷神GE50進行收獲。收獲后按照最佳輔助劑添加模式(處理3)進行還田,最佳耕作模式(深松免耕模式)播種玉米,研究不同收獲機械處理對秸稈腐解率、纖維素、木質素降解率的影響。
1.2.4 微生物菌劑活化模式 選擇地力條件基本相同的地塊,小麥成熟后采用日本洋馬聯合收獲機,按照最佳輔助劑添加模式(處理3)進行還田,以其中微生物菌劑(哈茨木霉)是否活化為處理對象,設置2個處理,以深松免耕模式進行玉米播種,研究同種微生物菌劑活化與否對秸稈腐解率的影響。
1.3 測定指標
從當年玉米播種至翌年小麥成熟(秸稈還田期1年),每2個月按S型取樣法隨機選擇15 cm×15 cm的取樣點,取0~10 cm深度土層的土樣帶回實驗室,用分樣篩去掉雜物,水清洗干凈后,在105℃的烘箱中烘至恒重,測定土壤有機質含量、容重、土壤溫度及濕度,計算秸稈腐解率、纖維素和木質素降解率。試驗前土壤有機質含量、容重、孔隙率均為每年玉米播種后10 d時0~10 cm處的平均值。


1.4 數據統計
采用SPSS 16.0和Orign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輔助劑添加模式小麥秸稈腐解率與土壤性質變化
2.1.1 秸稈腐解率 由表1看出,整體上小麥秸稈腐解率隨還田時間推移而提高。秸稈還田12個月,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尿素處理與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尿素+土壤調理劑的處理腐解率均達100%,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處理為92.7%,秸稈直接還田(CK)處理僅為51.7%。不同輔助劑添加后小麥秸稈腐解率差異明顯,添加尿素調節碳氮比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長繁殖,提高秸稈腐解率。尿素、微生物菌劑協同作用,加速秸稈腐解。說明調節碳氮比、添加微生物菌劑對秸稈全量還田是可行的,該結論與大部分學者的結論一致[8-9]。

表1 不同秸稈還田模式各還田時間秸稈的腐解率
秸稈腐解率增加值(腐解速度)隨還田時間增加呈先增后減再增趨勢,秸稈還田4個月時,即每年的6—8月秸稈腐解速度最大,秸稈還田8個月后,即每年的12月至翌年2月,秸稈腐解速度最小,其原因是6—8月地溫較高,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長繁殖及代謝,加之此時秸稈腐解的產物濃度小,對秸稈腐解的抑制作用相對較小,故此時秸稈腐解率最大[10];而12月至翌年2月土壤溫度低,降雨量小,秸稈腐解產物濃度相對較大,對秸稈腐解抑制作用較大,秸稈腐解速度最小。
2.1.2 土壤溫度與含水率 由表2看出,秸稈還田2個月、4個月、12個月,即每年的6—8月及翌年3—4月土壤0~20 cm處的平均溫度均低于地表溫度;秸稈還田6~10個月時,即每年10月至翌年2月,土壤0~20 cm處的平均溫度高于地表溫度,說明秸稈還田具有調節土壤溫度的作用[11]。

表2 不同秸稈還田模式各還田時間土壤的溫度與含水率
秸稈還田土壤含水率有隨空氣濕度變化而變化的趨勢,秸稈還田6個月,即每年的10—12月,陜西降雨量大,空氣濕度大,各處理中土壤0~20 cm處的平均含水量最大。添加微生物菌劑的處理土壤含水率明顯高于秸稈直接還田(CK)處理,原因是秸稈腐解產物如酸、醛、酮、酯類化合物中親水性集團多,持水率強[12]。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尿素+土壤調理劑處理的土壤0~20 cm的平均溫度、平均含水率均高于其他處理,說明土壤調理劑具有改善土壤性質的作用,其原因是土壤調理劑中的碳酸鈣與秸稈降解產生的酸作用形成鈣離子,鈣離子具有促進土壤團聚體形成的作用[13],從而使得土壤的蒸發量減少,持水力增加。
2.1.3 土壤有機質含量、容重、孔隙率及團聚體結構 由表3看出,隨秸稈還田時間推移,各處理土壤中有機質含量均逐年增加,土壤容重均逐年下降,孔隙率均逐年增加,粒徑大于2.5 mm團聚體的比率均逐年上升。秸稈還田前土壤有機質含量為1.11%,還田1年后提高至1.12%~1.16%,提高0.9~4.5百分點;連續3年秸稈還田后,土壤有機質含量提高至1.17%~1.24%,提高5.4~11.7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35~2.93百分點。秸稈還田前土壤容重為1.45 g/cm3,還田1年后降至1.27~1.41 g/cm3,降低2.8%~12.4%;連續3年還田后,土壤容重降至1.03~1.27 g/cm3,降低12.4%~28.9%,平均下降3.1%~7.2%。秸稈還田前土壤孔隙率為45.3%,還田1年后提高至47.9%~52.1%,提高5.7~15.1百分點;連續3年秸稈還田后,土壤孔隙率提高至52.1%~61.1%,提高15.1~34.8百分點。秸稈還田前DR0.25(大于2.5 mm土壤團聚體占比例)為76.5%,還田1年后提高至78.1%~82.3%,提高2.1~7.6百分點;連續3年秸稈還田后,DR0.25提高至83.2%~92.6%。

表3 不同秸稈還田模式各還田時間土壤的有機質含量、容重、孔隙率及團聚體結構
土壤中有機質含量高,微生物可利用的碳多且活性強,微生物代謝產物越多,土壤容重越小,孔隙率越大,土壤氧氣濃度大,促進土壤中微生物菌群改善和活力提高,最后達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故秸稈還田是改良土壤性質的重要方法[14-15]。
綜上,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尿素與添加自制微生物菌劑+尿素+土壤調理劑處理秸稈的腐解率最大,還田1年后秸稈完全腐解變成有機肥,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在解決土壤“碳饑餓”的同時疏松土壤,增加土壤孔隙率,降低土壤容重,對促進土壤團聚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秸稈還田的最佳模式。
2.2 不同耕作模式小麥秸稈的腐解率及土壤有機質的含量
耕作模式不同,小麥秸稈的腐解率及土壤的有機質含量不同。由表4看出,深翻播種處理秸稈還田10個月后腐解率為100%,土壤有機質含量1.20%;硬茬播種處理秸稈還田12個月,腐解率僅為60.9%,土壤有機質含量1.14%;深松免耕處理秸稈還田12個月腐解率達100%,有機質含量1.16%。深翻后秸稈被包圍在土壤微生物環境中,10個月可完全降解,適宜的碳氮比、溫度、水分含量為微生物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促進微生物繁殖,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硬茬播種秸稈與土壤接觸有限,只能靠自然力量進行降解。因此,建議小麥秸稈還田的地塊下茬耕作模式采用深翻或深松免耕。

表4 不同耕作模式各還田時間秸稈的腐解率及土壤有機質含量
2.3 不同小麥收獲機械處理秸稈的腐解率、纖維素及木質素降解率
由表5看出,小麥收獲機械不同其秸稈腐解率、秸稈中纖維素及木質素的降解率不同,其原因是2種機械的收獲原理有一定差別,洋馬收獲機出料口設在機器后面,拋撒均勻,無秸稈堆積發生,而雷沃收獲機有2個出料口,側邊出料口出的是較長秸稈,后邊出的是較小秸稈,容易形成秸稈帶,秸稈帶上的秸稈即使深翻入土壤,也容易造成跑風冒氣。秸稈纖維素、半纖維素降解率明顯高于木質素降解率,其原因是纖維素、半纖維素是由五碳糖、六碳糖通過單鍵連接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而木質素是由苯環類化合物通過δ鍵和Π鍵連接成的大分子化合物,苯環中Π鍵的存在[16],增加其穩定性,不易受外界干擾。故在秸稈還田時采用粉碎、柔絲技術更有利于提高秸稈腐解。建議有條件地方盡可能采用洋馬聯合收獲機進行收獲。

表5 不同小麥收獲機械各還田時間秸稈的腐解率、纖維素和木質素降解率
2.4 微生物菌劑不同處理秸稈的腐解率
由表6看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施用活化后的微生物菌劑(哈茨木霉)處理還田10個月時,秸稈腐解率達100%,而施用未活化微生物菌劑的處理秸稈腐解率為82.3%。其原因是微生物菌劑經活化處理后帶上部分小分子營養物質供微生物生長繁殖,加速秸稈腐解。

表6 微生物菌劑不同處理各還田時間秸稈的腐解率
3 討論
秸稈還田模式對秸稈腐解率、土壤溫度、濕度、土壤有機質含量、容重、孔隙率、團聚結構均有影響。研究發現,秸稈還田+尿素+微生物菌劑模式還田12個月秸稈腐解率達100%,較秸稈還田+尿素模式高7.3%,比秸稈直接還田模式高48.3%。秸稈還田具有調節土壤溫度、蓄水保墑作用,具體表現在寒冷時土壤的溫度高于地表溫度、炎熱時土壤溫度低于地表溫度。秸稈還田+尿素+微生物菌劑+土壤調理劑模式土壤含水率較大,土壤有機質含量較秸稈直接還田模式提高4.5%,容重降低12.4%,孔隙率增加34.8%,DR0.25提高7.6%。
深翻播種、深松免耕處理秸稈還田12個月其腐解率均達100%,較硬茬播種處理提高39.1%,土壤有機質含量較硬茬播種處理提高0.02百分點和0.06百分點,在同樣條件下,洋馬聯合收獲機較雷沃聯合收獲機還田12個月后秸稈腐解率提高7.1%。施用活化微生物菌劑的處理較施用未活化微生物菌劑的處理秸稈腐解率提高。
4 結論
進行小麥秸稈還田處理的地塊,小麥成熟期盡可能采用洋馬聯合收獲機進行收獲,秸稈還田盡可能采用秸稈+尿素+自制微生物菌劑+土壤調理劑的模式還田,下茬耕作模式采用深耕播種、深松免耕交替進行,微生物菌劑施用時最好進行活化并帶足營養,采取上述技術措施條件下,還田10個月秸稈腐解率達100%,并可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改善土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