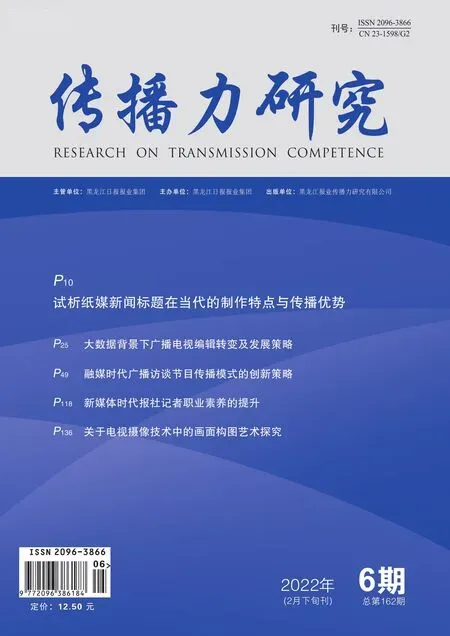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分析
◎蘇天行
(江蘇省靖江市融媒體中心,江蘇 靖江 214500)
引言
對事件進行還原,提高內(nèi)容敘述的完整度,并通過藝術(shù)加工闡述現(xiàn)象與問題,是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所需著重探討的對象,提高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性,需要由編導(dǎo)在現(xiàn)場中的設(shè)計與指導(dǎo),從專業(yè)的視角完成拍攝及鏡頭視角的轉(zhuǎn)換工作。同時,電視紀(jì)錄片是一種對藝術(shù)加工和創(chuàng)作過程,其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領(lǐng)域性,現(xiàn)已成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人員以及行業(yè)發(fā)展的趨勢,這就涉及對畫面內(nèi)容進行組織加工等多種創(chuàng)作問題,由此可知,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必須擁有畫面組成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以及明晰和確定的內(nèi)容規(guī)劃,這直接影響了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內(nèi)涵,需要編導(dǎo)人員在現(xiàn)場控制中,擔(dān)任其掌握鏡頭轉(zhuǎn)換節(jié)奏,光影構(gòu)成和畫面敘事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在確保內(nèi)容真實、內(nèi)涵豐富、節(jié)奏流程的鏡頭表現(xiàn)中,使所創(chuàng)作的電視紀(jì)錄片擁有更具人文色彩和藝術(shù)特色。
一、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的要求
(一)拍攝內(nèi)容層面的要求
確定好拍攝主題,才能基于內(nèi)容、表達(dá)視角以及光影組成明確上述幾種內(nèi)容的藝術(shù)關(guān)系。同時,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工作是對紀(jì)錄片藝術(shù)色彩的把握,在不脫離闡述真實事件這一前提下進行,只有當(dāng)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過程與人文色彩相互結(jié)合后,才能在拍攝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以靖江印記《青春無畏》為例,在拍攝內(nèi)容及畫面構(gòu)成上,編導(dǎo)利用長鏡頭與采訪鏡頭等手法進行了鏡頭語言的創(chuàng)作和表達(dá),這是通過鏡頭語言提高視覺藝術(shù)關(guān)系的現(xiàn)場控制方法,利于從淺入深地表明社會現(xiàn)象,也能夠從時間的推進中明確拍攝內(nèi)容的層級關(guān)系。而為了全方位、全面地解決人物情緒的表現(xiàn)及表達(dá)問題,編導(dǎo)還需要通過剪輯和視覺引導(dǎo)的方式,為表明內(nèi)容與內(nèi)容之間的發(fā)展關(guān)系,以此在分-總或總-分-總的表達(dá)中,給予觀看者流暢的紀(jì)錄片觀影體驗。這就使得,可利用的畫面素材成了幫助紀(jì)錄片現(xiàn)場人員表達(dá)情感,與屏幕前的觀看者進行情感對話的元素。
(二)進度控制層面的要求
為了向觀看者展示流暢的故事,還需從鏡頭藝術(shù)層面進行現(xiàn)場控制方法的學(xué)習(xí)與探討,尤其是基于進度要求,協(xié)調(diào)藝術(shù)性與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過程的關(guān)系,也只有這樣才能按計劃完成攝影工作,給予后期工作人員更多的處理空間。這是由于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需要各方的配合,也需要后期人員對畫面及鏡頭語言的剪輯,只有按照流程、按照進度要求完成現(xiàn)場拍攝計劃,才能在人員的配合中,產(chǎn)生的巨大效應(yīng)。這就需要現(xiàn)場編導(dǎo)依照紀(jì)錄片的內(nèi)核以及人物的情感訴求,合理規(guī)劃現(xiàn)場拍攝的流程與組織方式,以此利用環(huán)境與人物的配合,光影與畫面的關(guān)系,幫助大家更好地進入表演狀態(tài),這是進行現(xiàn)場控制的一種思路,同樣也是控制進度的一類辦法。
比如,靖江印記《我的相聲夢》的創(chuàng)作中,藝術(shù)表達(dá)只是幫助編導(dǎo)把握鏡頭語言的一種方法,其工作重心應(yīng)落于按計劃控制拍攝周期上,依靠后期剪輯等數(shù)字化的辦法,確保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特征,才能基于所拍攝的內(nèi)容,通過剪輯手法的配合以及后期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把鏡頭語言覆蓋不到的元素融入其中,讓每一個觀看者都能隨著人物情感的變化,鏡頭語言以及視角關(guān)系的變化,感受到電視紀(jì)錄片的魅力以及本土化的節(jié)目特征。
(三)剪輯及后期加工要求
鏡頭剪輯是有層級關(guān)系的,也具有整理視頻素材的意義,可以讓紀(jì)錄片的鏡頭表達(dá)變得更流暢,也更利于觀看者梳理其中闡述的問題。正因此,編導(dǎo)在工作現(xiàn)場中應(yīng)致力于確保畫面的流暢度,在自然的敘事節(jié)奏中,尋找獨一無二的鏡頭語言。以便結(jié)合不同生活視角下的案例,從拍攝指導(dǎo)、道具使用的安排中,提高所拍攝內(nèi)容的可利用價值,降低后續(xù)剪輯工作人員的工作難度。其次,無論是環(huán)境的變化,還是說光影及色彩關(guān)系的改變,都會影響到紀(jì)錄片的畫面表現(xiàn)力,一旦畫面中可利用的素材與創(chuàng)作內(nèi)核脫離,那么將難于通過剪輯的方式,發(fā)揮出整合素材信息、減少成本投入方面的優(yōu)勢,這是對現(xiàn)場編導(dǎo)人員提出的工作挑戰(zhàn)。正因如此,現(xiàn)場編導(dǎo)人員應(yīng)提高拍攝畫面的可利用率,這也被認(rèn)為是降低拍攝成本,確保紀(jì)錄片內(nèi)容可以表達(dá)情感關(guān)系的必要條件。最后,有效的后期剪輯手法,是基于良好內(nèi)容基礎(chǔ)上進行的,這就需要編導(dǎo)在現(xiàn)場控制中,向工作人員分享更多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幫助現(xiàn)場人員深入了解拍攝及表演技術(shù),以此從多種視角闡述不同局面下的故事,提高拍攝素材的可使用率。
二、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的價值
(一)降低環(huán)境因素的限制
視覺化的信息載體影視作品創(chuàng)作的內(nèi)核,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應(yīng)基于此進行創(chuàng)作內(nèi)涵的探析,而對外在環(huán)境的使用,是提高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人文性的最重要一環(huán),也是紀(jì)錄片拍攝過程中,通過先進開放的拍攝理念以及配合特有的環(huán)境,在最大程度上激發(fā)紀(jì)錄片表演者情感的方式,這對紀(jì)錄片的表達(dá)及創(chuàng)作而言至關(guān)重要。同時,環(huán)境因素對紀(jì)錄片拍攝還有一定的限制影響,這是由于雖然天氣的變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編導(dǎo)表達(dá)特有的情感,但惡劣環(huán)境的影響,往往不利于編導(dǎo)人員通過拍攝內(nèi)容與環(huán)境要素的配合,闡述特有的情感關(guān)系,這將對紀(jì)錄片的拍攝周期產(chǎn)生更多影響。而在進行現(xiàn)場控制工作中,利用人造光模擬特定的場景以及還原縱深關(guān)系,可以減少環(huán)境因素的限制,使整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在內(nèi)容、光影以及可傳播方面具有優(yōu)勢。可見,在現(xiàn)場控制工作中,編導(dǎo)人員首先應(yīng)基于對畫面表達(dá)的分析,更好地使用環(huán)境要素進行創(chuàng)作和表達(dá)。其次,編導(dǎo)人員還應(yīng)根據(jù)畫面道具和可使用的元素進行分析,以此確保畫面中主體關(guān)系和縱深關(guān)系明確,將環(huán)境及天氣的變化作為輔助創(chuàng)作的要素,完成本職工作。
(二)減少人員調(diào)度的影響
紀(jì)錄片的制作往往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這是由于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對光影、收聲的要求較高,通過故事闡述觀點,結(jié)合紀(jì)錄片中人物的語言側(cè)面反映現(xiàn)象,是紀(jì)錄片這一創(chuàng)作內(nèi)容的固有特點,也只有基于此進行現(xiàn)場控制工作的探討和分析,才能通過對拍攝人員、打光人員以及收聲人員的安排,配合現(xiàn)代化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方式,優(yōu)化現(xiàn)場拍攝中各方人員的工作組成,基于紀(jì)錄片制作和生產(chǎn)的流程,通過工作安排以及技術(shù)指導(dǎo)的方式,提高紀(jì)錄片拍攝效率。例如,紀(jì)錄片節(jié)目《陳函輝》,為了更具體深入地向觀看者介紹紀(jì)錄片內(nèi)容,需要對現(xiàn)場的人員進行細(xì)分,按照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紫陽街的特點,對畫面表現(xiàn)、鏡頭語言以及收聲方面的要求,幫助現(xiàn)場工作人員進行工作配合與合作,現(xiàn)場為工作人員答疑解惑,包括職能的劃分、構(gòu)圖外人員的站位等。最后,減少人員影響的第二大價值在于降低紀(jì)錄片制作與拍攝的難度,使拍攝的素材更加符合藝術(shù)表達(dá)的要求,確保后續(xù)的剪輯工作不會對觀看者造成邏輯關(guān)系的影響,并且能夠基于紀(jì)錄片表達(dá)的內(nèi)核,在內(nèi)容與制作方法上進行更多的探討,使現(xiàn)場拍攝工作的職能劃分明確,把握紀(jì)錄片現(xiàn)場控制工作需要整合的信息多、效率要求快、內(nèi)容質(zhì)量高的特點。
(三)避免拍攝技術(shù)受限
通過對節(jié)目《陳函輝》拍攝手法進行梳理可知,這類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在內(nèi)容體量上更小,在固定成本投入的基礎(chǔ)上,把握內(nèi)容與鏡頭切換的特點,可更貼切地表達(dá)出陳函輝懷揣遺憾而去,留給靖江和臨海無限思念的情感。這是由于此種紀(jì)錄片無論是在篇幅上,還是在投入上都具有精簡的特點,這使得拍攝方法成了現(xiàn)場編導(dǎo)控制工作的核心,只有平衡視覺表達(dá)和畫面構(gòu)成的關(guān)系,并基于紀(jì)錄片闡述的問題,投入相關(guān)研究,才能通過對前期拍攝手法的控制以及后期剪輯工作的配合,確保題材和內(nèi)容不會受限,也利于后期人員的剪輯。此外,細(xì)究拍攝層面的問題,對本項工作影響頗深的是鏡頭語言的動靜設(shè)計以及鏡頭切換與內(nèi)容進展的銜接。也只有通過編導(dǎo)人員對現(xiàn)場鏡頭的控制,才能更好地表達(dá)這一紀(jì)錄片的拍攝理念,為觀看者提供視覺信息、引導(dǎo)信息流暢的紀(jì)錄片內(nèi)容,使整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更加立體,并從全景、分景以及細(xì)部配合中,落實紀(jì)錄片編導(dǎo)人員的想法,使現(xiàn)場控制工作更具效率。最后,現(xiàn)場編導(dǎo)人員應(yīng)對關(guān)鍵幀這一攝影要素進行提取,因為這是表達(dá)鏡頭沖擊力、情感沖擊力的元素,甚至影響了紀(jì)錄片拍攝的最終效果。除此之外,依靠關(guān)鍵幀進行剪輯是較為簡單的工作方式,有利于縮減紀(jì)錄片拍攝的周期,使紀(jì)錄片的鏡頭語言盡可能豐富,邏輯關(guān)系盡可能明顯。
三、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中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
(一)制定拍攝預(yù)案
拍攝預(yù)案影響了紀(jì)錄片制作與內(nèi)容呈現(xiàn)的方式,在當(dāng)前時代下,各類型紀(jì)錄片作品頻出,使得紀(jì)錄片最終呈現(xiàn)出的方式發(fā)生了較多改變,但無論是按照時間長度進行劃分,還是從拍攝語言的視角下探討,類型細(xì)分的過程,使得紀(jì)錄片的制作標(biāo)準(zhǔn)以及制作要求逐漸增長。但細(xì)究起來,進行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核心在于選定拍攝預(yù)案,并在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中、編導(dǎo)人員的現(xiàn)場控制中,確保制作的內(nèi)容能夠解決預(yù)案的最終形態(tài),這對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以及對畫面素材的再挖掘來說具有更好的增益作用。比如,《靖江印記》:青春無畏的制作,這是種類型特征明顯的作品,使得整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更需要拍攝預(yù)案的支持,在此基礎(chǔ)上做好內(nèi)容的分化工作,不僅可有效減少編導(dǎo)在現(xiàn)場控制工作中所面臨的工作挑戰(zhàn),還能以預(yù)案為線索,通過對畫面元素的運用,探索出紀(jì)錄片藝術(shù)表達(dá)的新方向、新途徑。因此,現(xiàn)場編導(dǎo)人員在進行紀(jì)錄片拍攝中,需要重視前期預(yù)案的影響,合理組織各項資源的投入外,通過對現(xiàn)場拍攝素材的挖掘與整合使用,確保紀(jì)錄片拍攝的藝術(shù)性和人文特征,這是賦予紀(jì)錄片精神價值的重要條件。
(二)加強現(xiàn)場管理
對編導(dǎo)工作的流程以及分項內(nèi)容進行分析可知,編導(dǎo)首先應(yīng)對固定鏡頭的拍攝方法進行布置,從中按職能分配人員進行拍攝工作,還需對紀(jì)錄片拍攝要求進行全面的分析,并根據(jù)拍攝團隊的人員、設(shè)備和道具的使用情況,加強各個拍攝環(huán)節(jié)的銜接度,這意味著能夠使各崗位人員在自身本職工作的基礎(chǔ)上進行拓展,易于按照拍攝計劃安排工作內(nèi)容。可見,編導(dǎo)現(xiàn)場管理工作的價值,在于對拍攝預(yù)案的交底與組織,通過明確的職責(zé)劃分或許無法確保整個拍攝工作的藝術(shù)性特征,雖然是無奈之舉,但只有在職能明確的基礎(chǔ)上,確保紀(jì)錄片在固定周期中完成,才能解決現(xiàn)場控制工作中的頑固問題,有機會減少紀(jì)錄片拍攝工作在人力及物力上的投入成本以及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工作的影響范圍,使所有紀(jì)錄片拍攝問題都能落實到個人層面。最后,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作為一項集藝術(shù)性、人文性為一體的內(nèi)容呈現(xiàn)方式,需要內(nèi)容的完整,也需要進行流程及成本上的優(yōu)化,而做好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工作,能夠帶動拍攝效率的提升,也能賦予后期剪輯人員更多的工作空間,使整個拍攝鏡頭更加流程、邏輯關(guān)系更加明顯。
(三)運用鏡頭語言
無論是電影藝術(shù)還是電視紀(jì)錄片的表達(dá),都是在鏡頭語言的應(yīng)用中,快速理清任務(wù)關(guān)系和故事內(nèi)核的先決條件。同時,鏡頭語言需要與道具元素配合,也需要在大環(huán)境中進行設(shè)置,因此,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工作,不應(yīng)僅局限于道具和人員工作的控制上,還應(yīng)通過對鏡頭語言的控制以及對道具等拍攝素材的挖掘,認(rèn)識到不同鏡頭語言對表達(dá)內(nèi)容、表達(dá)人文屬性起到的重要影響。例如,靖江印記《我的相聲夢》的紀(jì)錄片拍攝中,拍攝人員主動改變了以前的鏡頭運用關(guān)系,以內(nèi)容制作與情感表達(dá)為方向,在探索鏡頭語言轉(zhuǎn)換方式的基礎(chǔ)上,挖掘了更多可用的機位和素材,配合畫面縱深感的設(shè)置,能夠使故事與采訪過程的銜接度更高,使運用鏡頭語言的技法和拍攝內(nèi)容的表達(dá)更加豐富,也在鏡頭語言的轉(zhuǎn)換下,落實了編導(dǎo)的創(chuàng)作意圖。最后,設(shè)備的保護以及高精尖設(shè)備的使用,也是編導(dǎo)的現(xiàn)場控制工作,基于上述兩個要求,確保高精尖設(shè)備能夠得到妥善的使用,可在內(nèi)容層面融入更多的創(chuàng)作思想,在人文特征上發(fā)揮出編導(dǎo)現(xiàn)場控制工作的價值。
四、結(jié)語
電視紀(jì)錄片編導(dǎo)的現(xiàn)場工作,不應(yīng)僅從設(shè)備、人員以及成本投入的角度進行介入分析,還應(yīng)從電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性以及現(xiàn)場的設(shè)計和藝術(shù)指導(dǎo)中進行,以便從更加專業(yè)的視角,展示人物和視角關(guān)系,并通過鏡頭的轉(zhuǎn)換進行藝術(shù)的再加工和再創(chuàng)作。需要編導(dǎo)具備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以及依照內(nèi)容規(guī)劃的方式,賦予電視紀(jì)錄片更多的內(nèi)在價值,使本身的工作能夠?qū)o(jì)錄片拍攝起到直接影響,確保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內(nèi)涵,也能夠更好地掌握鏡頭轉(zhuǎn)換節(jié)奏和畫面敘事的相關(guān)方法,達(dá)到豐富內(nèi)涵、確保節(jié)奏流程的目的外,使所創(chuàng)作的電視紀(jì)錄片成為更具人文色彩和藝術(shù)內(nèi)容的藝術(shù)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