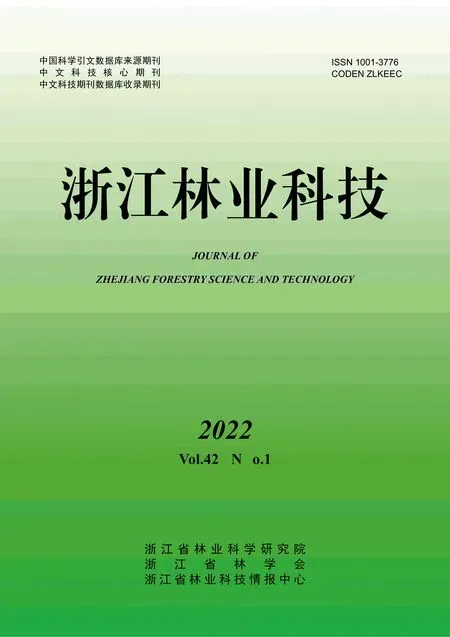旅游干擾對雞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
尚晴,王忠偉,程露
(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4)
在全球范圍內,基于自然資源的旅游活動(Nature-based Tourism)已經成為人們旅游休閑的重要形式。森林占陸地生態系統面積的1/4[1],因空氣質量優良、負氧離子豐富、動植物資源多樣等特征而備受游客青睞。森林風景區硬件設施的大幅投入以及游客接待量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有助于地方經濟水平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與旅游活動同步發生的開發、踩踏和垃圾排放等干擾過程對風景區生態環境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2-3]。土壤作為森林生態系統的重要構件,是生物繁衍與多樣性維持的基礎,相對于地表植物,其對于旅游干擾的反應更為敏感。國內外研究證實,風景區內的旅游活動通常可導致土壤緊實度[4]、土壤容重[4-5]、土壤有機質和全氮含量[6-7]的顯著提高以及土壤孔隙度和含水量[8]的顯著降低。然而,旅游干擾對于部分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仍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干擾活動可導致土壤pH值的提高[8-9]或降低[5];也可引起土壤速效鉀的增加[10]或降低[9]。此外,旅游干擾還會導致森林土壤生物指標的變化,如改變微生物群落結構[11]和降低土壤酶活性[8],從而間接地影響土壤理化性質。
在以色列Ramat公園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旅游活動對公園土壤理化性質(如土壤容重、濕度、pH值和有機質)的影響依賴于干擾強度的大小,表現為在輕度干擾下變化微弱,而在重度干擾下變化顯著[12]。Iwara等研究發現,土壤中交換性陽離子的濃度在重度干擾活動下顯著下降[13],進一步調節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土壤養分的有效性。在我國四川碧峰峽生態旅游區開展的調查發現,中度干擾顯著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和土壤有效磷含量等理化指標,暗示著中度干擾活動對土壤理化特征有一定的積極作用[14]。綜上所述,盡管針對旅游活動及其生態效應的研究備受關注,但是旅游干擾對風景區土壤系統的影響過程仍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本研究以雞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的波爾登森林公園為例,通過調查不同干擾強度下距干擾中心區域不同距離處的土壤理化指標,以闡明土壤理化特征隨干擾強度的變化規律,揭示干擾距離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為森林風景區的旅游規劃和科學管理提供參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在河南省信陽市李家寨鎮雞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的波爾登森林公園(31°51′ N,114°05′ E)內實施。該公園海拔為245 m,年平均降水量為1 119 mm,年平均溫度為15.2 ℃。土壤類型以黃棕壤和黃褐土為主,土壤pH值介于4~ 5。公園內以天然次生林為主,植物資源豐富,喬木樹種主要有栓皮櫟Quercus variabilis、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楓香樹Liquidambar formosana等,灌木樹種主要有山胡椒Lindera glauca、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黃荊Vitex negundo等。波爾登森林公園是雞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下設的森林生態旅游景區,景區內有波爾登紀念亭、茗湖、森林游樂園等20多個景點,每年接待游客近10萬人次。
1.2 干擾強度設定
在波爾登森林公園內,按照游客聚集時間和活動強度的差異,選擇3個不同干擾強度的景點作為調查區:①游客步道 風景區內游客步道大多數為1.5~2.0 m寬的土質路面,未進行水泥硬化,步道內無明顯的游客聚集,每位游客的停留時間均 <5 min,將其游客干擾強度定義為輕度;②波爾登紀念亭 亭內均為水泥硬化地面,亭外2 m寬環路為土質地面,有明顯的游客聚集現象,游客可在圍欄和長椅上進行短暫的休息,每位游客的停留時間為20~ 30 min,將其干擾強度定義為中度;③森林游樂園 區域內90%地面為土質,游客聚集現象強烈,游客可進行集中玩耍和適當的餐飲活動,每位游客的停留時間均>60 min,將其干擾強度定義為重度(圖1)。

圖1 干擾強度及干擾距離樣點設定示意圖Figure 1 Location of sampling plots under different trampling intensities and their distances
1.3 干擾距離設定
在每種干擾強度調查區內,按照距離干擾中心區的遠近,分別布置3個采樣區,依次定義為干擾核心區、緩沖區和背景區(圖1)。核心區位于調查區的中心區域(0~ 1 m)(游客步道以土質路面中心為核心區;紀念亭以亭外土質環路為核心區;游樂園以中心區域的土質地面為核心區),此區域受游客踩踏和景區管理作業干擾強烈,地面無喬、灌、草植物的生長,無凋落物層,土壤硬實。緩沖區是距離中心區邊緣之外3~ 10 m的區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游客(采摘及拍照等)及景區管理活動(打掃衛生及設施維護)的影響,生長有喬、灌木,地表凋落物豐富。背景區是中心區邊緣之外10 m以上的區域,受到游客及景區管理活動影響微小,植被及土壤狀況均保持自然狀態。
1.4 土壤樣品采集與測定
在每種干擾強度下的不同干擾距離區域上分別采集土壤樣品。核心區樣點的選取方法:沿著游客步道方向,在步道上每隔5 m取1個樣點,共取4個樣點;在紀念亭外的土質環路上,每隔2 m取1個樣點,共取4個樣點;游樂園在中心區域附近每隔5 m取1個樣點共取4個樣點。緩沖區和背景區樣點的選取方法:分別在每個干擾區域內,每隔5 m取1個樣點,共取4個樣點。樣點土壤采集方法:在每個樣點上,利用環刀分別采集表層0~ 10 cm的土壤,共計3種干擾強度×3種干擾距離×4個重復=36個樣品。將采集的土壤樣品帶回實驗室。在環刀采集原狀土壤的同時,用直徑5 cm的土壤鉆分別在4個樣點采集1個0~ 10 cm的土壤樣品(共36個),帶回實驗室。
土壤理化性質的測定:用環刀法測定每個樣品的土壤容重,并根據測定結果計算土壤總孔隙度,土壤總孔隙度(%)=(1-土壤容重/土壤比重)×100%,式中,土壤比重取其經驗平均值,為2.65 g·cm-3。
土壤含水率采用烘干法測定,土壤有機碳含量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法測定,土壤全氮含量采用凱氏定氮法測定[13]。
1.5 數據分析
采用正態性檢驗和方差齊性檢驗確定數據分布狀態后,利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土壤理化指標在不同干擾強度以及不同干擾距離之間的統計顯著性;分析干擾核心區和緩沖區土壤理化特征相對于背景區的變化及其在不同干擾強度下的差異。
數據統計分析在SPSS 19.0中完成,圖表制作在Microsoft Excel 2010中完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干擾強度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
由不同干擾強度下土壤容重和總孔隙度的比較結果顯示(圖2),重度干擾下的土壤容重(1.23 g·cm-3)顯著高于輕度(1.03 g·cm-3)和中度(1.07 g·cm-3)干擾的(P<0.05);而重度干擾的土壤總孔隙(57.8%)則顯著低于輕度(61.3%)和中度(59.6%)干擾的(P<0.05)。

圖2 不同干擾強度對土壤容重(A)和總孔隙度(B)的影響(平均值±標準誤,n=12)Figure 2 Effect of different trampling intensities on soil bulk density (A) and total porosity (B)
由不同干擾強度下土壤含水率、全氮含量和有機碳含量的比較結果顯示(圖3),輕度干擾和中度干擾下的土壤含水率(18.0%和16.6%)之間無顯著差異(P>0.05),但二者均顯著高于重度干擾的(16.6%)(P<0.05);土壤全氮含量隨著干擾強度的增加而逐漸下降,輕度干擾的土壤全氮含量(2.2 g·kg-1)顯著高于中度和重度干擾土壤的全氮含量(1.9 g·kg-1和1.8 g·kg-1)(P<0.05);中度和重度干擾下土壤有機碳含量(19.3 g·kg-1和21.2 g·kg-1)之間無顯著差異,但是二者均顯著低于輕度干擾的土壤有機碳含量(26.8 g·kg-1)(P<0.05)。

圖3 不同干擾強度對土壤含水率(A)、全氮含量(B)和有機碳含量(C)的影響(平均值±標準誤,n=12)Figure 3 Effect of different trampling intensities on content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A),total nitrogen (B) and organic carbon c (C)
2.2 不同干擾距離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
將不同干擾強度的同一類干擾距離樣點的平均值進行比較,如圖4和圖5。由圖4和圖5可知,不同干擾距離樣點的土壤理化性質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干擾核心區的土壤容重(1.29 g·cm-3)顯著高于緩沖區的(1.07 g·cm-3)和背景區的(0.97 g·cm-3);而緩沖區的土壤容重顯著高于背景區的(P<0.05)。核心區的土壤總孔隙度(52.5%)顯著低于緩沖區和背景區的(60.7%和65.4%),同時,緩沖區的土壤總孔隙度顯著低于背景區的(P<0.05)。

圖4 不同干擾距離對土壤容重(A)與總孔隙度(B)的影響(平均值±標準誤,n=3)Figure 4 Effect of trampling distances on soil bulk density (A) and total porosity (B)
核心區的土壤含水率(14.1%)顯著低于緩沖區(17.8%)和背景區(21.3%)的,緩沖區的土壤含水率顯著低于背景區的(P<0.05)。核心區和緩沖區的土壤全氮含量(1.8 g·kg-1和1.9 g·kg-1)之間無顯著差異,但二者均顯著低于背景區的(2.2 g·kg-1)(P<0.05,圖5)。核心區的土壤有機碳含量(20.7 g·kg-1)與緩沖區之間無顯著差異,但是顯著低于背景區和(25.5 g·kg-1)(P<0.05)。

圖5 不同干擾距離對土壤含水率(A)、全氮含量(B)和有機碳含量(C)的影響(平均值±標準誤,n=3)Figure 5 Effect of different trampling distances on content of soil moisture(A),total nitrogen (B) and soil organic carbon (C)
2.3 不同干擾距離區域土壤理化性質隨干擾強度的變化
對不同干擾強度區域土壤的理化性質的分析發現,就土壤總孔隙度和土壤容重而言,緩沖區與背景區之間的差異顯著低于核心區與背景區之間的差異(P<0.05);緩沖區與背景區之間的差異隨著干擾強度的增加而下降;核心區與背景區之間的差異則在重度干擾下達到最大(圖6)。

圖6 不同干擾強度下各干擾距離之間的土壤容重(A)和總孔隙度(B)差異比較(平均值±標準誤,n=4)Figure 6 Comparison on soil bulk density (A) and soil porosity (B) among different disturbance distances under different disturbance intensities
3 討論
3.1 干擾強度對土壤理化特征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旅游干擾對土壤物理指標如土壤容重、總孔隙度和含水率的影響因干擾強度而異,僅在重度干擾下表現為差異顯著(P<0.05)。這與張淑花等在黑龍江二龍山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后者研究也發現,重度干擾顯著增加土壤容重,并降低土壤總孔隙度和含水率[16]。這表明土壤總孔隙度和含水率對輕度的踩踏具有一定的抗性,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方面,首先,土壤自身的團粒組成對外界干擾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并且冬季短暫的凍融過程有助于土壤表層結構的恢復[17];其次,植物根系的貫穿作用及土壤動物(如蚯蚓Lumbricussp.等)活動有助于短期干擾下土壤物理特征的恢復。然而,在游客活動強烈的重度干擾下,土壤自身結構及植物和動物活動難以抵消旅游活動的干擾。與土壤物理性質不同的是,土壤化學指標如土壤有機碳含量和全氮含量在中度干擾下就表現為顯著的下降,這意味著,土壤化學性質相比物理性質更容易受到干擾活動的影響。這與孫飛達等在若爾蓋草原上的研究結果相近。后者的研究發現,與背景區樣地相比,輕度干擾就能導致土壤全氮和有機碳含量的顯著下降[17]。首先,土壤化學性質受到母質及植物器官凋落物輸入的影響,游客活動及景區常規管理都會降低地面植物凋落物的輸入量[18];其次,土壤微生物活動在干擾下可能會降低,從而降低對凋落物的分解作用[19]。因此,土壤化學性質比物理性質對干擾的響應更為敏感,這意味著旅游活動可能會加劇森林土壤中碳、氮的損失。
3.2 干擾距離對土壤理化特征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與背景區相比,旅游干擾導致土壤容重與總孔隙度的變化在核心區和緩沖區具有不同的趨勢。具體表現為,旅游活動導致核心區土壤容重和總孔隙度變化隨干擾強度的增加而增加;然而,旅游活動導致的緩沖區土壤容重和總孔隙度變化隨干擾強度的增加而降低。根據調查,核心區的游客聚集數量和活動強度隨著干擾強度的增加均呈增加趨勢,因此對土壤物理性質(容重和總孔隙度)的負面影響趨于增加。緩沖區與核心區有一定的距離,相比于設施不全的輕度干擾(游客步道)和中度(波爾登紀念亭)干擾景點,本研究中的重度干擾景點(游樂園)集合了娛樂、休閑和餐飲等設施,游客活動范圍相對集中,加之長途跋涉勞累,游客很少再到緩沖區域內活動,因此,就形成了干擾對緩沖區部分物理指標的影響較弱的現象,這表明游客干擾對土壤理化特征的影響受干擾距離的影響。
4 結論
通過對河南雞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波爾登森林公園不同干擾強度和干擾距離區域的土壤理化特征的分析表明,土壤物理特征如土壤容重和總孔隙度僅在重度干擾下發生顯著變化,然而,土壤化學特征如土壤有機碳和全氮含量則在中度和重度干擾下均表現為顯著的下降。本研究結果表明,森林土壤的物理和化學特征對旅游活動干擾的響應敏感性存在差異,這與不同指標的形成和產生過程有關。此外,森林土壤理化特征對干擾的響應程度還受干擾距離的影響,干擾核心區土壤理化性質更易于發生變化。因此,在評價基于自然資源的風景區旅游活動與生態環境狀況時,需要同時考慮干擾強度和干擾距離的差異性影響,這也是景區管理部門在考量接待能力和環境承載能力時要權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