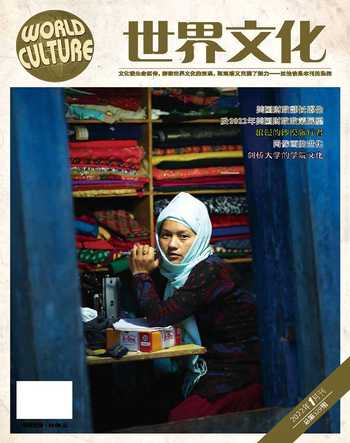獨特的研究探索
李忠東

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美國科學家真鍋淑郎、德國科學家克勞斯·哈塞爾曼和意大利科學家喬治·帕里西,以表彰他們為我們理解復雜物理系統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所有的復雜系統都由許多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組成,物理學家進行了幾個世紀的研究,卻很難用數學來描述它們。它們可能有大量的組成部分,或者受偶然支配。就像天氣一樣,也可能是混沌系統,初始值的小偏差會導致后期的巨大差異。這三位科學家迎難而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描述和預測復雜系統長期行為的新方法,揭示了它們背后隱藏的秘密,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此類系統及其長期發展趨勢。
2021年諾貝爾物理獎的一半獎金授予普林斯頓大學的真鍋淑郎和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的哈塞爾曼,以表彰他們“為地球的氣候進行物理建模,量化其可變性并可靠地預測全球變暖”。他們的研究表明,盡管天氣變化無常,然而計算機模型可以對地球大氣中不斷上升的二氧化碳的變暖效應做出具體的預測。模型清楚地顯示了溫室效應在加速,并指出人類活動是罪魁禍首。自19世紀中葉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了40%。幾十萬年來,地球大氣中從沒有過這么多的二氧化碳,而且溫度測量表明,過去150年全球變暖1°C。
諾貝爾物理獎的另外一半獎金授予羅馬大學的帕里西,以表彰他“發現從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統內的無序和波動的相互作用”。他發明了一種方法來理解某些磁性合金中的混沌原子運動,這被認為是對復雜系統理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其影響廣泛,甚至能幫助解釋數千只椋鳥的咕噥聲是如何協同行動的。
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主席、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斯德哥爾摩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托爾斯·漢斯·漢森在一份聲明中說:“今年的獲獎者為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復雜物理系統的特性和演化做出了貢獻,……氣候模型基于對觀測的嚴謹分析,是建立在愛因斯坦關于布朗運動理論的堅實基礎上的,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復雜物理系統的性質和演化。”關于氣候物理科學的研究價值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佩特里·塔拉斯在日內瓦指出,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顯示“氣候科學高度受到重視,且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巴黎索邦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氣候科學家桑德琳·博尼稱:“氣候是物理學學科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認識,早就應該研究了。”漢堡大學校長迪特爾·倫森盛贊哈塞爾曼這位在漢堡大學學習而開始走向世界頂級物理學之路的科學家。“他擔任漢堡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可以被認為是漢堡大學氣候研究的先驅。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學校已成為國際氣候研究中心。”
1931年10月25日,哈塞爾曼出生在德國漢堡市。父親是一名經濟學家、記者和出版商。他們雖不是猶太人,但全家生活在一個主要由猶太德國移民組成的社區。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哈塞爾曼快3歲的時候,與父母和姐姐一起移民到了英國。在英國,全家一直住在倫敦以北30公里的漂亮小鎮韋林花園城。哈塞爾曼就讀于韋林花園城小學和文法學校,在那里通過了A級考試(當時稱為高中證書)。哈塞爾曼很喜歡英國,他曾說:“我在英國感到很開心,英語實際上是我的第一語言。”
哈塞爾曼自述,在英國生活期間的一次事點燃了他對物理學的興趣。當時哈塞爾曼13歲,用2先令6便士從同學那兒購入一個晶體檢波器,在當時差不多是一張電影票的價格。晶體檢波器是20世紀早期無線電接收器中使用的一種電子元件,接上合適的電路就是一臺簡易的收音機。令他不可思議的是,竟然可以通過耳機聽到美妙的音樂。為了弄明白晶體檢波器的工作原理,哈塞爾曼忙著跑圖書館,從書本中尋找答案。
“這對我來說是一段令人興奮的經歷,我的物理‘啟蒙老師’是一個晶體探測器,完全獨立于學校所獲得的物理知識。我認為,這種個人學習和發現的經驗非常重要。” 哈塞爾曼坦言,“我的物理成績很好,但在老師眼里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學生,經常放學被處罰不許回家。幾十年過去了,‘哈塞爾曼,四點鐘留堂’這句話今天仍然在我耳邊回響。”
1949年,18歲的哈塞爾曼回到德國漢堡。回國后,哈塞爾曼曾在一家機械廠實習了半年,后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入漢堡大學學習,1955年獲得物理學和數學的文憑。哈塞爾曼繼續深造,僅僅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在馬克斯·普朗克流體動力學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博士論文的課題是對各向同性湍流(湍流指流體的一種流動狀態,各向同性湍流是一種最簡單的理想化湍流)的基本動力學方程進行更流暢的推導,由于堅持認為導師建議的方法行不通,用自己獨創的方法完成了研究,導師不太高興,給哈塞爾曼的博士論文判了相當于 B級的 2分,讓他畢業了。哈塞爾曼從此不走尋常路,開始了對物理的個人探索。他回到漢堡大學做了3年的博士后,繼續研究湍流理論。隨后在漢堡大學造船研究所進行流體動力學研究,主要是在船尾流中進行湍流實驗工作。
在學生時代,哈塞爾曼受到了帕斯夸爾·喬丹的啟發,后者在漢堡大學教授理論物理。哈塞爾曼說:“我和他沒有私下接觸,但我真的很喜歡他的講座。”哈塞爾曼堅持自主學習,讀有趣的書,像所有年輕科學家一樣熟悉與自己的研究有關的文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無論是學習期間還是之后的研究,我從來沒有遇到真正合適的導師,主要自己輔導自己。”
1961年,哈塞爾曼應著名海洋科學家沃爾特·蒙克的邀請,攜全家來到美國。哈塞爾曼在美國加州大學拉霍亞分校地球和行星物理研究所任助理教授,3年多的研究富有成果。其后,哈塞爾曼參加了蒙克組織的一場關于大海洋尺度的波浪實驗,在夏威夷觀測波浪,哈塞爾曼每天兩次檢查實驗數據,兼做后勤工作。他表示,美國的工作條件非常好,但他的妻子蘇珊娜不樂意,孩子們也沒有在德國時那么快樂,尤其是大女兒梅克,情緒變得相當不穩定,所以最終決定全家返回德國。

回國后,哈塞爾曼從1966 年起擔任漢堡大學地球物理和行星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在這期間,德國聯邦科學技術部提供專門資金在漢堡大學創建了一個理論地球物理系,并且聘請哈塞爾曼為該系的主任。成為教授之后的哈塞爾曼對學生出了名的嚴厲,有個學生在跟了他從事研究一年后出家當牧師了。這名學生后來向哈塞爾曼致謝,說他間接地鼓勵自己做出人生新決定。
1975 年至1999年,哈塞爾曼任漢堡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所長。該所成立于1975年,迅速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的氣候研究機構,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評估報告做出了重大貢獻。正是在這里,哈塞爾曼領導創建了氣候模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是德國的一所基礎研究機構,成立于1948年。這里人才輩出,成果累累,為德國乃至全世界的科技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馬克斯-普朗克太空物理學研究所所長、物理學家萊因哈德·根澤爾因在銀河系中央發現超大質量天體獲得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科學家們很早就知道,地球由于太陽光線照射表面而變暖,而大氣向太空發射紅外光使地球表面變冷,這兩種效應的平衡決定了地球的溫度。由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了部分紅外光,因此降低了冷卻的速率。隨著平衡的扭曲,導致全球氣溫升高。早在19世紀90年代,瑞典物理學家斯凡特·奧古斯特·阿倫尼烏斯就曾試圖預測二氧化碳上升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因為早期認為從上一層大氣到下一層的能量轉移純粹是通過輻射進行的,所以嘗試的方法過于簡單。
過去,研究人員習慣于從統計的角度研究氣候,然后以歷史數據為基礎對未來狀態進行推測。可氣候是一個長期變化且連續的復雜系統,自身內部所產生的變化也會影響到它的未來,因此僅僅憑借統計數據無法對未來趨勢做出準確的預測。建立復雜模型是一個具有非常挑戰性的研究項目。
在開發氣候模型方面,哈塞爾曼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首先使用簡單的模型來展示一些關于自然氣候變率的基本概念,接著構建更現實的模型,并將這些想法應用于整個氣候系統,即耦合的海洋——大氣環流模型。1976年,哈塞爾曼受愛因斯坦有關布朗運動的理論啟發,采用隨機微分方程,創建了一個將短期的天氣變化同長期的氣候變化相關聯的“哈塞爾曼模型”。它能根據一些基本的交互模式來捕捉控制整個復雜系統動力學的主要過程,將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與自然狀況下的氣候變化分離開來,更好地判斷人類活動究竟是如何影響氣候變化的。

隨機微分方程的每次積分都有不同的實現形式,決定了其構建的氣候模型像真實氣候環境一樣,存在著不確定性。并且這種不確定性進而對氣候本身產生影響,從而真實模擬出了氣候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下的變化趨勢。例如大氣中快速的溫度波動如何影響海洋溫度的長期變化,再如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與全球變暖之間的聯系。
哈塞爾曼還開發了用來識別自然現象和人類活動對氣候影響的特定信號,稱其為“指紋”。他發現,氣候模型以及觀測和理論考量,均包含了有關“噪聲”和信號特性的充分信息。例如,太陽輻射、火山有關顆粒或溫室氣體水平的變化會留下獨特的信號和印記,可被分離出來。這種印記識別方法也可應用于研究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影響,為進一步研究氣候變化掃清障礙。他證明,快速變化的大氣實際上會導致海洋緩慢變化。
哈塞爾曼后來回憶,他是在前往赫爾辛基開會的飛機上想到可以通過與布朗運動類比的大氣的短期波動來簡單地解釋長期氣候變化。他原先從事過湍流理論和熱線湍流測量方面的工作,因此熟悉各種形式的隨機過程。“噪聲”的來源是短時間尺度的湍流大氣,會在氣候系統的其余部分產生更長的時間尺度上的變化。哈塞爾曼還提出了相關的定量估計,很快使人們發現并普遍接受人為全球變暖是真實的。
為了具體介紹上述成果,諾貝爾獎官網運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對氣候進行預測,如同人在遛狗時,通過狗的足跡來預測人的行走路徑。寵物狗看似混亂的足跡便是天氣“噪聲”,但如果將時間拉長,尺度放大,看上去混亂無序的“噪聲”也可以反映出氣候的長期變化趨勢,就像我們可以通過狗的足跡來辨別人的運動路徑一樣。
雖然哈塞爾曼喜歡做理論模擬,但不只是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他參與了很多大型線下實驗,有一次還差點丟了性命。1961年,在蒙克主持的大型波浪實驗中,從新西蘭島開始,經過薩摩亞、巴爾米拉環礁等島礁,最后到阿拉斯加,沿著整個太平洋的大圓圈里建立了一系列測波站。幾位科學家分散在了不同的站點,其中科學家戈登·格羅夫斯和一名無線電操作員被空運到巴爾米拉。“ 二戰”期間那里是個空軍基地,后成為無人荒島。他們雖然帶了5臺發電機,但都是“二戰”時留下的,其中4臺經常出故障。有一天,荒島傳出消息說格羅夫斯的手受傷,流了不少血,隨后一周音訊全無。

哈塞爾曼焦慮不安,決定乘飛機去荒島看看。這是一架“二戰”遺留的老式B25 飛機,由于機上沒有導航設備,飛行員只能憑經驗飛行,往一個方向飛一段時間,考慮一下風向,算算自己在什么位置,離目的地還有多遠。由于飛行員頻頻失誤,根本找不到巴爾米拉。他們被迫無奈,往塔希提飛去。不湊巧的是那里正在下雷暴雨,無法讓他們降落。哈塞爾曼只得返回夏威夷。當時情況十分危機,B25 飛機已經用盡了最后一滴燃油,墜落事件隨時可能發生。為安全起見,整個夏威夷機場被清空,任何其他飛機都不得降落。如果當時不幸發生,后果不堪設想……事后,哈塞爾曼不甘心,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去營救那名“重病”的科學家。這次乘坐的是有導航的專業運輸機,終于降落到巴爾米拉。沒有想到,迎接他的是笑嘻嘻的格羅夫斯,只見他的手指上僅貼著一個小創可貼……
1968年夏天,哈塞爾曼回到德國開展跨國海浪研究。他協調英國、荷蘭、美國、德國等國家的有關單位實施“聯合北海波浪計劃”,從丹麥、德國交界處西海岸的敘爾特島沿西偏北方向,形成了一個伸入北海達160公里的測波斷面。沿斷面共布置了13個觀測站,采用多種觀測儀器觀測波浪。正當他們積極籌備海浪研究的時候,德國國防部的電話告之必須取消計劃。原來北約也打算在這個夏天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海對空導彈試驗,而哈塞爾曼他們的實驗設備會干擾到國防部門對導彈的跟蹤。
哈塞爾曼據理力爭,說為準備這個實驗至少花費了200萬德國馬克,國防部則告訴他海對空導彈試驗耗資5000萬德國馬克。物理學家向軍方討價還價,表示1968年可以只做簡化實驗,但1969年對方必須資助自己重做完整實驗。德國國防部同意了哈塞爾曼的要求。由于準備不足和通信被干擾等原因,第一次試驗徹底失敗,幾乎沒有獲得多少有用的數據。科研人員吸取教訓第二年再次組織進行全面的實驗,所有設備都運行良好,獲得了非常好的數據集。哈塞爾曼使用費曼圖(第三種建立量子力學的方式)對其進行了微擾處理,于1976 年開發出一個隨機氣候模型,確保了氣候的可變性。這個模型被全球200多個中心使用,其提供的海浪譜(描述海浪內部能量相對于頻率和方向分布的圖譜,又稱海洋能量譜)迄今仍被廣泛應用在海洋科學和海洋工程等領域。
“聯合北海波浪計劃”的成功對哈塞爾曼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這表明他具備開發一個新氣候研究計劃的靈活性。哈塞爾曼知名度大增,1972年,哈塞爾曼以海洋專家的身份成為全球大氣研究計劃聯合組織委員會的成員,并參與了后來成為世界氣候研究計劃的準備工作。1974年哈塞爾曼參加了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氣候會議,主持其中一個涉及海洋和氣候的工作組,在隨后的赫爾辛基海洋與氣候會議中擔任會議的共同召集人,這兩次會議為后來在日內瓦的會議上制定世界氣候研究計劃奠定了基礎。
“‘聯合北海波浪計劃’無疑是我參與過的最成功的實驗,發展了相關理論。”哈塞爾曼表示,“我的職業生涯的確非常幸運,假如沒有海對空導彈試驗,跨國海浪研究將困難重重。幸好有德國國防部的資助,我們才得以一年后重新進行實驗。”
半個多世紀以來,哈塞爾曼在科學的征途上從來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他投身流體動力學研究,從理論上解決海浪分量的非線性耦合問題。后逐漸轉向海洋學、氣象學和氣候研究,開發了耦合的氣候經濟模型來確定減緩氣候變化的排放路徑。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他一直在研究量子場論,甚至退休后也沒有閑著。
量子場論是量子力學狹義相對論和經典場論相結合的物理理論,已被廣泛地應用于粒子物理學和凝聚態物理學中。量子場論為描述多粒子系統,尤其是包含粒子產生和湮滅過程的系統,被認為提供了有效的描述框架。哈塞爾曼通過深入研究,大膽指出量子場論中的某些東西基本上是錯誤的,認為問題不在于它可以描述的現象的有限范圍,以某些參數范圍為特征,而是在于基本概念本身,在于否定真實對象的存在。量子場論只捕獲了一半的事實,即波粒二象性問題的波方面。盡管受到質疑和嘲諷,然而哈塞爾曼堅持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堅信“任何試圖提出經典理論的人都在與強大的主流作斗爭”。
哈塞爾曼的研究涉及氣候、海浪和衛星遙感三個典型的領域,真正讓他感興趣的事情是其中那些根本不清楚是否會成功的問題。像對湍流理論或量子現象的研究,沒有一條通往成功解決方案的捷徑。但是哈塞爾曼建議年輕的科學家,如果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天才,那么就先去做一些對社會有用的研究。這能帶來自由,不必面臨不斷取得成果的壓力……

哈塞爾曼很早就開始高度關注人為氣候變化和溫室效應。他提醒說:“在30年到100 年內,根據消耗的化石燃料,我們將面臨非常明顯的氣候變化,應該意識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沒有回頭路的局面。”2021年10月5日,這位老人接受美聯社采訪,在談到全球暖化正對人類和地球構成威脅時,稱寧愿自己沒有得到諾貝爾獎,也不希望有全球暖化。
哈塞爾曼直言,像許多科學家一樣,自己缺乏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經常在溝通中倍感沮喪,因此將一些與媒體、公眾、政策制定者互動的壓力交給了其他人。在身任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所長時,該所的聯合主任哈特穆特·格拉斯爾就幫他分擔了不少的媒體采訪。在哈塞爾曼看來,媒體熱衷于報道人們喜歡讀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應該讀的東西,也就是科學事實。但科學事實有時候又稍顯無聊,尤其像氣候變化這類議題,變化本身就非常緩慢,而媒體卻喜歡提出極端的觀點,而且往往是沒有充分的科學支持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就弄不清楚氣候變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哈塞爾曼對于科普本身還是非常贊同的,認為科學家有義務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成果,而媒體就是最有效的途徑,尤其是對于那些可能會影響社會政策的科學成果,就更應當如此。他分享了一個十分正面的例子:“有一年,我們做了一個量化的研究,證明全球變暖會引起自然界的變化。這很快就讓民眾意識到,氣候變暖是真的,而且已經可以被監測到了。”
1991年,哈塞爾曼60歲生日的時候,人們舉辦了一個生日驚喜座談會。他曾經的許多合作者都突然出現了,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不同領域,讓這位老科學家感動不已:“我如此幸運,能在職業生涯里擁有這么豐富的友誼。”2021年10月25日哈塞爾曼迎來了90歲誕辰,也同樣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