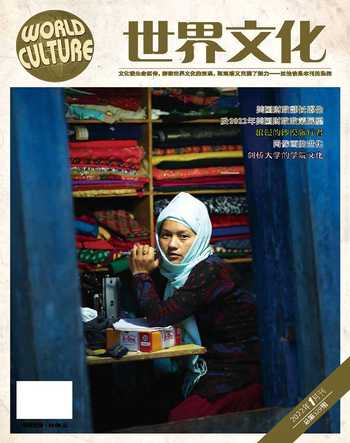從西班牙到希臘、土耳其
賴某深
晚清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國,從閉關鎖國被迫對外開放,從農耕文明被迫面對工業文明。面對西方的挑戰,開始有先行者將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遙遠的國度,開始用審視的眼光看向西方,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奔赴西方試圖探索富國強兵之道。繼岳麓書社出版《走向世界叢書》,收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進的中國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設立專欄,陸續推出系列文章,以紀念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國救民之道、不遺余力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驅。
汗漫客來賦遠游,今宵除夕渡非歐。
兩洲連跨三邦土,半日飛行一葉舟。
千載英雄爭地角,九年飄泊望神州。
明朝五十應知命,空念君親摩白頭。
這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元旦康有為自西班牙乘船渡直布羅陀海峽前往摩納哥游覽時寫的一首感懷詩。康有為次女康同璧所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說這是康有為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除夕所寫,有誤,康有為西班牙游記作了更正,原因是船中沒有日歷,康有為誤以為寫詩那天是除夕,所以詩中應作“今宵元旦渡非歐”。汗漫,形容漫游之遠。唐代陳陶《謫仙吟贈趙道士》:“汗漫東游黃鶴雛,縉云仙子住清都。” 明代張煌言《冬懷》詩之八:“萬里孤槎真汗漫,十年長劍總蹣跚。”舊歷元旦,年近五十,康有為還在歐洲與非洲漂泊。自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流亡海外,至此已有九個年頭,但他人在異國他鄉,心卻記念祖國。這正是康有為異國流亡生活的真實寫照。

岳麓書社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之《康有為西班牙等國游記》,收入《滿的加羅(摩納哥)游記》《西班牙游記》《葡萄牙游記》《瑞士游記》《補奧游記》《匈牙利游記》《歐東阿連五國游記》《希臘游記》,共八種,作于1907年—1908年,少數曾刊于《不忍》雜志,大部分系根據上海博物館藏手稿整理。和其他游記一樣,康有為最為關注的是歐洲各國的歷史文化、宗教紛爭、名勝古跡。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臘是中國人接觸較多的歷史古國,晚清出使日記中有多人寫到,但對于其歷史文化、名勝古跡少有人像康有為考察得那么仔細,記述那么詳盡。至于摩納哥、奧地利、匈牙利、塞耳維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馬其頓,則在康有為之前很少有中國人到過那些國家,更別提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詳盡而全面的游記了,這正是康有為這部游記的價值所在。
《滿的加羅游記》寫摩納哥地理環境“其國土背掛崇山,面臨大海,形勢極似香港,樓閣皆抗山占壑為之,乃無尺寸平原”,“滿的加羅南臨地中海,碧浪紫瀾,萬里卷波,風景佳勝”。滿的加羅雖然不過是彈丸之地,卻非常繁華,堪稱“宮室第一……服飾第一,飲食第一,戲樂第一,女亦第一”。之所以如此,是歐洲貴族將滿的加羅視為銷金窟,在此縱情享樂,“故滿的加羅,以其極小國而得成為極樂國”。
《西班牙游記》記從法國南部進入西班牙,望見比利牛斯山,峰巒競秀,應接不暇:“汽車(此指火車,下同)終日穿山行,巖壑百重,峰巒萬簇,爭奇競秀,青綠未了,山秀嫩已極。嶺顛皆種葡萄,連畦接云,望皆碧綠。”但是火車中設施簡陋,極為寒冷,并且治安秩序差,有的乘客“如盜如丐,惡臭蒸熏”,巡警數人,持槍巡視。后來得知西班牙、葡萄牙盜賊猖獗,常搶劫火車中乘客財物,故車中常有警察持槍執勤,有時警察甚至被盜賊所殺。不禁感慨:
吾行遍歐美數巡,未聞有劫盜事,不意來班而聞此,班與諸歐比鄰,政治皆同,民權立憲無異,而民貧多劫盜,行李多警,人視之畏途乃若此也。
他不理解的是兩國政治制度與歐美無異,為何盜賊特別猖狂,根本原因是民眾貧窮。進而想到:“他日吾國汽車遍地時,未知尚有盜賊否?或亦處處須巡警隨車耶?若班、葡者,不可不引以為戒也。”
來到首都馬德里,印象卻不佳:“街道狹而污”,“客店皆褊小”,坐馬車出行,乞丐“隨車行乞”。仕女服飾打扮遠不如巴黎、倫敦,透著一股“土氣”。唯一值得稱道的是飲食:“惟烹調頗美,能合數味為之,甚似中國。”

在王宮旁邊的博物院,康有為仔細考察了西班牙的兵器發展史:
大概所陳列,彼十五紀多弓弩,十六紀多甲,十七紀多槍,可考其兵器進化之序也……彼十七紀以前,殆無日離甲冑劍戟弓弩之世也。其以精槍橫行,僅三百馀年耳。
反觀中國,明崇禎時炮、清康熙時槍已甚精,“但無競爭之國,偃武修文,銷鋒為器,故不事此,因以不進也”,“吾國文治之至而遂衰也,歐人爭亂之極而遂進也”,競爭導致進步,何獨兵器為然?
在西班牙博物院,康有為見到的珍品美不勝收:有“十三紀至十六紀之古書萬冊,皆金花邊者。有十三紀之可蘭經(指《古蘭經》),有十五紀以列沙伯所讀之經,錦匣”,以上都是手寫本,“蓋近世刻印本書皆不收焉”。還有“十六紀之天文圖,度僅有經緯,甚粗。十四紀之班戰圖,亦甚粗。班古王各像,葡國炮壘圖,印度炮壘圖,皆珍品也”。
其中最珍貴的是與哥倫布有關的歷史文物:
有哥倫布手筆一,存其尋美洲筆記第一卷至第二卷,其第三、四卷則失矣。此為世間瑰寶,與海軍博物院之哥倫布尋美洲地圖并為雙璧矣。
在海軍博物院,珍藏著哥倫布尋美洲船型和其手畫地圖:
第一是哥倫布尋美洲之船型也。船似中國,大眼雞平頭,四帆,凡七船,船燈猶存,恍然如見哥倫布指揮西向之象焉……其手畫地圖,橫長五尺,深二尺許,方針盤線極多。所畫人馬紅綠袍,城郭塔宇無數,多平方者。其畫美洲全形,墨西哥海灣形已甚似,此最奇矣。
在西班牙怎么游覽?康有為的體會是,“西班牙無可游也”,值得游玩的是名勝古跡,“故夫觀班者,新無可見,惟考古跡”。康有為的游覽路線是:“先訪陀厘度(托雷多),次尋迦憐拿大(格拉納達),而先便道過訶度(科爾多瓦)焉,終訪篩非(塞維利亞),而以便道游摩洛哥國、直布羅陀峽。”這一路線,沿途都是歷史文化名城,既能領略西班牙不同時期的建筑風格,又能欣賞摩洛哥人的風情,還能一睹天險直布羅陀海峽的雄偉。
《葡萄牙游記》開篇就談到葡萄牙盜賊多,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交界處“盜賊易匿,故縱橫尤甚,多劫殺汽車之事。雖派兵常駐車中,而停站上下太多,終不能防也”。首都里斯本“臨海依山,形勢頗勝,數山突兀,高下環絡,頗類羅馬”。在里斯本,康有為游覽了議院、動物園、植物園、武庫。在游多連度噫士L拉寺時,看到許多有功于全球之名人石像:“花士哥奸瑪,尋印度者;彼得亞花利士迦巴打,尋巴西者;迦士多路,以水軍攻印度者”,不禁感慨:“葡雖海隅彈丸國,而印度遠東乃其交通,巴西數萬里為其開辟,歐人與我通商,遂為第一最先之國,奄有南美洲,實為泱泱大國”,進而聯想到“假無科倫布(哥倫布)及諸公,吾其能游大地而睹新世界哉?故覽諸像甚拳拳焉”。葡萄牙,這個大西洋岸邊的古國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特別是在15、16世紀之交地理大發現的高潮時期,憑借先進的航海技術和海上實力,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一流強國。葡萄牙航海家們對于人類的文明發展史曾經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逐漸走向衰落。其輝煌和衰落,值得我們深思。
在游覽“散落哥祆祠”時,康有為見廟前開賭票的人非常擁擠,“乃知澳門賭風,固有自來”,首善之區,賭博尚且堂而皇之,何況是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澳門!“而廣東盜賭二風之盛,實為全中國所無”,廣東賭風就是從澳門傳過去的,這些賭徒“賭敗則為盜,故人日多而盜日熾”。廣東賭風盛行,與張之洞開征賭稅亦有關系,“及張之洞督粵,乃公然開賭而收其稅,中國之以賭政府名者,數千年來無之,張之洞遂真得葡人賭衣缽之正傳矣”,“不意中國百物未維新,而開賭先維新也”。譏諷之情,溢于言表。
《瑞士游記》贊美瑞士:“瑞士非國也,歐洲之大公園也;非歐洲之大公園也,實全地球之絕勝樂土也”。

《補奧游記》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在長江以南建立新的國都:“吾國若全開鐵路,宅新京于大江以南,東自上海至蘇州,北界長江,而南襟杭、湖,大野數百里引太湖為池囿,可使數十年間新京居人至四千萬,比今英、法、德、奧、日本全國之人數,令全地人游者震駭之,吾別有《宅新京記》詳之。”
《匈牙利游記》說首都標得卑士(布達佩斯)“有東巴黎之名”,“為歐洲行樂之地焉”,“其浴室有女浴,亦男女同浴,與日本同,全歐只有匈京耳”。匈牙利人“精于音樂,其琵琶最有名”,還說“琵琶入中國自隋之鄭譯使,此為吾北部音樂,匈牙利本自匈奴遷來,然則此樂自吾北部入歐至明也”,即是說琵琶是從中國北方傳入匈牙利的。
《歐東阿連五國游記》寫的是東南歐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馬其頓、羅馬尼亞、土耳其五國。塞爾維亞首都“名悲羅吉辣(貝爾格萊德),以其地之山名也”,“其都即建于悲羅吉辣岡顛”,康有為游遍各國,未見到像塞爾維亞這樣將首都建在山巔上的。其議院與其他各國不同,“行一院制,無上院”。塞爾維亞“以兵立國,常兵四萬五千,戰時兵三十五萬,幾居其國民五之一”。語言“純為斯拉夫語,亦略假用突厥語”。塞爾維亞“民社會甚平等,無高卑等級,無貴族,以真農民之國也”。
布加利亞(保加利亞)“本為突厥屬郡”,至1877年,方擺脫突厥統治,建立國家。“布加利亞未立國前,外人不甚知其名”,直到“千七百六十二年前,亞梳士山之遁僧名啤治者,曾著《布加利亞國史》。后俄人名滑匿連者,旅行巴根半島(巴爾干半島),著《新舊布加利亞》一書。布加利亞國史,自此二本之外無之”。
門的內哥國(馬其頓)位于巴爾干半島西南山中,在保加利亞西南。因其“國小而險遠,故獨未至”,但康有為記錄了所了解的馬其頓情況:“所見其人,獨較高大肥白,似瑞典、德人”,“其人性多忠義,尚勇敢,故各國甚倚重之,多延為兵。其婦女多力,能舉臼,且能任戰,上下山石如飛”,“聞其山水幽勝,巖瀑奇妙,冬夏皆雪,避暑甚佳,亦不亞瑞士”。
羅馬尼亞游記首先介紹國名由來及歷史:“羅馬尼亞人種,自東羅馬來。尼者人種之名,蓋突厥滅君士但丁那部,故東羅馬人北徙居此,故語言風俗多傳故國之舊,而文明程度亦比塞、布與突、希為特高”。在羅馬尼亞游歷時,康有為獲悉光緒帝病重,“為之大憂,飛電北京問訊”,并口占恭祝萬壽詩。
《突厥(土耳其)游記》前有小序,劈頭就闡明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先找出病癥,對癥下藥,并且有的可改,有的則不能改:
病家不能醫方,徒憤激于病劇而妄用刀割,未有不傷死。亂國之人,不學治術,徒憤激于舊弊而妄行革變,未有不危亡其國者也。
所謂立憲:
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蕩然無紀綱、可人人平等自由也。
改革一定要從本國的歷史、風俗、國情出發,循序漸進:
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太去甚,以漸行之,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
他認為土耳其立憲失敗的原因是該國青年黨之徒,長期受法國思想的熏陶,只知破壞而沒有實際政治經驗,“徒艷炫歐美之俗,而未細審歷史、風俗之宜”。立憲之后,一朝廢除舊有的法律、制度二百余個,固然非常痛快,但舊制盡去,新的制度未及時建立,國人難免手足無措。青年黨掌權之后,壓制比君主專制時更甚,局勢嚴重不堪設想:
突以大亂無寧,生民涂炭,國人既厭惡之,而舊制不可得復,新政又不能施,爭亂,召仇敵不怠,只有待亡而已。
封建的中國與土耳其政治制度相同,人民文明程度亦相當,康有為擔心實行立憲也會導致天下大亂,甚至有亡國的危險。這段文字寫于1908年。康有為政治觀點以保守著稱,其思想是真理與謬誤并存,看看辛亥革命之后的社會現實,不能不嘆服康有為的先見之明。
土耳其本來是封建專制國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廿九日,忽下詔“復行立憲法”,康有為正好這天來到君士坦丁堡,親眼看到了土耳其革命,看到了人民載歌載舞的歡呼情景。他介紹土耳其本來在光緒四年被俄戰敗后,宰相阿士文曾行立憲。但后來被“突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廢除。此時卻是“民噪三日,立憲即定”。先是軍官呢詩賓“登山而盟,誓請立憲”,“突主怒,派衛兵八千人討之”,“則此八千人同時兵變”;后調衛兵二萬人往討,“已而衛兵二萬人,同時電奏,請行立憲、開國會”;又調精兵二十萬征之,“皆同時電奏行立憲開國會”,“突主乃彷徨大恐,召諸大將而問其故,皆叩頭曰:萬國皆行立憲,惟突厥立而后廢,故民積怨。今者全國兵心盡變,臣等不知死所,臣等無他術,惟陛下鑒于法路易十六、英查理第一之禍,決自圣心。”“突主無語”,又召諸大臣、宦官首領、妃嬪問之,回答與諸大將如出一轍。“突主無語垂淚,乃援筆自作詔書,宣立國會”,于是“立憲之事,三日而成,國會之開,三日而舉,自大地萬國,無如是之速且易者”。差不多與此同時,清朝也掀起了立憲運動。其大背景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以君主立憲小國戰勝俄國那樣一個專制大國,給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動。朝野上下普遍將這場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體聯系在一起,認為日本以立憲而勝,俄國以專制而敗,“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非小國能戰勝于大國,實立憲能戰勝于專制”。于是,不數月間,立憲之議遍于全國。因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1882年)曾派員赴歐洲考察憲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1906年,清廷頒發《宣示預備立憲諭》,“預備立憲”由此而來。1908年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23條,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這激起了人民的義憤,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晚清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其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土耳其立憲與清末立憲有無關系,或相互影響?兩國立憲背景和失敗的根本原因何在?似乎還少有人進行比較研究。
康有為寫突厥(土耳其)首都君士但丁那部(指君士坦丁堡。如今已遷至安卡拉)“遍大地中控扼兩海(指黑海、地中海)之口,綰彀兩洲(指歐洲、亞洲)之地,以為都會者,亦惟此一都”,“就一城論雄偉,亦當為大地冠焉”,“突京形勝風景,皆甲全球”。但是“突京之污穢破壞,實為全歐所無”:糞便隨意棄于門外路上,到處都有野狗,行乞者眾多,道路坑洼不平。
在土耳其首都,有英、俄、德、法、意、奧六大國公使館,由于土耳其積貧積弱,“六公使在突,有非常大權,尊嚴異常”,聯想到清朝遭受西方列強欺壓,康有為“望此公館,回首燕京,真所謂同病相憐者矣!”
康有為還注意到,土耳其與清朝有一相同之處,就是宮中皆用閹人,不同的是土耳其不用本國人,而用非洲黑人充當,康有為評價說這種做法“不殘同種,猶勝我國”。對于這種丑陋現象,康有為斥責為“國恥”“怪異不祥之事”。
土耳其有多腐敗?“官及辯護士貪甚,官得賄廿五鎊,即殺人者亦放之。其外國人有罪不敢問,大罪拘之,則領事來爭領去,即訊得實,僅放逐還本國。所見獄卒,乃用奧人,而不敢用本國人”。
《希臘游記》開頭就說:“希臘為歐洲文明之祖,向慕之久,欲游數矣”,但到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七日才成行。他認為“大地文明之國,惟吾中華、印度、巴比倫、亞述、波斯、埃及與希臘矣”。而希臘之文明,又“以雅典為盛,國會、議院、立憲、民權之制,雅典實為大地之先河”,“即吾中國最為數千年獨立文明國,而今者立憲、國會、議院之制,石室、公園、浴場、戲館、刻像、音樂之事,不能不用歐制,即亦不能不溯遠祖于雅典”。但是康有為認為共和、民權、民主并非適用于所有國家,“共和民權,只易行于小國,故盧梭謂共和政宜行于二萬人之國”,“若吾中國,自黃帝時即已征服萬國而統一之,泱泱大陸,比于全歐。假令立民主乎,則道路不通,紀綱不立,中國反不能強、不能安,而為人所弱,或分亂成多國久矣”,在康有為看來,共和也好,民主也罷,只可行之于小國,大國行之,不僅不能使國家強盛,反而會導致國力衰落,甚至會引發內亂或分裂!
游記的最后,康有為抒發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然則古文明國地至大,人至多,傳至古,文字、種類、宮室一切皆不少變,而能保存者,橫覽大地,惟有我耳。”在《游希臘畢感賦》中他呼吁:“陸國我最大,愿起神州魂”。
康有為寫這些游記的目的,在《意大利游記》自序中說得很明白,是想通過對西方的實地考察,為中國尋找解決問題的藥方,而他就是嘗遍百草的神農。因此這些游記雖名為游記,實則是政論,從中可看出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的政治思想。而康有為當年對西方文明的反思,對中國歷史、前途命運的思考,“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游外國地”的研究方法,“陸國我最大,愿起神州魂”的殷切期望,依然值得我們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