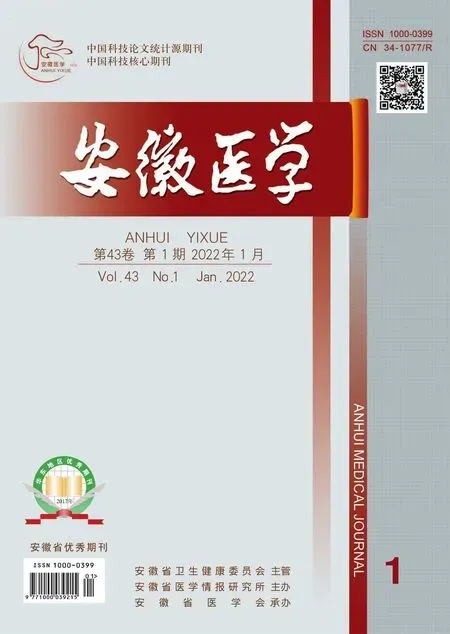腦電聯合肌電生物反饋治療對痙攣型腦癱兒童腦功能及其上下肢運動功能的影響
陳曉霞 楊 李 唐久來
痙攣型腦癱是臨床最常見的腦癱類型,約占腦癱的65%[1],以椎體系受損為主,以腓腸肌肌張力增高、踝關節背屈困難、站立與步行功能異常為主要表現[2-3]。目前,臨床尚無腦癱的特效治療藥物,主要通過長期性的綜合康復治療,效果不盡人意[4]。有研究[5-6]表明,痙攣型腦癱患兒運動功能異常與腦電異常有關。肌電生物反饋治療是借助表面肌電接收設備,使患者恢復對自身運動功能的控制,從而起到治療作用,該方法廣泛運用于痙攣型腦癱康復中,療效亦得到了證實[7]。然而肌電生物反饋對痙攣型腦癱患兒腦功能的影響并不明顯。腦電生物反饋治療又稱為神經反饋、腦反饋治療,以腦電生物反饋治療儀為手段,利用神經電生理技術,有針對性地改善腦電異常,該方法可有效改善痙攣型腦癱患兒腦功能[8],但其對于患兒運功功能影響的研究卻鮮有研究。因此,本文通過隨機對照研究,探討腦電與肌電生物反饋聯合治療對痙攣型腦癱患兒的腦電功率、上下肢運動功能的影響,以期為該類患兒的臨床康復治療方案的選擇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9月至2019年8月安徽醫科大學附屬巢湖醫院收治的痙攣型腦癱患兒96例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4組:對照組、肌電組、腦電組與聯合組,各24例。納入標準:①所有患兒均符合《中國腦性癱瘓康復指南(2015)》[9]中腦癱的診斷標準,分型符合《實用小兒腦性癱瘓康復治療技術》[10]中痙攣型分型標準;②年齡6~10歲;③患兒粗大運動功能分級(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為2級;④肌張力Ashworth分級為2~3級;無視力與聽力障礙;能獨坐或借助坐姿矯正椅,能配合完成生物反饋訓練;⑤上肢抬離桌面15 cm,腕伸展<20°;⑥患兒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可配合完成相關隨訪和檢查,且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合并重度認知障礙者;合并精神類疾病、癲癇或心臟病;治療前6個月內下肢接受過肉毒素注射;接受過神經選擇性切斷術或矯形外科手術;正在使用抗痙攣藥物。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11]要求。4組患兒年齡、性別、病程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4組患兒一般資料比較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患兒入院后根據《實用小兒腦性癱瘓康復治療技術》[10]進行常規康復訓練,主要予以患兒實施Vojta療法、Bobath療法進行康復治療;同時予以患兒進行認知行為訓練進行康復治療,一天一次,一次治療40 min,一周治療5次,4周為一個療程,共治療12周,康復間歇期間保持患兒的日常基本運動需求。Vojta療法和Bobath療法[12]:主要通過抑制患兒非對稱姿勢如角弓反張、曲背、拇指內收、前臂旋前、下肢硬直等異常的姿勢與運動,從而促進正確運動。①Vojta療法包括反射性腹爬、反復性翻身。②Bobath療法以抑制異常運動和促進正常運動為原則,控制運動的關鍵點,涵蓋頸部協調、上半身協調、坐位訓練、爬跪訓練。認知行為訓練[13]包括:注意力、記憶力、理解能力、判斷力、思維能力訓練。
1.2.2 腦電組 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給予腦電生物反饋治療。使用Infiniti系列多參數生物反饋儀(南京偉思醫療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規格:Infiniti4000A),腦電生物反饋治療采用EEG模式,采樣率為256 Hz/s。操作方法:用磨砂膏摩擦頭皮和耳垂去除皮膚角質層,按照國際10-20系統標準電極放置方法安裝盤狀電極,耳參考電極夾在一側耳垂位置,地電極夾在另一側耳垂,以增強β波、抑制θ波為主要的治療方案,并以增強SMR波、減少α波為輔助治療方案,對患兒進行一對一的視覺追蹤訓練、注意力維持訓練、辨別力訓練、短時記憶力訓練與實時任務訓練。
1.2.3 肌電組 在對照組的基礎上給予肌電生物反饋治療。儀器同腦電生物反饋,采用EMG模式。操作方法:清潔欲放置電極處皮膚后,將刺激電極置于雙下肢脛前肌上,另外取記錄電極置于下肢適當位置,地電極貼于下肢肌腹位置,3塊電極互不接觸,電刺激參數為:波形為雙向方波,頻率45~50 Hz,脈沖寬度200 μs,刺激時間12 s,間歇4 s,刺激強度為25~38 mA。肌電生物反饋首次治療前,治療師向患兒講解與示范指定動作與注意事項,給患兒被動踝背屈,致使患兒關注儀器顯示屏上線變化,最后囑患兒主動活動踝部,鼓勵患兒努力提高脛前肌的肌電信號,將最高值作為初始數據記錄下來,在下一次的治療中以該值作為基點,當患兒通過自身運動超過該基線時,給予獎勵性刺激,然后儀器會自動調高閾值,若患兒多次均難以達到基線,儀器會調低閾值,以使得患兒能努力達標;同時,治療師應根據患兒耐受情況調整頻率、刺激強度和閾值大小。治療時間每天1次,每次20 min,每周治療5天。
1.2.4 聯合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腦電+肌電生物反饋治療,在進行腦電生物反饋的當天進行肌電生物反饋治療。各組療程均為3個月。
1.2.5 隨訪 對研究組人員進行專業統一培訓,通過主動復診或者電話通知復查面對面獲得數據方式進行隨訪,分別于治療前、完成治療療程后(治療3個月后)與完成治療療程后1年(治療后1年)對患兒進行各量表評估與腦電功率收集,隨訪截止至2021年10月。由接受過培訓人員對患兒進行各個量表評估,并進行電功率分析檢測。
1.3 觀察指標 收集并比較4組患者治療前、治療3 個月及治療后1年時的粗大運動功能、精細運動功能以及患者腦電功率。①粗大運動功能采用粗大運動功能測試量表(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GMFM)評價。GMFM評分[14]分值為0~100分,包括5個能區,各能區原始分占各能區總分的百分比之和乘以100再除以5計為總分,得分越高,表示粗大運動功能越好。②精細運動功能采用精細運動功能測試量表(finemotor function measure,FMFM)評價。FMFM評分[14]分值為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相應功能越好。③腦電功率:記錄腦電生物反饋儀分析得出的θ波、β波、θ/β波、α波、SMR波與α/SMR波值。

2 結果
2.1 運動功能評分 各組FMFM評分和GMFM評分分組效應、時間效應以及分組和時間交互效應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t2和t3時間點4組FMFM、GMFM評分均增加(P<0.05),4組t3與t2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t2和t3對照組FMFM、GMFM評分均低于其余3組,t2和t3聯合組評分均高于腦電阻和肌電組(P<0.05);t2和t3腦電阻和腦電阻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 腦電功率的比較 各組θ波分組、時間與分組和時間交互效應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β波、θ/β波值、α波、SMR波分組、時間與分組和時間效應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α波/SMR波值分組與時間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分組和時間交互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組t2、t3θ波均低于t1(P<0.05);t2、t3腦電組與聯合組的θ/β波值、α波與α/SMR波值明顯降低(P<0.05),β波與SMR波升高(P<0.05);與腦電組相比,治療后聯合組θ/β波值、α波與α/SMR波值降幅更大,而β波與SMR波升幅更大(P<0.05);各組組內t3與t2比較,各腦電波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 討論
引起腦癱患兒運動障礙的病變部位主要在腦部,既往多項研究表明腦癱患兒的腦電波異常率達到40%~90%,其中又屬痙攣型腦癱患兒異常率最高,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腦電異常程度還會有所增高[15-16]。常規康復訓練通常為Bobath療法等,是一種通過抑制患兒異常姿勢而促進正確動作的康復方法,但效果并不盡人意[17]。研究[18]表示,肌電與腦電生物反饋聯合常規康復訓練均對康復療效有加成作用。然而,肌電生物反饋多用于恢復患兒肢體運動功能恢復;腦電生物反饋對患兒則側重于對腦功能的影響。因此,本文探討腦電結合肌電生物反饋治療對痙攣型腦癱兒童的腦功能與上下肢運動功能的影響,旨為探尋治療小兒痙攣型腦癱更優方案,為該類患兒的臨床康復治療方案的選擇提供參考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各組在治療后,腦功能與上下肢運動均有明顯改善,而肌電組、腦電阻與聯合組改善程度均優于對照組,聯合組效果優于單獨采用肌電組與腦電阻,腦電阻與肌電組效果并無明顯差異。由此可見,常規康復訓練與肌電、腦電生物反饋對痙攣型腦癱患兒療效具有加成作用,與研究[18]結果一致;同時肌電與腦電生物反饋之間,效果亦有加成作用。本研究中予以患者Vojia療法、Bobath療法以及認知行為訓練進行康復治療,可糾正患兒異常姿勢同時通過認知行為訓練改善患兒的思維與判斷能力,從而有效改善患兒的肢體與腦功能恢復。肌電生物反饋儀可自動收集患兒肌電信號,設置動態的閾值,可通過刺激幫助患兒完成最大限度的運動,調動患兒使用更大的力量去完成更高的目標,最大限度激發患兒肌肉潛在的運動能力,從而促進患兒上下肢運動功能恢復[19-20]。而聯合組在使用肌電生物反饋訓練的同時,采用腦電生物反饋改善了腦電異常情況,在改善腦功能同時實現了患者主動訓練意識。
同時,各組治療后θ波較治療前均有所降低;治療后腦電組與聯合組的θ/β波值、α波與α/SMR波值亦明顯降低,而β波與SMR波升高。研究結果提示,腦電生物反饋具有改善腦功能作用。人在安靜、放松、清醒與閉目的時候會出現α波,在睜眼與思考α波會消失,而困倦時常出現θ波,是中樞神經受抑制的表現。神經系統抑制功能未發育成熟或發育遲緩時腦電波會出現θ波活動增強,而患者常表現為行為異常興奮,自制力差,注意力難以集中,當大腦處于興奮狀態時,β波頻率增高,而當患者集中注意力而放松肌肉時SMR波頻率增高。腦電生物反饋即利用這個原理,抑制部分頻段腦電波,同時增強相應頻段腦電波,從而達到訓練患兒注意力,調整腦功能的目的。Alves-Pinto等學者[21]亦通過試驗研究證明采用腦電生物反饋訓練可以調整腦電波的異常表達,從而改善腦功能。而與腦電組相比,聯合組治療后θ/β波值、α波與α/SMR波值降幅更大,而β波與SMR波升幅更大,表示在增加肌電反饋生物治療鍛煉了運動功能的同時,腦功能亦得到了相應的鍛煉,間接地改善了腦電異常狀態。可能采用腦電生物反饋的同時增加肌電,同時采用肌電生物反饋訓練,收集患兒主動收縮肌肉時產生的弱肌電信號,并轉換為視、聽覺信號反饋給患兒,使患兒的注意力集中、肌肉處于運動狀態,因此肌電從側面輔助腦電生物反饋對腦功能的改善作用。
綜上所述,對于痙攣型腦癱兒童,在常規康復訓練的基礎上給予腦電聯合肌電生物反饋治療能顯著改善患兒腦功能,并有助于提高上下肢運動功能。染本研究中可能存在樣本量少造成結果存在偏倚的局限性,未來將通過更多的臨床病例來完成對本研究結論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