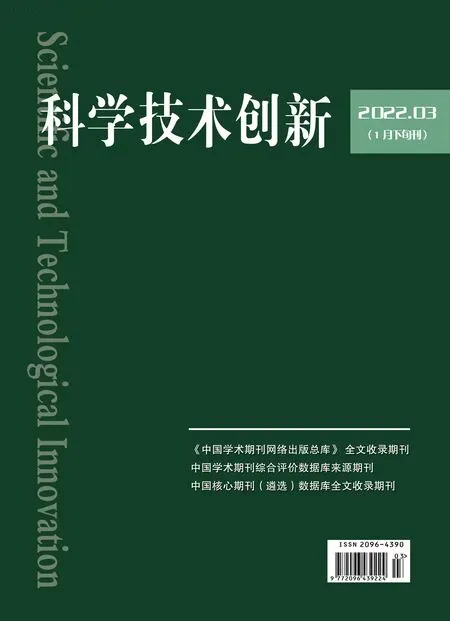基于海面高度和流速場的渦旋探測方法對比
甘瀅暉
(大連海洋大學 海洋科技與環境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
1 概述
中尺度渦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海洋現象,它攜帶巨大動能,占據了大、中尺度海流上層動能的80%以上[1],且具有高動態性,在移動和旋轉過程中,下層冷水將營養物質帶到上層,促進浮游生物的發育與繁殖,實現海洋中各營養級的資源重新分配。由此可見,中尺度渦對海洋中的動力過程、能量分配和物質運輸起著重要作用,了解當前渦流模式、研究渦旋對海洋生化過程的響應機制對于海洋動態預報、海洋與大氣相互作用和海洋生態系統可持續性至關重要。中尺度渦的形成機制主要是大尺度環流、海流與海底地形相互作用的不穩定性以及風的直接強迫,通過測量海流圍繞的海表高度異常可以觀測這種現象。
海洋渦旋的研究強烈依賴于實際觀測提供的真實海洋渦旋的物理特征,以及渦旋產生、發展、消亡過程和水動力條件。由于渦旋產生地點和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尺度較小、以及海洋現場觀測費用昂貴等因素,使得渦旋的現場觀測資料有限[2]。現階段,海洋遙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人類實現對海洋的全面認識,在同一時間獲取的大范圍海洋要素信息,被廣泛應用于中尺度渦旋提取的研究中[3],目前,國內外中尺度渦遙感診斷應用較廣的包括海洋高度數據、海表溫度數據和水色信息等較高分辨率數據。海洋高度計可獲取海洋高度數據,估算海洋風場、流場和有效波高等信息,用于研究海洋大尺度環流、中尺度渦旋和潮汐等海洋過程及現象。我們利用法國國家空間研究中心衛星海洋學存檔數據中心提供的基于SSH 算法的中尺度渦數據集與本研究采用的VG 算法得到的渦旋進行對比,探究兩種算法的優異程度,針對不同的渦旋提取需求提供幫助。
2 算法對比
法國國家空間研究中心(CNES)公開發布的中尺度渦軌跡追蹤產品采用的是基于海表高度(Sea Surface Height,SSH)的渦旋識別算法,該產品對歷年數據進行分析建庫,內容包括中尺度渦旋的半徑、位置、極性(氣旋或反氣旋)、渦動能等特征參數。我們使用該產品與基于速度矢量幾何(Vector Geometry ,VG)算法得到的結果進行對比。其中,產品所用的高度計融合產品是由哥白尼海洋環境監測中心(https://marine.copernicus.eu)發布的絕對動力高度(Absolute Dynamic Topographies,ADT),空間分辨率為0.25°×0.25°,時間分辨率為1 天,研究所選的空間范圍為30°~40° N 東 經 140° E~180° , 時 間 范 圍 為2020/01/01~2020/12/31。
中尺度產品采用高度計觀測得到的絕對動力高度進行渦旋識別與追蹤,即基于ADT 高度計產品提供的地轉流異常數據,VG 算法采用基于海面高度異常SLA 數據,該研究利用中尺度產品和VG 算法對上述海域進行渦旋識別與提取(設置a=2 和b=1),然后將兩種結果對比分析。
VG 算法由Nencioli 和董昌明[3]等提出,原理是將渦旋直觀上定義為速度矢量繞著一個中心點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的區域。VG 法利用以下四個約束條件判定渦旋中心:
(1)沿渦旋中心點東西方向,速度分量v 在遠離中心點的兩側數值符號相反,大小隨著與中心點的距離增大而逐漸增加。

圖1 VG 法第一約束條件示意圖[3]
(2)沿渦旋中心點南北方向,速度分類u 在遠離中心點的兩側數值符號相反,大小隨著與中心點的距離增大而逐漸增加。(圖2)

圖2 VG 法第二約束條件示意圖[3]
(3)在選定區域內找到速度最小值點近似為渦旋中心。(圖3)

圖3 VG 法第三約束條件示意圖[3]
(4)在近似渦旋中心點附近,速度矢量的旋轉方向必須一致,即兩個相鄰的速度矢量方向必須位于同一象限或相鄰的兩個象限。(圖4)

圖4 VG 法第四約束條件示意圖[3]
在上述四個約束條件中,需要確定兩個參數a 和b,參數a 用于確定有多少個網格點用于檢驗沿著東西方向速度v分量的增加情況(第一約束條件);同上,用于確定有多少個網格點用于檢驗沿著南北方向速度u 分量的增加情況(第二約束條件);此外,用于確定檢驗速度矢量方向變化的繞渦旋中心的四條邊界線(第四約束條件)。參數b 用于確定局地最小速度的區域范圍(第三約束條件)。算法中參數a 和b 的取值是彈性的,以便用來設定渦旋檢測的最小尺度,并使算法可適用于不同分辨率的網格。需要注意的是,a 和b 的大小為網格點的個數,a 的取值必須大于等于2,b 的取值必須大于等于1 且小于等于a,同樣的a 和b 能夠檢測的最小尺度渦旋與所用數據集的分辨率有關。a 和b 的取值越小,越能識別更小尺度的渦旋。該算法雖然能較好識別中尺度渦的位置,但用于渦心搜索的閾值選取使識別過程更加復雜。
中尺度渦產品的提取步驟包括對ADT 濾波,目的是去除大尺度變化,突出中尺度特征。之后,以等值線1cm 的間隔識別ADT 閉合等值線。將符合條件的閉合等值線定義為渦旋,計算渦旋中心、渦旋形狀和渦旋半徑并進行追蹤。其中,SSH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流線大致貼合海表高度異常的假設,依據判定法則提取渦旋,大大降低了計算量。在算法提取過程中,為了消除閾值影響,該方法對氣旋渦和反氣旋渦分別查找,海表高度字段在-100-100cm 的“跟蹤區域”內以1cm 為步長識別ADT 閉合輪廓線,并在每隔一段時間對閉合輪廓線進行識別和分析,如果特征符合判定標準,就可以確定渦流。該算法的判定標準是:a.定義誤差為偏離擬合圓的面積和與該圓面積的比值,要求誤差小于55%;b.渦旋包含的像素個數大于8 小于1000;c.氣旋渦中包含的SLA 像素均低于當前SLA 像素值間隔,反氣旋渦中中包含的SLA像素均高于當前SLA 像素值間隔;d.氣旋渦中的SLA 最小值不能超過一個,反氣旋渦內的局部極大值不能超過一個;e.振幅的范圍大于1 小于150cm。接下來,定義渦流的中心為與最大速度輪廓最符合的圓心,再根據定義計算出相應的半徑。該方法簡單,不受閾值影響,噪聲影響也較小。但是,該方法依賴于檢驗標準的其他閾值(如面積和水平尺度)確定渦邊界,難以準確識別渦核,可能產生多渦結構。同時,受背景流影響,該算法可能夸大渦流邊界,且計算過程隨數據分辨率的提高而變大。
根據判定法則可以看出兩種算法的區別,基于SSH 算法識別渦旋的原理是基于渦旋的渦心存在SLA 的局部唯一極值,而VG 算法是基于渦旋中心流線方向相反。
3 結果分析
我們分別統計了VG 算法和SSH 算法在同一天檢測到的渦旋,圖5 為VG 算法在某一天識別提取的渦旋,圖6 為同一天SSH 算法識別得到的渦旋,藍色代表氣旋渦,紅色代表反氣旋渦。流場算法識別得到反氣旋渦17 個,氣旋渦20個;海表高度的算法識別得到的反氣旋渦29 個,氣旋渦32個。

圖5 VG 算法識別提取的一天的渦旋

圖6 SSH 算法識別提取的一天的渦旋(圓圈大小正比于渦旋半徑)
造成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SSH 算法對絕對動力高度進行濾波和插值等處理,通過識別間隔為1cm 的閉合等值線探測渦旋,能夠識別出振幅1~150cm 的渦旋;VG 算法基于高度計產品提供的原始海表地轉流異常,分辨率為0.25°,沒有進行插值處理,參數a 和b 的設置決定了無法識別更小尺度的渦旋,因此數量上相對于中尺度渦產品更少。
利用上述的方法,我們對此海域2020 年1 年內的兩者方法識別獲得的渦旋數量進行了對比分析。對比結果如圖7所示,其中,上圖為氣旋渦數量,下圖為反氣旋渦數量。藍色代表VG 算法識別得到的渦旋數量,紅色為SSH 算法識別得到的渦旋數量,綠色為SSH 算法中等效半徑大于50km 的渦旋數量。通過對比同一年的算法識別數量曲線可以看出,去除半徑大于50km 的渦旋內,兩種算法得到的渦旋數量接近相同,但是SSH 算法得到的數量始終略大于VG 算法得到的結果。通過對比不同極性渦旋得到的數量曲線可以看出,VG算法在反氣旋渦的識別中精度更高。在氣旋渦的識別過程中,即使去除小尺度渦旋的差距,VG 算法識別的渦旋數量始終與SSH 算法存在一定差距。

圖7 兩種算法識別的一年的渦旋
同時,我們統計了兩種方法得到的每日識別渦旋的平均個數,如表1 所示。SSH 算法能夠識別小渦旋,個數明顯多于VG 算法,剔除半徑小于50 km 的渦旋后,兩者數量相近,VG算法結果略少。與圖3.3 相對應的,氣旋渦的VG 算法得到的日均個數與剔除后SSH 算法得到的結果之差大于反氣旋渦的統計結果。

表1 兩種方法2020 年每日識別渦旋的平均個數
4 結論
通過對比兩種識別算法,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4.1 SSH 算法的原理是基于渦旋的渦心存在SLA 的局部唯一極值,而VG 算法是基于渦心流線方向相反。
4.2 與VG 算法相比,SSH 算法可以識別到更多小渦旋,這可能是因為VG 算法需要設置參數a 和b,SSH 算法不受閾值的限制。
4.3 剔除相對小的渦旋之后,兩種算法得到的渦旋個數無較大差別,其中反氣旋渦的提取結果更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