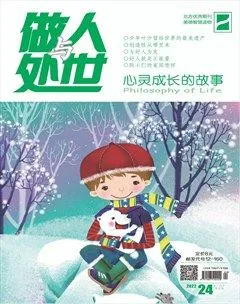祖國在我心中
水刃木

葉輝曾兩度登上中央電視臺,他展示的“航天精度”令人折服。
從技校畢業后,葉輝被分配到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磨組。上班的第一天,師父仔細打量著他的手掌,觀察了好一會兒。葉輝這才知道,研磨這個活兒跟別的不一樣。此時,車間的研磨工種正面臨著“失傳”危機,研磨是一項高精密加工技術手段,打磨全靠兩只手的感覺,需要幾年的練習和琢磨,枯燥、累人、上手慢。葉輝的師父已經退休返聘5年了,體力和精力大不如從前,誰來接班成了他的一塊“心病”。
剛開始,葉輝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信心滿滿。然而,每天就是磨廢鐵塊,既枯燥又累人,還沒有一點兒成就感。一個月后,他的好奇心被單調重復的動作消磨殆盡,變得心浮氣躁,鑄鐵平面被他磨得凹凸不平、慘不忍睹。師父看出了葉輝有些倦怠,說道:“要不你就放棄吧,這個精度你干不了。”其他工種上手一年就能獨立工作。但是,研磨這個工種靠的是肌肉記憶,需要練習好幾年,并且規定沒出徒前,不能研磨成品零件。“你越說我干不了,我就越要做給你看。”葉輝的較真勁兒被激發了出來,又回到了工作臺前。
經過無數次的練習、無數次的研磨,葉輝逐漸找到了“感覺”。“老頭兒知道我是什么樣的人,所以總是給我設置難題,說我不行。”葉輝喜歡管師父叫“老頭兒”。其實,葉輝知道,他是師父的“關門弟子”,師父對他很嚴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因此他必須勤學苦練,絕不能讓師父失望。5年后的一天,葉輝像往常一樣來到工作室,準備磨報廢的零件。“你可以修理這批0.5微米的量塊任務了。”師父拿給了他一套需要研磨的零件,這意味著葉輝終于出師了。
沒想到,正當葉輝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時,他卻遭遇一場意外事故 “右手手掌貫穿,三根手指筋斷,僅剩拇指和食指可以活動”。醫生的話讓葉輝感到絕望:“以后右手可能無法像普通人那樣正常伸展打開,更別說工作了。”師父聽聞后趕到醫院,鼓勵葉輝道:“你要是放棄了,這一脈就斷了!”作為第一代研磨師,師父等了40年才培養出了一個優秀的傳承人。師傅的話讓葉輝心潮難平。出院后,葉輝用那雙被醫生判定為“殘廢”的手,開始了新的研磨歷程。相伴了5年的平臺就是葉輝最好的理療機,他開始強制自己右手全開,按壓平臺,重復那套熟悉了5年的動作。“疼啊,抽筋一般地疼。磨幾分鐘,就一身汗。”就這樣,經過持續3個月的自我復健理療,他的手掌從一開始只能勉強半開到后來能夠全開,再到右手恢復正常伸展,連醫生都說這是個奇跡。
康復后的葉輝對研磨有了更深的感悟,研磨精度再次提升。零件哪塊兒厚了或是薄了,葉輝一摸就能清楚地感受到。經過年復一年的磨礪,葉輝已經突破最高檔的研磨精度,加工精度早已超出了機器的測量范圍。幾年前,有一個零件精度要求極高,國內沒有研磨師敢接這個工作。國外有人嘲諷說:“中國永遠也做不出這樣精度的零件。”葉輝接下這活,他說:“說我不行可以,說中國不行,那不成!”加工好的零件被送到國外進行測量,精度等級比要求的還要高。最令葉輝自豪的是,2015年的大閱兵上,在天安門前接受檢閱的導彈方陣的武器裝備里,其中就有一些裝備關鍵零部件是葉輝參與研制與生產的。他說:“一切都是因為祖國在我心中!”
在葉輝看來,研磨量塊就是打磨人生,零件有瑕疵,猶如人生有缺陷,只有經過一遍遍打磨,才能打造精品、創造精彩。每天,他都準時來到研磨恒溫室里,20多年都在這里度過,他也從一個對精度毫無感覺的愣頭青,變成了手一伸就能探知幾十納米精度的研磨專家。經過20年的摸爬滾打,葉輝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一線工人,成長為行業內的“航天研磨師”。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