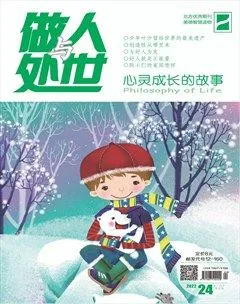愛在祖國的花園里永不凋謝
潘彩霞

歲月鎖不住愛的花枝,時光催開情的種子
1944年,馮理達考入戰時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醫學院。她是愛國將領馮玉祥之女,報國情懷流淌在血液里,當成都五所大學聯合起來成立抗日救國合唱團時,馮理達擔任領唱。而另一位領唱是華西大學的羅元錚。一個笑顏如花,一個英俊儒雅,對音樂的共同愛好成為月老的紅線。
后來,馮理達隨同父母流亡美國。從華西大學畢業后,羅元錚去美國與馮理達團聚。
這年中秋節,馮玉祥夫婦準備去美國東部城市推動華僑的反內戰活動,馮理達和羅元錚隨行。一路上,紅日高照,秋色如畫,馮玉祥夫婦提議:“你們今天結婚吧!”說辦就辦,讓一位路人幫忙照相,他們就在路邊拍攝了一張結婚照。沒有戒指,沒有婚紗,但馮理達與羅元錚十指緊扣、笑容甜蜜。仿佛一切都是天意,馮玉祥打開地圖后發現,附近居然有一個叫“愛鎖”的小鎮,當晚他們便投宿在那里。那天,馮玉祥為新婚夫婦撰寫了一副對聯:“民主新伴侶,自由兩先鋒。”多年后,馮理達回憶,唯一的遺憾是:“當時我不知道這天會結婚,不然就會穿一條漂亮的裙子了。”
1948年,馮玉祥受邀回國,馮理達和羅元錚也放棄了國外的優厚條件,決心報效祖國。在回國的輪船上,羅元錚引用古詩送給馮理達:“皚若山上雪,皎若云間月。直若朱絲繩,清若玉壺冰。”在他心中,他們的愛就像山上的雪一般純潔,就如云間的月一樣皎潔。難以預料的是,在船上,一場火災突然而至,馮理達永遠地失去了父親。
回國后,馮理達和羅元錚雙雙被派往蘇聯,一個學醫,一個在經濟系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后,羅元錚先行回國,激情澎湃地投入建設中。他急切地盼望妻子歸來,特意寄給她一首《盼歸》:“故園蘭竹正逢春,中南海里會群英。北國天寒地又凍,盼你載譽早回程。”愛人的呼喚帶來不竭的動力,馮理達在蘇聯創下佳績。她采用針灸和中藥、西醫相結合的方法,使得列寧格勒市一舉消滅了白喉病,一時引起轟動。她的論文破格被提升為博士論文。
學業已成,面對導師提出的優渥條件,馮理達婉拒了:“我是祖國派來的,我要用學到的知識報效我的祖國。”回國后,她投入流行病學的研究,組織籌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消毒研究室。工作繁忙,可愛的家庭成了她最深的眷戀,每晚的燈光下,她織毛衣,羅元錚則給兒子講古詩詞,那幸福濃得化不開。
1973年,馮理達被調入海軍總醫院,成為一名軍人。那年,她已經48歲了,想要把失去的時光全補回來,她開始在醫院創建第一個免疫學研究中心。沒資金、沒設備、沒資料,她是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自己的工資搭進去了,出國講學的報酬她全部用來添置設備。哪里有傳染病,她就冒著感染的風險奔赴哪里。“我只想專心專意做好一件事,那就是讓中國免疫學有利于科學進步,有利于國家建設,有利于人類健康。”馮理達為免疫事業殫精竭慮,羅元錚成了她最堅強的后盾,他包攬了全部家務活兒,不管她回來多晚,他都會等她一起吃飯。難得的閑暇,馮理達就在家畫畫,詩詞造詣頗深的羅元錚則負責配詩題字,他們一起彈琴唱歌,一起探討經濟問題。簡約的房間里,愛和美妙的音符一起緩緩流淌。
幾十年來,他們琴瑟和鳴、攜手共進。在金婚紀念日上,羅元錚風趣地總結道:“我們之所以恩愛如初,一是因為平等,當我們意見一致時,絕對聽我的,當意見分歧時,絕對聽她的;二是因為民主,小事聽她的,大事聽我的,可我們家從來沒有過大事。”從熱血青年到華發暗生,浪漫從未遠離,韶華從未逝去,七十多歲時,馮理達仍然自稱“小姑娘”,她親熱地喊羅元錚為“我的男朋友”,就連上街,他們也一定要手拉手。
也許是上天嫉妒了,2003年,一同走過半個多世紀后,羅元錚突發心臟病去世。臨終前,他對兒子交代說:“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母親,你要好好照顧她。”巨大的打擊之下,馮理達連續幾天把自己關在屋里。每晚,她都會對著他的相片說說話;他坐過的搖椅上擺放著他生前最愛看的一本書,每天早晨,她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他翻開新的一頁,叮囑他不要讀得太多太累……愛人的氣息無處不在,馮理達把思念寫進日記:“親愛的錚,今天是你100天的日子,你的理達想著你,念著你,愛著你。”她對兒子說:“你爸爸沒有離開我們,他會一直陪著我們的。”
痛失愛人并沒有打倒馮理達,她把悲痛化為力量,繼續奮斗在免疫戰線,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沒有多少時間了!”她四處奔走,傳播健康理念,依舊把大部分收入捐出,就像羅元錚一直支持的那樣。她說:“我的傷痛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但是我沒有被悲哀壓倒,元錚不希望我那樣。我要繼續他的足跡,向著我們共同的理想奔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出一切。”
2008年,帶著與愛人重逢的喜悅,83歲的馮理達倚在兒子的懷里,她說:“你爸爸想我了。”這是她留在世間的最后一句話。
誓言存在心里,他們的愛,一鎖就是一生。正如她說的那樣:“相信我和元錚的愛戀之花,在社會主義祖國的苑圃中姹紫嫣紅,永不凋謝。”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