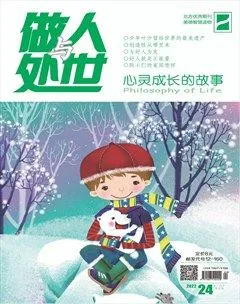交誼篤厚“兩吳生”
魏邦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吳宓是陜西人,吳芳吉是四川人。1911年,兩個人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園留美預備學校,兩人同班,交誼篤厚,世稱“兩吳生”。
1912年,吳芳吉不滿當局的一些舉措,寫了一首《討校長檄》,自署姓名張貼在食堂的墻壁上。校方要求吳芳吉寫檢討書悔過,方可繼續留校。但吳芳吉認為自己無過可悔,寧愿被開除也不寫檢討。吳芳吉表現出的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和勇氣,令吳宓大為嘆服:“碧柳(吳芳吉字)性格之激昂高潔,殆無可比!”吳芳吉失學后,生活陷入困境。吳宓呼吁同學們為吳芳吉捐款,在他的帶領與呼吁下,為吳芳吉募集到40塊大洋。當吳宓將帶著體溫的40快大洋交到吳芳吉的手中時,吳芳吉感動得熱淚盈眶。
吳宓赴美后并未忘記吳芳吉。吳芳吉因失學而沒拿到文憑,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吳宓便在美國留學生中發起支援吳芳吉的募捐活動,并訂下五條約定:“1.數目多少,各人自由認定。2.定期繳納,不容延緩。3.只盡在己之義,不問受者作何使用。4.永無酬報還答。5.俟碧柳獨立時,公議解組。”因吳宓的倡議,每月都有一筆款子飛越大洋,按時抵達四川的吳芳吉家中。吳宓還寄來英文書刊,供吳芳吉自學。有了這筆資助,吳芳吉得以安心在家自學一年,獲益甚多。
吳宓歸國后,介紹吳芳吉赴西北大學、東北大學等多所高校任教。有一段時間,西北大學所在地西安爆發戰爭,吳芳吉工資停發,與家人聯系中斷。吳宓承擔了吳芳吉老家的父母妻子孩子共六口人全部生活費用。吳芳吉父親去世時,吳宓立即匯款“以作奠儀”,但苦于“郵匯、銀匯均不通”,他讓吳芳吉設法募資辦后事,自己以后代為償還。
吳宓知道吳芳吉在四川老家處境不佳,有才難展,一再邀請吳芳吉去清華和自己朝夕相處,切磋詩藝。為解決吳芳吉生計問題,他個人出資60大洋,請吳芳吉協助自己編《學衡》,空閑時間吳芳吉可自由讀書寫作。至于吳芳吉“家人生計”,吳宓“愿負全責”。
由于家累甚重,交通不便,吳芳吉沒能接受吳宓的邀請,一直困守在老家,吳宓多次在信中表示了惋惜之情。在他看來,吳芳吉若能來清華,兩人可相互切磋,增長學識和詩藝,他斷言,這種理想的生活有助于吳芳吉“成為中國二十世紀之大詩人”。1919年,吳芳吉陸續寫出《婉容詞》《兩父子》等膾炙人口的詩篇,聲名鵲起。吳宓為之興高采烈,寫詩致賀:“此道今時無敵手,中華第一大詩人。”成名后的吳芳吉飲水思源,頗動感情地說:“雨僧(吳宓字)者,吾良友而賢師也……吾詩有今日者,全賴雨僧之力也。”
吳宓和吳芳吉清華一別,“別時容易見時難”,兩人只能魚雁往還,以詩訴情:“半載不裁箋,思君情如醉。君意亦何長,尺素頻繁寄。”對于兩人的深情厚誼,吳宓有詩作答:“嗟予與季子,情深不自量。蘇武與李陵,差許為榜樣。”對于吳宓的幫助與教誨,吳芳吉自是心存感激,他在詩中寫道:“江上二劉子,涇陽一長兄,微君勤教誨,及長猶頑童……”“涇陽一長兄”指的就是吳宓。
1932年,年僅36歲的吳芳吉病逝。接到噩耗后,吳宓當即寫下悼詩:“如何碧柳逝,驚聞初不驚。塵世為旅客,修短各驛程。亭館偶唔集,舟車互相送。君靈獲安息,從茲樂永生。”平淡的詩句卻蘊含著對摯友的真情。為紀念亡友,吳宓搜集吳芳吉遺作,刊印《白屋先生遺書》。此后,每次請人吃飯,桌上多擺一副杯筷,舉箸前靜坐、默禱3分鐘,足見其與吳芳吉的友情是多么深厚。
吳芳吉去世后,其年僅19歲的長子吳漢驤不得不輟學,去中學教書,挑起養活全家的重擔。吳漢驤婚后,隨著孩子的出生,家累更重。1955年,吳宓主動聯系上他,每月支持他10塊大洋,長達11年。其間,吳漢驤的長女考入西南師范學院英語系,吳宓每月資助她直至畢業。
吳芳吉能得吳宓這樣一位摯友,可謂一生幸甚!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