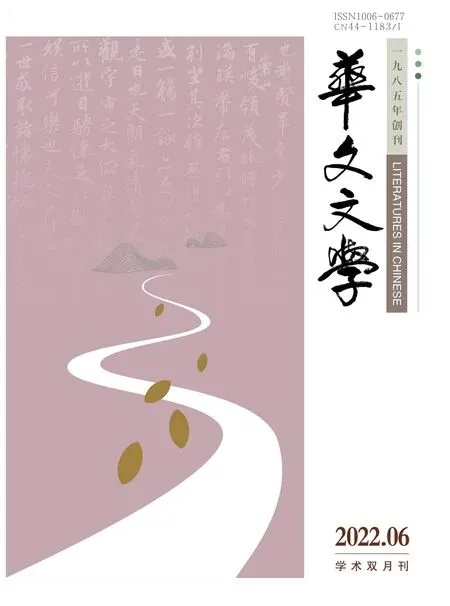海外潮人兒童文學中的潮汕文化研究
曾小月
潮汕民間流傳這樣一句俗語: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凡是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汕文化。潮汕人向來具有冒險精神,據稱從宋元時期開始就有了海上經貿活動。逮至近現代,一批批潮人奔赴海外,為自己和親人謀求更好的出路和遠大的前程。移居海外的潮汕籍華人逐漸安身立命于異國他鄉,卻又難以忘懷曾經的一花一木,于是提起筆來,在語言文字的王國抒發對故土的眷念之情。在華文文學創作中,潮汕籍作家不僅關注成人題材,還傾心于少年兒童的成長和教育問題,這些作品可稱作“海外潮人兒童文學”。
在數量和質量上,海外潮人兒童文學均已形成一定規模與水平。然而,囿于華文文學之“成人文學”光環,海外潮人兒童文學一直處于冷遇狀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兒童文學作品一方面蘊含著審美的文學屬性,另一方面彰顯出濃濃的潮汕文化特質,是我們全面了解潮汕籍海外作家華文文學創作的一個極好補充。
一、海外潮人兒童文學概觀
海外潮人兒童文學,此一概念的提出應屬首次。因此在考察海外潮人兒童文學創作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厘清一下兒童文學的基本內涵。
兒童文學不等于兒童讀物,它不只是傳達知識內容的形象化手段,而是具有獨立的、完整的藝術品格和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有論者曾提及兒童文學的三個概念:一是指被孩童收編或是認證的作品;二是指以兒童為創作的預設對象的作品;三是從文類的角度來歸納的作品。①兒童文學是一個現代的概念,這就使得在明確和自覺的兒童文學創作觀念產生以前,部分為兒童所喜愛的作品實際上并不是專為兒童創作。但是實質上,這些作品滿足了兒童的精神需求,因而也就自然地被兒童所接納。誠然“兒童文學”一詞源自于與“成人文學”的區分需求,但這些作品的讀者不僅限于兒童,還可以包括成人。比如,最初童話故事的讀者除了兒童之外也包括成人,至少當兒童還無法自主閱讀的時候,往往是由家長為他們講述故事。況且,許多童話故事集均取材于民間故事或古典文學中某些膾炙人口的情節,這就更加延展了兒童文學的能指范圍。
由上可見,以第三種類型為標準,將兒童文學視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或許可以整合三種觀念所包含的作品,從而更全面、客觀地考量兒童文學作品。所以,本文中所涉及的兒童文學,主要指具有簡潔、童真、幽默、奇異和叛逆性等審美屬性的一種類型獨特的文學作品。
明確了這一個概念,就便于我們甄選海外潮人兒童文學作品了。海外潮人兒童文學創作,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紀上半葉。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產生了一大批享譽海內外的華文兒童文學作品和華文兒童作家。從地理環境上來看,這些作家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和北美地區。代表作家有馬來西亞的馬漢;新加坡的孟紫、葛凡、李建、箏心、陳華淑、郭永秀;泰國的司馬攻、夢莉、范模士;文萊的何信良;美國的非馬等。除創作者之外,華文兒童文學體裁也十分豐富,包括童話、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兒童詩歌等。其中,兒童小說和兒童散文為創作最為集中的兩個文體,不少作家創作時會同時兼顧兩者,如孟紫、馬漢、范模士、司馬攻等。有部分作家擅長寫童話和寓言,如葛凡、李建、孟紫、箏心等;而像非馬、郭永秀等的作品多以兒童詩為主。
二、海外潮人兒童文學中的潮汕文化表征
(一)以潮汕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源頭,影響與規范著海外潮人兒童文學的審美旨趣和價值訴求。
潮汕文化是在潮汕地區的地理環境和民情風俗孕育下的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潮汕文化深刻地影響著海外潮人作家的文學創作,成為他們表情達意的一種精神源頭。其中,提倡人倫、重視親情、勇于進取的主題鮮明地存在于海外潮人兒童文學作品中。
旅居馬來西亞的潮汕籍作家馬漢,在其兒童故事《鱷魚王子》②中為讀者塑造了一位舍棄榮華、孝順母親的鱷魚王子形象。雖然身為鱷魚王的孩子,但他并不準備住在父親的皇宮里,而是更愿意回到鄉下去服侍含辛茹苦養育了自己的母親。在此文本中,我們可以了解,親人是比任何金銀珠寶都要珍貴的寶物。潮汕地區雖遠離中原厚土,但潮汕文化始終秉承儒家文化,重視孝悌仁義。因此,浸淫于潮汕文化的馬漢先生也就自然地把這種傳統美德賦予筆下人物,成為其鍛塑海外潮人兒童品性的主要方向。
潮汕地處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自古以來便多出海經商之舉,由此形成了潮汕人民努力拼搏,勇于進取的“紅頭船”精神。馬漢在兒童小說《獅子城的建立》③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布維納,就是一位勇敢無畏的開拓者。布維納年輕有為又很有才干,把自己治下的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條,但他卻并不滿足。“我一定要像兀鷹與海燕那樣,渡過小河,進入大海洋中去,然后遠渡重洋,去看看海的那一邊的世界,為開拓我的前程而努力,趁著年輕力壯的時候!”抱著這樣的想法,這位年輕人踏上了冒險之旅,以勇氣為盾,謀略為矛,一路披荊斬棘,最終在新的大陸上建立起更為強大的國家。
(二)以世界各國潮人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個人認同與群體認同為關聯。
文化認同是個人認同和群體認同相互作用的產物。海外潮人作家在移民后,猶如一滴小水滴落入了另一種文化的包圍之下,所創作的每一篇華文作品都是孤立于本土主流文化之外的,但當這些作品匯聚到一起,就形成了汪洋大海。每一位潮人在尋找到群體認同的庇佑和襄助后,得以在相互交流和共同成長中看到個人的價值。
時至今日,祖籍潮汕的華人早已擺脫了移民初期的窘迫,他們逐漸融入當地社會和主流文化。但在堅持用漢語進行文學創作的海外潮人作家心中,故土文化始終是他們無法割舍的根。一方面是綿延五千年的母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是移居國的本土文化,兩相結合,共同滋養著其文學創作的質素,其中便包括了兒童文學寫作。
新加坡潮人作家孟紫的一系列兒童文學作品中,就體現出由個人到群體的文化認同。童話《鵝》透過大白鵝家庭,向小讀者講述了個人意識與集體認同的內在關系。④奇奇是家里最小的鵝寶寶,在嬌養之下,形成了奇奇驕縱、貪玩的性格。當他第一次看到白天鵝時,被這種會飛又美麗的生物迷住了,他甚至想要就此離家,而同天鵝夫婦一起過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天鵝媽媽清醒地勸他說:“回家吧!好孩子!回到你的同胞那兒去,你才能夠找到真正的快樂!”作者采用童話慣用的動物喻人手法,將大白鵝、天鵝比擬為現實生活當中的海外潮人和移居國的本土人,以此宣揚團結一致、不忘初心的道理。潮人雖遠離故土,但他們的心仍是緊緊相連,異鄉生活再好,也不要忘卻自己的華人血統。奇奇向往變成天鵝,可只有回到家人身邊才能收獲真正的快樂。潮人也只有身處華人團體,才能明確個人的情感認同和文化認同。
(三)以潮汕傳統文化與華人聚居地本土文化的交流對話為表征。
潮汕文化和本土文化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在相遇時并不總是和諧融洽的,時常存在著文化沖突和文化誤解。這些矛盾和問題被作家們反復書寫,并由此凸顯出個人的態度和立場。
馬漢在兒童生活故事《倫敦來信》中,以一個小學生對語言的接受為例,探討了文化接受的問題⑤。小主人公吳多偉成績優異,唯獨華文很差。他認為全家很快要移民去英國,所以他只要學好英語,了解英國文化就夠了,沒有必要學華文。直到他到了英國后才追悔莫及,因為他發現自己身為華人,卻對本身的文化、習俗或語言完全一無所知,成為了當地人的一個笑談。在面對兩種文化的沖突上,作者提出的看法是既不能屈從于異國文化,拋棄本民族文化,也不能固守本民族文化而排斥異國文化。而應以寬容理解的態度對待兩國文化,促成其交流與對話。
泰國潮人作家司馬攻在散文《祖母的芒果樹》中提出的“兩個故鄉”概念,便是中泰文化交流影響的結果⑥。作者以移植的芒果樹暗喻移居的華僑。文中寫道,被祖母從故土泰國移植到異鄉潮州的芒果樹,剛開始水土不服,然而經過祖母的悉心培育,它們結出了滿枝碩果,給我們形象地呈現出“樹挪活,人挪也活”的“故鄉”概念演變過程。散文中的“我”由潮州至泰國,“我”的祖母由泰國至潮州,那棵久經風雨仍屹立不倒的芒果樹勾連起了兩個大陸,兩個故鄉,兩種文化。類似的“兩個故鄉”的文學書寫,在其他潮人兒童文學中也有體現。他們雖已融入了移居國的生活,但在使用華文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時,自覺地雜糅了移居國異鄉文化和祖籍國原鄉文化,故而,其作品在題材與主題上便顯得更為多樣和豐富。
(四)以構建一個跨越國界的同文同源、蓬勃發展的兒童文學藝術家園為創作宗旨。
海外潮汕籍華文作家在創作兒童文學,給孩子們講述潮人故事的同時,也是為整個華文兒童文學家園添磚加瓦。五千年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世界華文兒童文學共同的精神源頭,潮汕文化是海外潮人作家賡續母國文化,書寫兒童故事的創作法寶。無論是在蕉風椰雨滋養下的東南亞,還是在摩天大樓穿梭中的北美諸地,潮人作家總不忘在其兒童文學王國盞上一壺工夫茶,歌詠一位肩擔道義的人物形象。
一源多元是海外潮人兒童文學的又一大特色,作家們始終以立足母國,面向世界為其創作宗旨。在雙重文化的影響下,既不忘本民族文化,又吸收接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交流和對話中進行創作。
三、海外潮人兒童文學潮汕文化的建構方式
(一)借助兒童文學作品培養華人兒童的自我意識能力。
海外潮人兒童文學創作著意于華人少年兒童主體自我意識能力的培養,在兒童人物形象、成長故事敘述、教育主題提煉等維度,將潮人優秀傳統文化與華人兒童的價值理念相連結,進而提高華人兒童的文化自覺與自信,夯實潮人兒童文學文化認同的基礎。
兒童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性格特征。品格高尚的人物倍受作者稱贊,成為兒童讀者學習的楷模,而頑劣習性的人物則堅決批評,并力勸讀者引以為戒。比如新加坡潮人作家葛凡《家鼠落難》里借一群臟兮兮的老鼠之口,告誡讀者要保持生活環境的干凈整潔⑦。李建的《大象與黃狗》塑造了一個敦厚穩重、溫和有禮的大象形象和一個色厲內荏、蠻不講理的黃狗形象⑧。黃狗指責大象不經允許擅進它的地盤,要給大象一個下馬威,結果自然是正義打倒了邪惡。童話《不講理的烏龜》告訴我們要謙遜守禮,剛愎自用只會引來眾人的厭惡⑨。在這些童話故事中,作家常以動物喻人,借動物之行為生動地向兒童們傳遞著中華傳統美德。
培養兒童主體自我意識的另一個維度就是成長故事的敘述。成長主題不僅可以揭示人物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現,更能夠藝術化地呈現人物由幼稚到成熟的人生發展軌跡。這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和前后形象的比較可以更立體地傳達出作者的理念,而不流于模式化的說教。馬漢在兒童生活故事《崇華的假期》里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⑩。一位母親發現自己的兒子崇華滿腦子虛榮心,不懂得勞動的可貴,還充滿著可笑而又幼稚的幻想。因此,她決定把崇華送到鄉下的舅舅家,讓他去切身體驗勞動的辛苦和可貴。在初次體驗勞動時,小主人公崇華對農活一竅不通,但隨著故事的進程,我們發現崇華逐漸有了改變。由于田間勞作,他的體魄得到了鍛煉,他的心智也得到了增長。舅舅的言傳身教讓他認識到,勞作并不是不花腦筋、只靠體力的低賤工作,反而是大有學問的,因為這需要具備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由故事開始時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溫室花朵,成長為一個能夠獨立勞動、具有思辨能力的小大人,崇華的成長經歷足夠令我們肅然起敬。
立德樹人,是兒童文學的核心目的。兒童文學作家在寫作中主動探討教育元素,希望在兼顧審美性的同時,也能讓小讀者有所裨益。所以,在題材的選擇、內容的寫作上,作家們傾向于能夠引發人們思考的教育主題。無論是塑造兒童形象,還是講述個人成長故事,潮人兒童文學都飽含著鮮明的道德教化主題。憑借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故事,潮人作家把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價值理念潤物細無聲地傳播開來。
(二)興建潮汕文化的華文兒童文學場域。
潮汕文化的華文兒童文學場域,主要由潮汕文化的物質或精神載體予以體現。在潮人兒童文學創作中,作家們積極融入潮汕民間習俗(如傳說、節日、神話、典故、游戲等)、潮汕傳統物質文化(如潮汕建筑、潮汕烹飪、潮汕醫藥等),以及潮汕傳統藝術(如潮劇、潮樂、英歌舞、民謠等),把潮汕元素與兒童文學特有的敘事手法、語言文字、思維模式相結合,營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兒童文學王國。
潮汕地區流行的特有節日和慶祝方式,是海外潮人作家反復書寫的內容。泰籍華文作家夢莉的兒童散文常以潮汕傳統民俗為背景創作。《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以第一人稱口吻,追述“我”按潮汕慣例,在中秋節為自己砌小塔的往事[11]。“我”不像其他女孩,總是依靠男孩的力量砌塔,而是毅然獨立完成此項“重任”。全文簡潔流暢,描寫細膩。由于文中融匯了潮汕中秋燒塔風俗,讀來便也多了一份朦朧靜謐之美。通過砌塔習俗,作者著意塑造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小女孩形象。文中寫到,砌塔進展并非一帆風順,“我”的小塔被一個男孩惡意毀壞,“我”感到莫大的憤怒卻又無計可施。成年后,當“我”回首這段往事時,卻已然釋懷。《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情節簡單而又圓滿,“我”的形象與性格也逐漸清晰起來,其中最令人們難以忘懷的便是潮汕人謙遜待人的品德了。
將潮汕方言、俚語融入文本,也是海外潮人兒童文學的一大特色。《黑馬·白襪》(孟紫)中把挨校長的藤條叫做“炒粿條”[12],《祖母的芒果樹》(司馬攻)里將芒果稱為“望果”(潮汕俗語)[13]。此外作家們還辛勤引用潮汕民歌、潮劇元素,以便凸顯文本的歷史背景。《檳榔》(司馬攻)一文開篇就吟唱潮州檳榔民歌,“葉埔蟬,叫勻勻,大個拼欲衫,二個拼欲裙,三個拼欲檳榔鼓,四個拼欲銅面盆。……”[14]朗朗上口的民歌,配合著簡樸活潑的故事情節,給整篇散文帶來一種天真爛漫的美感。
四、海外潮人兒童文學潮汕文化認同的建構原因
(一)家國情懷的促動。
潮汕兒童作家和華人兒童散居世界各地,無論他們身居何處,總不忘追溯精神源頭,不忘尋求文化之根。由此,潮人兒童文學作品中滿溢著潮汕文化質素。
由于生計、求學等原因,潮汕先民遠渡重洋,過番僑居。然而,對于故鄉的思念卻濃得化不開。作家們擇物而詠,書文寄情。司馬攻的芒果樹、夢莉的小塔、郭永秀的筷子,無不彰顯著潮汕意味和中國風情。
眷戀故土并不意味著抱殘守缺,一味地沉溺過去,相反,守住自己文化的根源才能堅守本性,立足于他鄉。司馬攻散文《明月水中來》[15]中那把傳承了三代的潮汕功夫茶茶壺,就是這樣一個象征物,從中國到泰國,這把茶壺承載了三個人的思想回憶,滿盛著過往的歲月。而“我”的兒子對潮汕功夫茶的態度由討厭到喜愛,暗示著潮汕文化在賡續過程中的問題和契機。
潮汕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使得每一個海外潮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無論身在何處,聽到潮汕話便倍感親切,品到潮汕美食便如返家鄉。正如陳華淑在作品中抒發的感慨:“‘作客’不如‘做主’,只有生活在自已所屬的國土上,才不會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16]同樣,只有生活在自己認同的文化中,才能真正心安。潮人總是習慣把歸鄉省親喚作“回唐山”,這一個“回”字體現的就是潮人對家鄉的眷戀之情。
(二)育兒樹人的旨歸。
海外潮人對兒童教育非常重視,他們秉承儒學傳統,在海外不遺余力地為潮人新生一代創造優良的學習條件。從興建華文學校到創辦華文報刊,潮人們矢志不渝地將華夏文字和潮汕文化薪火相傳,為華人兒童在異邦文化中墾拓出一方精神家園。
孟紫在《考試夢》一文中以華人重視國文教育為故事線索,塑造了孟智強一家人[17]。孟智強的父母非常重視學校教育,要求兒子智強專心學業,不要沉湎于課外雜書。《倫敦來信》(馬漢)督促小讀者們要好好學習自己民族的文化,才能在外國人面前展現出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18]。《到處是書》(范模士)教導孩子們時刻不忘閱讀,夯實個人的文化基礎[19],其中講到,華人父親為自己的孩子不懂華文,不會潮汕話而憂心忡忡。但事實上,孩子已在父親不知曉的情況下便開始學習華文潮語,因為華文學習已流行于同學們中間,落后者是會遭人恥笑的。作者將華人兒童的真實校園生活記錄于文中,不僅反映了華人的現實問題,還試圖調動起華人兒童求知進步的積極性。
兒童時期,是一個個體身心成長的重要階段,每個華人家庭都非常重視兒童的教育問題。一個集體與社會是由千萬個家庭組成的,個人的成長直接關聯著整個族群生命延續和文化傳承。通過這些文學作品,給海外潮人兒童講述潮汕故事,可以讓兒童在遠離故鄉本土之時,感知潮汕文化,接續母國精神。
(三)文化身份的立場。
華人兒童身處他國,面對異質文化的挑戰,需要明確個人與群體的身份。通過文學作品所包含的潮汕文化智慧,華人兒童獲得戰勝孤獨、寂寞、屈辱和貧困的精神支柱,從而健康地生活在移居國。
郭永秀的詩歌《筷子的故事》巧妙地選擇“筷子”作為核心意象,警示華人失去文化之根就等于失去了抵抗困境的精神力量[20]。詩人追訴著先輩的戒律,以為人應當像筷子一樣,“一支易折,兩支/才有御敵的力量/合起來便可——頂天立地威武不懼”。但是,當今的子孫卻早已遺忘傳統,拿起刀叉就再也不記得筷子的用法。筷子起源自古老中國,它既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又成為了中華文化的象征之一。該詩以筷子為意象,暗喻海外潮人應團結一致,協同合作。
移居泰國的潮人作家常在文學作品中孜孜不倦地描繪潮汕美食。曾心的散文《一壇老菜脯》動情地描寫了在異國品嘗潮汕菜脯的難得;洪林《兒時的油炸粿》中,感慨曼谷的油炸粿無法堪比兒時的油炸粿;姚宗偉《一碗粉絲羹》中追憶母親親手烹飪的長壽粉絲羹;陸留《荔枝節的悲哀》聲明熱愛來自家鄉的荔枝要多于芒果和榴蓮,等等。泰華潮人作家在用散文書寫美食,表達思鄉情緒之外,更深層次的目的是通過食物構建、維持、強調血液里的華人身份。
本質上,海外潮人作家對潮汕食物的關注與珍視是一種文化自覺的體現。不論潮汕美食,還是潮汕民俗、潮汕歌謠,這都是作家鋪陳情感、凸顯文化身份的一個有效途徑。通過這些潮汕文化象征物,潮人不但獲得了一種在移居國個體存在的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尋求到了集體歸屬感與價值認同感。而這種有意識的文學創作理念,也會清晰地傳達給潮人新生一代。
五、結語
綜觀海外華文兒童文學,潮汕籍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均不可小覷。對潮汕文化資源的吸收利用,使得潮人兒童文學內涵豐富、主題鮮明。這些作品既守護潮汕文化,又關切兒童的成長與發展,將兒童文學創作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向融合,為讀者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在當前熱切探討地域文化與文藝創作問題的背景下,海外潮人兒童文學的藝術技巧、美學價值是應該引起我們做深入研究的。
①杜明城:《兒童文學,所為何來?》,《竹蜻蜓(少兒文學與文化)》2020 年第6 期。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11][12][16][17][18][19]王泉根主編:《世界華文兒童文學大系》,開明出版社1996 年版,第250 頁,第253 頁,第212 頁,第581 頁,第198 頁,第205 頁,第204 頁,第804 頁,第596 頁,第773 頁,第528 頁,第216 頁,第581 頁,第598 頁。
⑥[13][14][15]司馬攻:《司馬攻散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年版,第5 頁,第5 頁,第19 頁,第10 頁。
[20]郭永秀:《郭永秀詩集》,七洋出版社1989 年版,第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