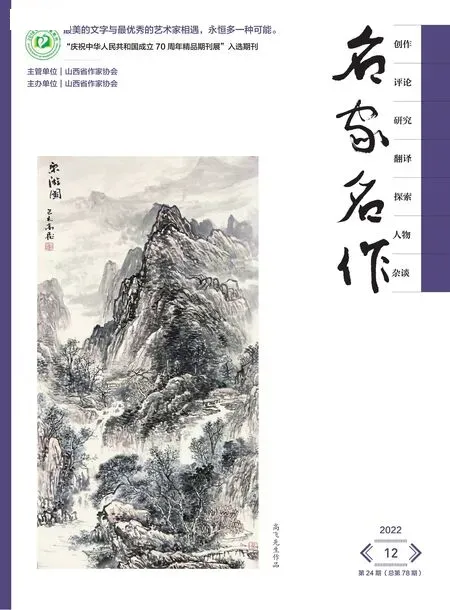試論蒙古族詩人瑞常漢文詩歌創作的藝術風格
林科留
清代最早將杭州設立為八旗駐防之地,八旗子弟久駐江南而遠離疆場。長時間的城市定居生活,造成了“不但是駐防人口的城市化,而且也是他們的地方化。這一過程最終使來自滿洲的旗人變成了杭州旗人”①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系的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地方化使駐防旗人對杭州逐漸產生了歸屬感,生活習俗的認同感也越來越強。
在這樣一個民族融合、文化認同的過程中,杭州駐防營中的八旗文人大量學習漢族文化,很多蒙古族詩人從事漢文詩歌創作,如赫特赫納、裕貴、瑞常、瑞慶、蘇哷訥、萬清、文瑞、文秀、貴成等。其中瑞常有詩集傳世,極具代表性,藝術成就很高。瑞常約生于嘉慶年間(1796—1820年),字芝生,號西樵,石爾德特氏,蒙古鑲紅旗人,杭州駐防,道光壬辰(1832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元年(1862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謚文端,著有《如舟吟館詩抄》一卷。瑞常在朝中做官地位極高,作為八旗駐防代表,生活條件較為優越,且常與不同民族間的文人進行唱和,其詩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八旗駐防文學的特色。他生長于杭州,其詩深受杭州山水的影響,又研讀漢文經典,博采眾家,風格顯著。研究具有代表性詩人的詩歌,可管窺到當時八旗文人漢文詩歌創作所達到的藝術高度。
一、清水出芙蓉
文學與地域的關系密切,地域文學在清代文學中比較顯著。唐代魏征在《文學傳序》中清楚地表明南北文風有“清綺”與“貞剛”的差異。李浩在《長安都市文化與朝鮮·日本》中指出,地域空間有制約性和差異性,如“駿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南北地域常見的景物及特征完全不同。瑞常的詩歌明顯受到杭州這一地域的影響。杭州是一個人文氣象與自然風光相得益彰的城市,名勝眾多,先賢不勝枚舉,氣候溫潤,風光旖旎,人民淳樸,這一切讓杭州充滿詩情畫意。瑞常作詩強調性情,杭州山水則源源不斷為瑞常提供創作的靈感。正如夏同善在《如舟吟館詩鈔》中指出的:“詩本于性情,而詩人多以山水為性情,吾杭山水,據東南之勝,靈秀之氣,尤萃于西子一湖。古詩人宦游于此,往往勾留不能去。白公蘇公,其尤著者也。矧性耽風雅,生長其地者哉!”②見《如舟吟館詩鈔》。生活在這樣一個鐘靈毓秀的地方,瑞常的詩歌呈現出詩風清明的特色。
(一)意象清
瑞常的詩歌題材廣泛,紀游、贈答、詠物、閨情、懷古、感懷等諸多類型一經點染,妙筆生花。在其詩集中,閑適詩占據一半以上,也最見其詩歌風格。“凝結于真山水真性情而不可解”,以“纏綿悱惻的感情、淺白空靈的語言、畫比景的創作技法”,實現“以山水為性情”的“詩言志”的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清新俊逸,妙集眾長,足以繼蘇、白二公之后,而為湖光生色”③見夏同善作《柳營謠》序。。其詩歌“清”的風格首先表現在意象上。瑞常或寫西湖四時景致,或以春夏秋冬時令為名勾勒風景,或是旅途所見、漫興偶吟,“即景便生情,形形兼色色”(《學詩》),“清”的特色無處不在。
他選取的意象是樸素清明的自然風物,從而營造出清逸明秀之境。如《山雨》:“綠痕遙劃草萋萋,新漲添來水滿溪。山雨仨停云滃起,隔林猶有鷓鴣啼。”草綠、水滿、云起、鳥啼,這些意象尋常又詩意,渲染出清明寧靜之美。瑞常在歌吟景物時,將村居的安閑與純凈的美著色于意象,一股清新雅致之趣撲面而來。“小橋低處響魚叉,綠滿池塘草色斜。難得村居門卷僻,隔籬春水呌蝦蟆。”(《郊外》)悠綠的池塘上,是魚叉在撥弄蝦蟆。詩人把魚叉動態化、擬人化,同時又把它安置在優美的環境之中,雅趣異常。在《暮春》中“湖山十里開圖畫”,詩人的筆下“草滿郊原水滿溪,拖藍潑翠徧高低。打魚舟去沖波穩,叱犢人來插稻齊。芍藥殿春千朶放,鷓鴣帶雨一聲啼”。翠草、藍溪、魚舟、叱犢人、芍藥、鷓鴣這些意象構成一幅畫卷,農家勞動與飽滿、活潑、鮮艷的大自然水乳交融。 在《郊居》中“新萍漾碧滿池塘,眾綠圍村樹影涼。閑向柴門扶杖立,晚風吹送稻花香”。稻花的意象將詩歌的清雅之趣推向極致。詩人以如此閑適的心情感受風中的稻香。這稻花不僅熏醉了詩人,也仿佛在散播著豐收的預兆、幸福的希望。在《微雨過辛豐》中,“細雨斜風暗客程,池塘水滿聽蛙鳴。牧兒牛背騎偏穩,披得蓑衣自在行”。細雨、斜風、池塘、蛙鳴、牧兒、牛背、蓑衣所襯托出的清閑自由之樂令人神往。
(二)語言清
瑞常“清”的詩風表現在語言的干凈、簡白,如同水墨丹青。如《閶門遇雪》:“金閶羈客路,風雨一孤舟。隔岸人家密,漫天雪意浮。浪翻驚渡口,花冷撲船頭。遙憶西湖上,煙波動遠愁。”習用的表達,清淡無比。孤舟、漫天的雪、浪花翻騰等,用語簡潔,在工巧的結構中,將孤舟行人途中遇雪的清愁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外,《山行》《湖上》《南屏》《秋暮》等詩均能突出詩人的用語特色。瑞常的詠物詩淺白易懂。如《詠菜》:“一覽畦中色,斯民系我思。灌園輸仲子,學圃笑樊遲。葉熟飛霜候,香凝滴露時。若非根可咬,清味有誰知。”
從看到園中菜苗,想到黎民百姓,又進一步推及菜苗成熟,不咬根難以知味,其表達所思所感明白如話。“一覽”“我思”“葉熟”“咬”都是偏口語化的詞,甚是淺白。
“清”的風格還表現在詩人對“清”的鐘情。在瑞常的詩中,“清”字大量出現:“詩懷水樣清”①出自《秋暮》一詩。“風送軺車驛路清”②出自《題花松岑尚書車輶詩刻手卷》一詩。“數去風懷水樣清”③出自《藕香贊善假滿旋京書贈四律》一詩。“作宦敢云清似水”④出自《答貴鏡泉見寄原韻》一詩。“清風吹滿曝衣樓”⑤出自《賀英梅臣新婚》一詩。“綺窗開處清光射”“公余昕夕聆清話”⑥出自《張詩齡少宰除夕贈手卷詩畫即步韻志謝》一詩。“藤花廳上接清暉”⑦出自《三月晦日張詩翁約極樂寺看海棠即和原韻》一詩。“買書乏清俸”⑧出自《書寄雪堂弟》一詩。等。在267首詩中,43首詩寫到了“清”,足見詩人對“清”的鐘情。景清、味清、官清、清情、清談、清游,“清”字無處不在。
瑞常詩歌“清”字鮮明,除杭州環境影響之外,與他身居高位有關,一則生活休閑,二則大抵似嚴迪昌所言:“深于文學的皇子、宗室群從們在嚴酷的宮廷權力斗爭和無情懲處的現實面前,不少成員竟轉化為一種奇特的‘朝中之野’的心態,借詩歌以自娛或宣泄苦悶。”⑨嚴迪昌:《清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第18頁。在個人審美的追求之下,“清”的詩風就不足為奇。
二、清中生新意
瑞常的詩歌創作,清中生新。米彥青指出:“清新的寫景之作,在瑞常詩集中占有主導地位。”⑩米彥青:《接受與書寫:唐詩與清代蒙古族漢語韻文創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第196頁。有“清新俊逸”之美。“新”的特點在“清”中顯得尤為突出。詩人是“得句先留翰墨新”,寫景空靈清新。如《湖山看山》:“久困風塵客,歸來飽看山。寺藏紅樹里,僧住白云間。遠渚眠鷗穩,孤峰倦鶴還。黃昏時已近,石磴尚登攀。”
湖山看山,如臨仙境。不是“深山藏古寺”,而是“寺藏紅樹里”。不是“空山不見人”,而是“僧住白云間”,山到底如何,并沒有直接論述,而是以隱藏在紅樹間的古寺和僧人住所白云繚繞的細節之景,表現山勢之高、峰巒疊紅、環境幽靜,從而呼應看山之題,這種表達猶如神來之筆,空靈無限。
從細處品讀,他的“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字的使用。他的筆下“新”字出現三十多次,“草木新”“新月白”“水新綠”“迎歲新”“筑新墳”“續新詞”“吟新詩”“生新愁”“吐新絲”“見新篁”“愛新晴”“新插花”“新載花”“酌新醅”“新換衣”等等,“新” 總是觸動詩人的情思。二是意象的捕捉。所謂“詩家清景在新春”,詩人總在最初的時令物候里捕捉新的意象。如《初夏》中“清晨初試葛衣涼”,葛衣初試往往在寒冷褪去脫去棉衣,漸生炎熱卻還未到“單衫杏子黃”的時節,正是初夏。而正因為初試,感覺才會無比敏銳和新鮮。詩人抓住最初的時節,捕捉新鮮的意象,對初景的關注,可折射出詩人對新鮮的敏感,所作的詩也異常的清新。這在《新秋》《早起》《新竹》《御河早柳》《初夏》(布襪青鞋任所之)《初冬》《冬日早起》《初寒》《初冬早起》《初夏》(花到殘時蛺蝶稀)《春日早起》《初夏遣興》等詩中相當明顯。三是造語新。他造語新鮮,用常人不用之語。如“難得嫩涼天”①出自《重九柬石碩庭隆華平諸鄉友同飲》一詩。“嫩寒重換薄綿衣”②出自《四月朔與寶佩蘅少農同值六班話雨》一詩。“嫩涼先向客衣生”等等,他以“嫩”字來形容“寒”“涼”,表現出觸感的新鮮和細膩,使無形的感受有了肌理般的手感,用語非常新鮮。
三、風格背后的詩學思想
從瑞常的詩歌創作和詩歌風格中可以感知到瑞常的詩學思想。其詩學思想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其一是要求“清淡”。瑞常不推崇辭藻的華麗,講求平實和樸素。詩歌用語要求淺顯直白,不故作艱深、求奇求怪。自言“詩懷淡似僧”(《寄意》)“詩懷水樣清”(《秋暮》)“詩以道性情,所貴在清刻”③出自《學詩》一詩。,作詩以性情為主,情感真摯而清淡。他的詩歌有“清水出芙蓉”之美,要求“即景便生情,形形兼色色”(《學詩》),即不加雕飾,自然天成之中,“活潑見天真”(《學詩》)。
如“風前黃葉禿,雨后綠苔生。涼月隨人坐,微云帶雁橫。小窗眠不得,萬籟寂無聲”④出自《秋暮》一詩。。詩人描寫出秋暮之景,風起葉落,枝干變得光禿禿的,月色微涼,詩人不眠,萬籟皆寂。詩人所選用的景物“風”“黃葉”“涼月”“微云”,均是日常所見,描摹景物之態樹干之“禿”、人“坐”、綠苔“生”、大雁“橫”飛,簡潔生動,畫面感強,但無雕琢之痕,可謂妙極。秋暮情懷清淡,情緒輕柔,樸素中充滿感染力。
另外,他注重興感,及時記錄。如“逸興有時飛,披衣中夜起。得句便揮毫,真如撞鐘喜”⑤出自《自嘲》一詩。。逸興來時,便揮毫潑墨,自然暢達中直逼“我行我素即天真”的人生狀態。
其二是認為作詩要下苦功。他秉承著學人之詩的特色,指出“讀書志圣賢,格物先窮理”“欲得貫通須仗學,不經盤錯豈成材”⑥出自《九月朔接雪堂袁江信》一詩。“文章得失知應早,砥礪功夫愧未深”⑦出自《柬花松岑舒云溪兩同年》一詩。。學人之詩要求嘔心瀝血下苦功,要格物致知。瑞常對作詩的態度是“燈前詩稿要求工”⑧出自《還都》一詩。“詩吟半夜墨頻磨”⑨出自《漫興》一詩。甚至為作詩索盡“枯腸”。其作詩的狀態是“苔荒曲徑雙扉掩,書對韓燈一室親”⑩出自《春暮書懷》一詩。。瑞常的詩學思想,既有江西詩派學人之詩的特點,又有晚唐苦吟的特色,明顯受到主流詩壇上的“唐宋之爭”的影響,兼采眾家。他師法前人,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煜、杜牧、蘇軾等都有所接受,從而“機軸從心自一家”,塑造了自我的詩歌風格。就其詩歌的總體風格來看,他接受的更多是唐詩“主情”的特色,有王、孟優美寧靜、清逸嫻雅的特點。如其《田家》與王維《渭川田家》甚是趨同,在此不再贅述。
杭州駐防蒙古族詩人瑞常的詩歌風格,因為八旗駐防的地方化,“生長西湖秀氣中”,個人的學養性情以及傳統的“詩言志”的詩學觀使得他的詩歌有了“清”的風格,其創作匯入了清詩“唐宋調和”的洪流中,呈現出蒙漢民族文學交融的特點,具有獨具特色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