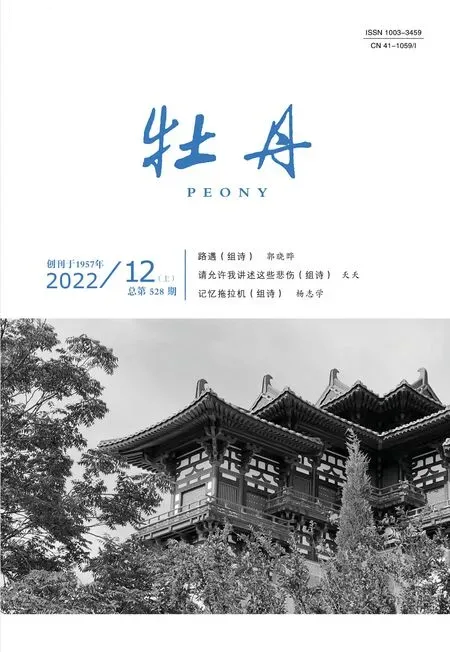長春,長春(組詩)
葛筱強
黃昏,走過臨河街
先說說離我更近的世榮路
或世舜路吧,次第點亮的路燈
收回了每一個需要拐彎的路口
而我已準備好和昨夜的夢境
背道而馳
在積雪的職業學院樓下
一個城市的冬天開始變得脆弱
甚至不堪黃昏的手掌一擊
她無比碩大的胸腔需要休息
也需要水泥與鋼鐵夢境中的安頓
再說說稍遠一點的現代詩公園吧
那些詩歌被刻進石頭的詩人
有的尚還年輕,有的步入暮年
有的已成為石頭的一部分
他們齊刷刷站在那兒,等待風吹來
冬天的酒杯,或者春天的一顆小小煙蒂
而讓我難于開口的,是我的身體
在走過臨河街黃昏的時候
忽然長出了一道虛掩的門
他是如此斑駁,閃爍,像一封
寫給自己的長長舊信,一片慌亂地
從田野飛過城市的落葉
在時間的孤島沉浮
在近埠街頭
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一個地名
放射性的隱喻,就像自己眼下的生活
它有顛覆性,也有消失于一個城市正午的可能
在近埠街的西側,般若寺窄門洞開
仿佛表意失準的鳥鳴,開始瀕臨塌陷
起風了。我站在近埠街與長春大街的夾角
不為時間和世界所動,仿佛一個
廣告牌也無法擦掉的斑點
忽然想起里爾克和阿赫瑪托娃
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我想和他們一起
拒絕任何深思熟慮的抒情
就像此時的近埠街,它并未成為一種文體
讓我在恍惚中再次著迷
雪地里的伊通河
在生活的左岸,所有的期待
都將變成傾聽心跳的誘餌
即使我仍舊期待從河流上游
歸來的鴿群的早晨,就像期待
一個完整的星系,在一座城市的腹地
安全過冬
我當然知道,從不可能的時間里脫身
無異于讓死亡也成為一種消費
無異于讓打水的竹籃從火中取栗
當我和這些河流帶來的念頭緊緊地抱在一起
朝陽橋
慢慢降臨的夜色切開了白晝的殘稿
卻無法切開我對橋下一個小說家的惦記
當天空開始下雪,開始一個冬天固有的癥候
我未能如往常一樣收到他用手機
發來的只言片語
這些年來,我們同樣心懷與世界無關的舊夢
也同樣相信生活常常需要一聲斷喝
就像黃昏時分的麻雀,為了振動羽翼
不得不面對與生俱來的如履薄冰
只有朝陽橋拆了又建,建了又拆
在落雪中寂靜無聲,只有我一個人
走向輕軌站臺的夜色,因為小說家
今夜消息的缺席深感不安
長春大街
朝霞是從東大橋開始的
而我在人間尋找城市,要從馬號門的拐角
出發,才能找到適合的姿勢
樹上的鳥鳴不需要天空將其顛倒
熄滅的路燈,也不需要早已湮滅的護城河
將其修改為過路人的眼睛
在某些不可信的傳說里
生活也不需要認真地談論
我和所有人的遭遇
僅僅因為清晨的一縷微風
我身體里的時間,僅僅是一件
意料之外的容器,他臨時收藏了
一條大街的空曠,卻不能完整地
把需要無數個出口的此生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