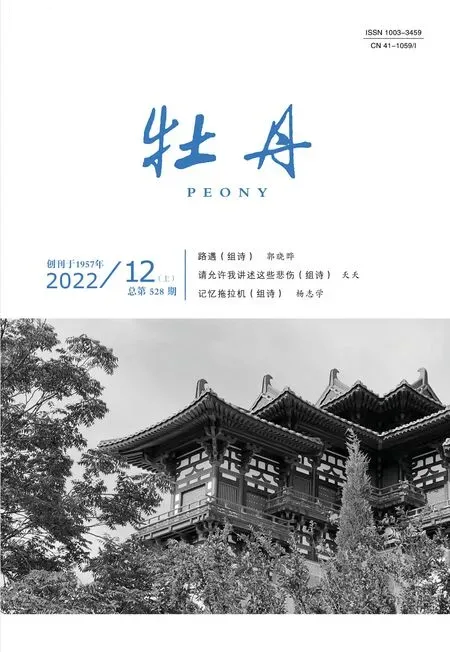夢中際遇(組詩)
高春林
面目
一旦醒來,我就會再回想一遍夢中的際遇,
夢里多年輕身姿,意味著什么?在暗示
老之將至?“因為詞,我們的面目還泛著微光。”
我說出這句時,你使勁點頭,使勁地
指了指水災后的城市——一些人就那樣消失了,
不消失的是詞。還有,這條街以及那條街,
一棟棟房子早就魔幻般消失了,唯有詞……
我還記得它的面目,有時我在夢里才覺得自然。
潁水記
過禹王像,仿佛傾聽到巨水——
無比寬闊的想像,在我看到
馬踏飛燕一個瞬間,化為潁河細浪。
潁河岸這時被蔚藍的秋水映照,
像一種最單純的存在。我們的存在。
不再是膠片感。“時間太快了,
它收服水,也收服了我的野性?”
“其間你的變化在于知我。”
我望著浩渺,定靜了一會兒,
想到這是遠古禹王治水獸之地,
據說,禹擊退水獸耗盡心血,
他的“女嬌”也變成了石頭。
秋風吹過耳郭時我有些微的戰栗。
這時水清澈到能看見自由魚,
“那些水獸后來都去了哪里?”
“或許是魔界,或許人的身體里。”
潁河水以極其細微的浪涌動著,
仿佛融入了我們斷續的交談——
“身體多景致,如若打開秘密。”
“除了水性美,還有一種危險?”
幾十米之外,各色車輛還是飛快,
再過一個多小時,或者更短,
中秋月就將從水面上升起……
黃岡,或明月上的黃州
赤壁磯收容了一個人的境遇。詞收容
暗時間的連翹。這時散結他身體的不適。
黃州的現代性,迄今找不到他的荒徑。
耳郭陷入“老來荒”截句的蕭瑟。
雪自北方來,緊跟著下到了南方帽檐上。
濤聲在。漩渦什么時候都在撕扯,
他的舟,在顛簸中駛入我們的街巷。
時間再度被明月柔軟,仿佛我忘了我有
一個真身,消瘦,低嗓門,
在記憶和遺忘之間,將睡著的語言喚醒。
現在它們厭倦了波濤。它們是靜靜的詞。
貌似貶謫也發著光,成為靜的詞。
十二月儲著雪——身體里的雪
印在雜志的封面上。給眼睛以表情。
現實的松針總是尖銳,如同詩歌,
以及詩里的“雨勢”“墳墓”,和倒帶。
列車快過了時間。我像是一個游蕩者,
停在舊地圖上,察看醒著的夢。
暗物質的世界,一個人,即是光的影像。
所有納入對象平均年齡為(61.6±10.0)年。按年齡分組,分為<50歲、50~60歲、60~70歲、≥70歲,其肺功能指標FEV1%為54.6%±22.7%、57.3%±22.7%、51.8%±21.5%、51.7%±17.4%,組間有統計學差異(F=3.04,P=0.028)。
有那么一個時間我感動于星河在亮
酒后的山顯得搖晃。我扶不住
迷蒙,沿一條寬闊山路散步
也叫散酒。世界感動于星河在亮
——大山之上唯有的星河,
每個星于開闊處獨立,又彼此照耀。
我以我的醉眼,說醉話,
醉即正確,我即星河之岸的眼睛。
觀水,水逝時間——
每一個真正的人都是時間上的星宿,
匆匆走著,憧憬或者隱身,
有時不得不給黑暗以詛咒,
有時在沉睡中為了再度蘇醒
做一個奇特的夢。我好奇于
星星有什么樣的面孔——
人面獅、獨角獸、鳥身女?
還是人模人樣?在無邊黑暗的
三更天,各自舞,或站成肅穆。
是什么已不再重要,即便是個流浪
牧人,被城市擠壓得失去牧場,
這里也兌現你的青坡青草。
你是你的妖嬈,這也等同于
山河在,星辰變幻出另外的天空。
我貌似更醉了,被山風吹著,
星河像波濤之水,不對,確切說
流動之火有了詞語的形象。
曾經,過多的時間里我們失去了它
——被捻暗的人,我有理由
擁著這個夜,“我是我的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