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快遞
胡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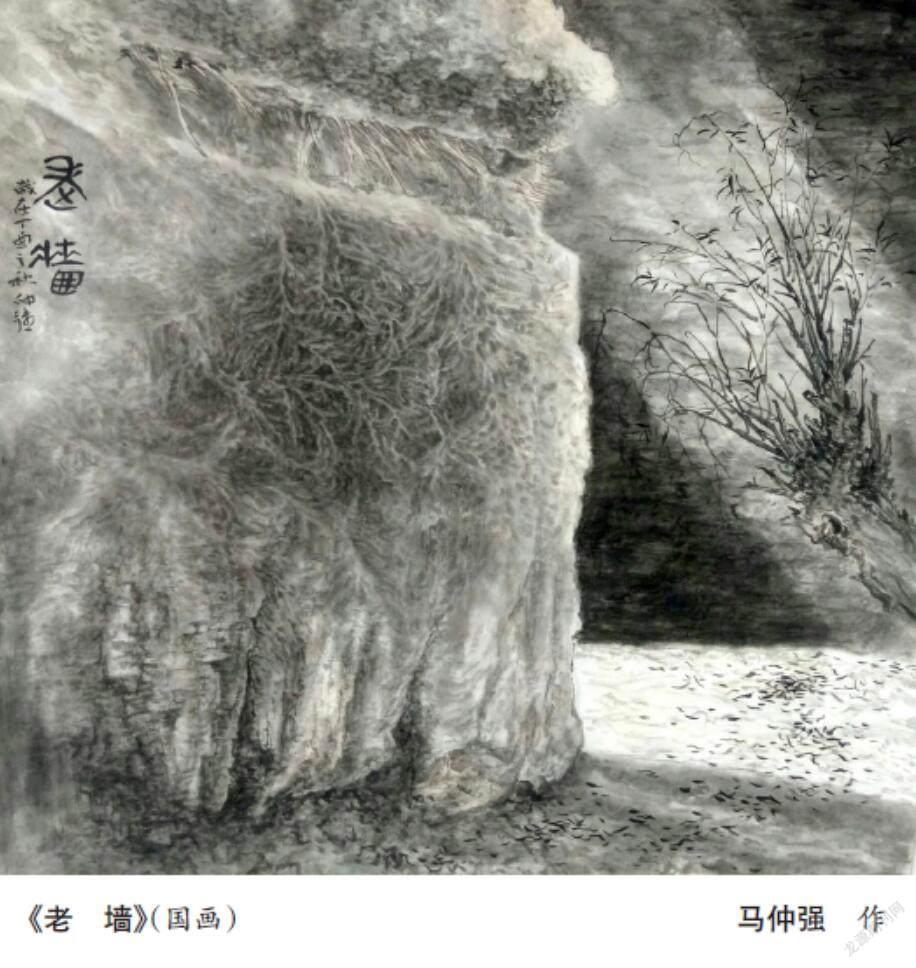
快遞員飛哥發動他那輛快遞三輪車,天嗖的一聲就全亮開了。
飛哥送完當天所有的快遞包裹,將那輛快遞三輪車停下,天又嗖的一聲全黑了。
飛哥就是把每天的日子干得兩頭黑的那種快遞小哥。他的車輪軋遍了這座城市的每一條大街小巷。飛哥每天早晨從床上爬起來,睜開眼,刷牙,洗臉,健身,快快地吃過早餐去公司打卡上班時,天還是黑的。傍晚送完所有的快遞,駕著空了的三輪車趕回公司做當天的業務交接時,天已經完全黑了。飛哥的快遞業務是那么地忙啊,總是見他駕著那輛快遞三輪車飛馳而來,又駕著那輛快遞三輪車嗖的一聲便不見了他的蹤影。
在這之前,飛哥是干報刊投遞的,也是每天早早地起床,騎上用腳蹬的二八自行車,把兩只鼓鼓的郵袋馱到自行車的后座上面,蹬起自行車沿著馬路的每一個報亭、彩票投注點投遞報紙雜志。偶爾也會從報刊市場的熟人那里批發過來一些暢銷書刊,自己晚上到地鐵口、天橋邊擺上一個雙人床單大小的地攤,把這些刊物擺出來,按定價的八五折出賣。賣得好的時候,一天能掙一百來塊錢。近些年紙質期刊發行量走向低谷,報刊投遞這一行越來越不好干,公司的業務越來越少,瀕臨破產。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網購進入了千家萬戶,快遞業務一下子繁忙了起來。飛哥就通過在大街上送報刊時認識的同行老鄉的介紹,在一家中型規模的快遞公司干起了快遞。飛哥的主要業務是把公司分配到他負責的那一片小區的快遞(包括信件和包裹)按照到件的時間順序擺放好,然后駕上自己的快遞三輪車順著每天設定好的路線,一件一件地給收件人送過去。待收件人取走快遞之后,他又將這些簽收過的快遞的詳細信息反饋給公司,公司收到反饋上去的信息,給了肯定的回復,飛哥當天的快遞業務才算完成。
飛哥租住在郊區的平房里,這個村里的平房小院大多數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起來的紅磚房。一家院子連著旁邊的一家院子。整個村子十幾家,二十來家,都連在一起,連成一片,這讓飛哥剛來的時候想起過《三國演義》中的赤壁之戰,曹操的士兵多是北方人,不慣于水戰,于是就用鐵鎖將船只一只接一只地連在一起。進入新世紀之后,涌向這座城市的外來工越來越多,住房一時緊張起來,這座城市一下子進入了寸土寸金的時代,似乎是在一夜之間房租猛漲。市中心的房價太高,那些拖家帶口,操著外地夾生普通話的外來工就開始涌向郊區租房,郊區的平房村剎那間一房難求,這時就有人把那八九十年代蓋的紅磚平房掀了頂子,就著下面的一層老房基在上面再加蓋一層,這樣原來的平房就一下子變成了二層的樓房。有的人家覺得蓋起了二層樓房還是不夠高,不夠寬,為了能收更多的房租,他們還會在新蓋起的二樓頂上再蓋一層高度相對要低些的三層,三層蓋起來,看上去搖搖欲墜,但還是可以住人,房少人多,那些可憐的外地人,為了要一個棲身之所,即便是更差一些的住處,很快就會有人租住。那些九十年代的豬圈、雞窩,經過輕微的改造都租出去了,外地人同樣在這里住得好好的。飛哥就住在這個城中村改造后的三樓上,三樓上一共住了八戶人家。外墻是單磚砌的,四面墻都是單磚,它的厚度不及一樓二樓墻體的一半。八戶人家各戶之間的間隔墻都是用木板隔起來的,木板上敷一層薄薄的石灰膏,初眼看上去和結實的磚沙墻體并沒有什么不同,用手輕輕一敲,就發出咚咚的響聲,隔音效果很差。飛哥之所以租住這樣的房子是為了節省房租,他要把自己干快遞掙來的工資盡可能多地寄回老家去。家里有六十多歲的父母,還有一個上初中的弟弟。父親三年前在果園里伐樹,一棵大蘋果樹猛地栽倒下來,父親躲閃不及,左腿被砸成了粉碎性骨折,現在走路只能靠單拐,干不了重活。飛哥和母親一起支起了一個爐子,每逢趕集時,由母親推著爐子,父親拄著單拐跟著,到集上去擺攤賣麻辣燙。弟弟上初中三年級,學習成績不錯,每年都可以評上“三好學生”。弟弟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個頭還只有飛哥的胸口高,瘦削,腦袋顯得尖尖的。那一天,父親去山上干活,把家里的一只紅殼暖壺遺留在南山坡地邊的草叢中忘記帶回來,到晚上吃飯時才記了起來。父親一拍自己的腦袋自責自己不長記性。弟弟放下手中的碗,對家人說他要去把暖壺拿回來。從南山上的坡地回來要經過獵人峰,獵人峰下有一道山谷,大晴天白天都很少有人經過,遇上陰天更是昏暗,煙霧繚繞。那時候天已經黑透了,沒有月亮,天空中僅僅只閃爍著幾顆星星。小屁孩說完就沖進了黑暗,一路憑著記憶在黑夜里奔跑,一個人穿過獵人峰谷,爬上南坡,從草叢中取回了暖壺,又一個人原路跑了回來。就是那一次,就是那一件事,飛哥覺得弟弟比自己強,他決定退學,去外面打工,把讀書的機會讓給弟弟,他要掙錢供弟弟讀到大學。
工作之余,飛哥有兩個愛好,一是看書,另一個是下象棋。飛哥日常吃穿都很節儉。不抽煙,不喝酒。飛哥年年被評為優秀員工。年底公司組織聚會,飛哥被安排在優秀員工席上,這個時候他也會喝酒,敬領導,敬同事。別人敬他的酒,他都會喝,但絕對不喝醉。飛哥把自己掙來的工資的一部分拿出來買書。他租住的地方雖然只有十幾平方米,但有一個占了大半面墻的書架,這書架是他從淘寶上淘來的,舊,但結實耐用,飛哥把這書架視作可以信賴的朋友。書架上擺滿了書,桌上,床的一邊,抽屜里都是書。書太多了,就覺得時間總是不夠用,很多書沒有時間讀。那就先買下來,存放在那里,有時間了再讀。人家休息日是去同女朋友約會,飛哥的休息日是在出租屋里獨自看書。
飛哥曾經談過兩個女朋友,先后都同居過一段時間,覺得彼此不合適,就好聚好散了,互不相欠。在一起是彼此需要了,來一個暫時的組合,無關乎愛情。城市太大,遠離家鄉,青年男女需要抱團取暖。城市太大,人又太多,各自的選擇愛好、三觀都不一樣,在這座大城市里每一個人都仿佛是從這大千世界采集下來的獨立的樣本,擱在一起時,又都可以合群。但真正在一起,一涉及情感、婚姻這些問題時,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便充分地暴露出來了。飛哥說,婚姻這個東西他也不反對,什么事情不都應該辯證地看它不是,既然在一起不幸福,又何必談婚論嫁。再說他飛哥還有自己的夢想沒有實現。飛哥的夢想是什么呢,這個他沒有向別人提起過,他只是在一本書的扉頁空白處寫到過。他說他的夢想是供弟弟讀完大學,讓父母過上安穩的日子,在這座城市里有自己的一家快遞公司。看看,飛哥還有不小的夢想,他想自己做老板,經營自己的快遞公司。
飛哥住的蛋殼樓的一樓旁邊原來是一個雞窩,經過改造后變成了一間四平方米用白石棉瓦蓋頂的小房間,租給了一個河南來的收廢品的中年漢子。綠漆木門上經常掛一把黑色的永固大鎖,鎖是開著的,“2”字形掛在門鼻上。門外空水泥地上擱著一臺生著紅銹的舊磅,磅上摞放著四只大小不一的砝碼。這磅是用來稱廢品的。磅的右側立著一張一尺來高的方桌,桌面上一天到晚擺著一盤象棋殘局。那個河南來的鄉下漢子下得一手好象棋,自稱少有對手。收廢品空閑的時間多,閑下來,他要么與人對局,招來小區里的閑人觀看,要么就獨自一個人在那里布局,自己跟自己下棋。下到高興處,他猛地停下來,壞笑著,把面前的象棋局造成一個殘局,像一個獵人一樣精心布下一個陷阱,只待獵物奔跑過來,失足掉進陷阱,他才會開心地笑出聲。河南漢子布下的棋局一般人難以破解,不少高手過來坐到棋局旁邊搔首撓耳,舉棋不定,磨蹭半日,難下一子。也有人說有人破過他的棋局。來者是個棋藝很高的老者,老者在漢子擺下的棋局旁轉了兩轉,平靜地坐下來,只走了三步,漢子就輸了。老者的舉動,令漢子目瞪口呆。從此老者就成了漢子的棋友。小區來往的人經常看到漢子棋盤前坐著一個衣衫破舊的老者,兩個人默不作聲面對面坐著,之間擱著一盤象棋的殘局,漢子不下一子,老人也不下一子,他們常常就這樣靜坐著彼此注視良久,把周圍的人都忘記了,把自己所在的這一座城市也忘記了。他們在棋盤中回到了他們人生中已經逝去的那些歲月,回到了他們遙遠的如今早已回不去的老家,那個讓他們記憶十分稠密的地方。人們看到老者同漢子共用一個茶壺喝茶。茶壺不大,里面有漢子泡的濃茶,是從鄉下帶來的粗劣茶葉,泡了一壺,擱在棋盤旁邊,兩個人渴了,一先一后地抓起茶壺,將茶壺嘴對著嘴,飲起茶來。他們喝茶從來不用茶杯,直接對著茶壺嘴喝。
老者是小區外面馬路邊靠撿破爛為生的老頭兒。他至少有七十歲了,穿一身破舊的衣服,臉很黑。那一雙粗糙的大手,手上的皺紋又深又黑,皺紋的深處布滿污垢。老頭兒姓什么,沒有人知道,連河南漢子也沒有問過他,聽他說話是安徽淮北口音。他每天往返于小區和附近兩條半馬路撿礦泉水瓶和舊紙殼盒子。收入好的時候一天可以掙到三十元錢。他沒有錢租房子,就在小區圍墻的拐角處,用破石棉瓦,舊得破了膠皮的電線借著圍墻的兩邊搭起了一個窩棚,窩棚里只有兩床破舊的臟兮兮的棉被,棉被旁邊放著一個蓋子擰不緊的一尺來高的塑料瓶,瓶里裝的是從小區旁邊的公共圖書館里接來的凉開水。
那天傍晚,樓下傳來男女大聲說話聲。女孩說:“完了完了,這么好的風箏今天算是報廢了。”男孩說:“我剛才跟你說了不要往這邊放。”女孩說:“我哪知道它飛得這么快,一下子就躥到樹上。”男孩說:“這一下可好了。”女孩說:“你會不會爬樹?”男孩支支吾吾,說:“爬樹嘛,爬樹其實沒有什么,真的沒有什么的……”
飛哥從樓上的窗戶向下看去。見樓下的楓樹底下站著兩個二十出頭的男女,兩個人同時仰著頭看向滿樹綠葉的楓樹梢,兩個人的臉上都布滿了憂愁。葉叢中棲著一只足有半米長的大蜻蜓,牢牢地掛在了一根樹枝上。在兩個人束手無策的時候,只見不遠處走來一個老頭兒,站在楓樹下,先目測了樹枝的高度,又打量了一下手中竹竿的長度,然后蠻有把握地舉起手中的竹竿,竹竿對著樹葉叢這樣鼓搗一陣子,風箏竟然自己從葉叢中掉了下來。兩個青年高興得一個勁兒地說:“謝謝大爺,謝謝大爺。”
又一天下午,小區公共廁所門前站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小伙子染著紅頭發,腦袋看上去像一只刺猬。他上身穿一件西裝,還打著領帶。只見他在廁所門外急得團團轉,打量著每一個從他身邊走過的人,對向他走過去的人保持著警惕。他很希望有人走過去幫他,又害怕有人走向廁所,尤其是男人,他對每一個向廁所走過去的男人都充滿提防。盡管如此,還是有人陸續走進廁所,有人從廁所里出來。小伙子在廁所門前來回走動,他在等一個人。從小區的大門處走過來一個老頭兒,他的肩膀上扛著幾塊紙殼板,這是他在大廈前的垃圾桶邊蹲守了大半個上午的收獲,今天的收益不錯。老頭兒走在路上面露喜色。小伙子見老頭兒過來了,他一下子高興得快要跳起來。小伙子跑過去,一把抓住老頭兒的胳膊,火燒眉毛似的說:“大爺,有一件事您一定要幫我。我在這里等您很長時間了。”老頭兒把紙板從肩膀上卸下來,人一下子松快多了。他轉身,拿右手在身后的空氣中拍了一把,把三只跟了他一路的蒼蠅給趕走。老頭兒沖小伙子笑了笑,他若是有一個這么帥氣的孫子就好了。他今天的心情不錯。他問小伙子到底有什么事。小伙子說,他剛才上廁所時一不小心把蘋果手機掉進廁所里了。手機一脫手,在瓷磚地面上彈跳著打了幾個翻身,掉到馬桶眼深處去了。小伙子急得頭上直冒汗。這臺手機是他上個星期才買的,花了七千多元。
小伙子說:“爺爺,我不會讓您白白幫我的。您把我的手機撈上來,我給您一百元錢。”他說著,習慣性地伸出自己右手的小拇指,做出一個拉鉤狀。老頭兒覺察出小伙子身上有幾分孩子氣,覺得有一些好笑。不過為防止小伙反悔,他還是要小伙子先把錢掏出來,交到他的手中。小伙子果真掏出一百元交到老頭兒的手里,老頭兒二話不說向廁所的坑邊俯下身去。
五分鐘后,小伙子又一次看到了他那臺心愛的蘋果手機。手機失而復得讓小伙子喜出望外。他一個勁地給老頭兒點頭表示感謝,似乎忘記了自己剛才已經給了老頭兒一百元錢。老頭兒瞇著眼睛把正要離開的小伙子叫回來,說:“你的手機掉得不深,我一伸手就把它拿到了。這錢我不要,干這么簡單的活兒不值一百元,我不能昧著良心掙你的錢。”小伙子接過老頭兒退還過來的錢,身體晃動了一下,他突然有些不認識面前這個老頭兒了。他拿了這一百元,跑到不遠處的小賣店買了一塊香皂,交到老頭兒的手上,說:“爺爺,這個您總得收下吧。”老頭兒接過香皂。小伙子又把一張五十元的鈔票裝進老頭兒的口袋里,說:“爺爺,這五十元您一定要收下,要不然我的內心不安。”說完,小伙子握了一下老頭兒的手,沒等老頭兒再說什么便匆匆地走了。
河南漢子跟老頭兒已經成了一對老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殺將,有時到深夜還為一盤殘局僵持不下。有一次,兩個人竟然爭吵了起來,老頭兒面紅耳赤,一氣之下把河南漢子茶壺里泡好的茶水全都倒在了地上,水泥地上頓時黃汪汪的一片水,順著地面向低處流去。這時飛哥送完快遞正騎著三輪車從外面回來。老頭兒見飛哥過來,停住了爭吵,轉過身來對騎在三輪車上的飛哥說:“你給評一評理,看有沒有像這樣下棋的?都說落子無悔,他倒好,悔一步棋還不算,還要再悔一步,哪有這種下法?”河南漢子也氣呼呼的,臉都紅了,像剛喝了很多酒,見老頭兒搬另外的人來評理,氣不打一處來。只見他一抬手,把面前的棋盤一下子打翻在地,棋子七零八落,四散而逃。從二人的爭吵中可以聽出,他們為了一局殘局下了一下午,雙方仍不分勝負。老頭兒突發奇想,他換了一種走法。漢子一下來了精神,但是他一時還看不出老頭兒的真實意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勉強招架。哪知越到后來,他越占下風,眼看節節敗退,自己的馬炮即將走入死胡同。河南漢子使了欲擒故縱。他的辦法是走一步悔一步,想用這種手段來試探老頭兒的真實意圖。只向下走了幾步老頭兒就被激怒了,這才發作起來。飛哥見兩個老棋友爭得面紅耳赤,說:“二位不要爭了,聽我說一句吧!如果有興趣的話,我來陪二位各下一盤,算是化解二位的矛盾。下完這兩盤棋你們握手言和怎么樣?”這二人見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飛哥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都覺得新鮮。河南漢子雙手抱在胸前,他想看一看飛哥究竟有幾斤幾兩。他不再跟老頭兒計較,把矛頭指向飛哥。漢子說:“我先跟你下。”說著彎下腰伸手把掉在地上的棋子一一撿起來,重新擺好一盤棋。飛哥先走一子,漢子跟走一子。飛哥又走一子,漢子又走一子。二人殺了十多個回合,只見飛哥賣一個破綻,沒想到漢子果然中計,飛哥說一聲“將軍”。這一子下下去,漢子完全沒有想到就這樣被將死在地了。落子無悔,飛哥贏了。輪到老頭兒下時,老頭兒不住地咳嗽,咳到急了,喘不過氣來,把臉憋得通紅。飛哥覺得老頭兒一定患有重病,要不然怎么會把自己的臉咳得像一塊豬肝。但不得不說老頭兒的棋下得穩健。畢竟是歷經滄桑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實誠,考慮得周到。從這一點上講,河南漢子遠不及老頭兒。幾著棋下來,飛哥在內心里已經有了計較,他可以斷定河南漢子是下不過老頭兒的。老頭兒新的一陣咳嗽又升起來,他的后背處像裝了一個風箱,一陣咳嗽過去,眉眼和腮幫布滿了痛苦。飛哥盯住對方的將軍營帳,做出一味的沖殺狀,在己方的營盤放松守備,只饒了一著。老頭兒果然察覺到了飛哥在防范上的“疏忽”,只一個回合,將死了飛哥。兩個人對視著笑了一回。飛哥起身給老頭兒遞一根紙煙,又給在旁邊看棋的漢子也遞過去一根煙。飛哥說:“姜還是老的辣,我甘拜下風,輸得心服口服。”老頭兒看飛哥的眼神變得意味深長。
飛哥重新騎上三輪車離開,車拐到胡同口的大槐樹下,還聽到老頭兒發出的一連串咳嗽聲……
飛哥送完附近的快遞正從樓上下來,剛走出電梯,在單元門口,就聽到一個老人的聲音,“送快遞的。”飛哥回頭,見是那位撿破爛的老頭兒。老頭兒拎著一只蛇皮袋,手上又拿著一根木棍。木棍頭上用鐵絲綁著兩根粗鋼絲彎成的鉤子,形狀如象牙。“您今天的收益不錯吧?”飛哥問。老頭兒說:“就這么個樣兒,能撿多少算多少唄。”這已經是午后了,老頭兒的那只布滿油污的蛇皮袋子的一半還沒有裝到,看來他今天的收入會很少,飛哥的鼻子里頓時生出一些酸楚。老頭兒說:“送快遞的你上次和我下棋時為什么要讓我一著?”飛哥沒有想到老頭兒會問起這個,這讓他有些始料不及。飛哥說:“哪里哪里,我沒有讓您,是您的棋藝高超,我下不過您,我甘拜下風。”老頭兒沉思良久,自言自語地說:“我知道你為什么要讓我這一著棋,你本來可以先我一步將軍的,可是你沒有,我知道你為什么要這樣做。”老頭兒說著眼睛里噙滿了淚水。
從那以后,飛哥時不時地就在小區的馬路上,在自己住的村子的村道上碰到老頭兒。有時是老頭兒先看見飛哥,有時是飛哥先看見老頭兒,這時候飛哥就把三輪車停下來,和老頭兒說一會兒話。飛哥從老頭兒的話中得知,老頭兒是安徽人,今年七十一歲,無兒無女,一個人來這座城市里討生活已經快二十年了。家里原先有三間瓦房,幾年前賣給了鄰居。老家還有一個長他五歲的老姐姐,日子也過得非常艱難。這有很多年沒有和她通音訊了。他一個人漂在這一座城市里,靠撿破爛生存。逢年過節,生活艱難時他也想到過回老家去,可是又沒有路費,家實在是難回。老家的田地已經被征收了,房子沒了。他住過大半輩子的山村幾年前就空無一人了。山清水秀,綠樹成蔭,可是人們不再愿意在那里住。多么美的鄉村,多么清新的空氣,可是人們就是不愛那里,都往外跑,所有的人都出來了,都往城市里跑,村落衰敗下去。老鼠、蛇聚滿村莊,成了名副其實的鼠村、蛇村。好端端的村落再也看不見裊裊炊煙了,再也看不到牧童吹短笛了,再也沒有雞犬聲相聞了。落日余暉下,留在那里的是衰草連天,殘垣斷壁的荒涼。飛哥深知此情。飛哥老家的村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兒時無邊玩耍的那一片青山綠水,如今早已失去了人氣。枯萎,衰敗了。每一年春節回家,總能聽到說某某人搬走了,又是某某人搬走了。搬走的人不再回來,空房子還留在了那里。后來又經常聽說某某人死在了外面,因為舍不得老家的青山綠水,燒成骨灰也要帶回老家安葬。人走了,靈魂仍然希望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出行千里,葉落歸根。
冬天夜里,氣溫驟降到零下十攝氏度。飛哥把他自己的棉被拿出來一床給老頭兒送去。老頭兒住在小區圍墻邊拐角處的窩棚里,天剛剛黑他就躺在了兩床破舊被窩里,把身體縮成一小團,在黑暗中蠕動。飛哥沒有叫起老頭兒,他摸著黑輕輕地把被子放在窩棚門口,然后自己悄悄地走了。
傍晚,飛哥騎著三輪車行走在村道上。老頭兒迎面走過來,臉上還是那一副笑瞇瞇,有些討好他人的表情。飛哥跟老頭兒打招呼,老頭兒頓時立住了腳,像是有話要說。老頭兒告訴飛哥他想寄一個快遞到安徽老家,不知道具體要收多少錢。飛哥見老頭兒說得小心謹慎,就問道:“到底是什么寶貝,看你這么神秘。”老頭兒把雙手在飛哥面前一拍,帶有一些孩子氣地說:“你還別說,你猜對了,真的是一件寶貝!”老頭兒向左右瞧了又瞧,見周圍沒有其他的人路過,向飛哥走近兩步,這才壓低聲音,悄悄地說他今天在天外天別墅區里撿回來一個寶貝玩意兒,可能是個古董。只是瓶口處破了一個小缺口,要是拿膠泥把這個缺口補好,它就是一個漂亮的古董。在飛哥的追問下,老頭兒才告訴他,今天上午他和往常一樣去天外天別墅區撿破爛,在小區的垃圾堆里見到一只兩尺多高,身上印著很好看的山水畫的瓶子。這瓶子并不是用來裝東西的,是白瓷的,里面干干凈凈,瓶身上了釉,釉下印的是天青色的山水畫,一看就是好東西。他就把這個瓶子撿了回來。老頭兒說,他想把這個瓶子寄回老家去,由他的老姐姐把它保存下來,問飛哥寄一個快遞要多少錢。飛哥說,這要看到實物才可以定價格,對于易碎品,還要對它進行精細包裝,具體多少錢,要等驗完貨物之后才可以確定。飛哥讓老頭兒明天上午把他的寶貝帶到所在的快遞公司去,先檢測一下物品的質量、硬度、可攜帶性等方面的問題。
老頭兒抱著他的寶貝走進屋時,飛哥正在柜臺前整理快遞運單,把手中的運單整理好了,他就要外出送上午的快遞。他抬頭看見老頭兒抱著一個大家伙從外面走進來。那是一只敞口瓶子,很像是清代燒制的青花瓷器,上面印有一幅山水圖,看樣子應該有一些年頭,瓶口處碰了一個豁口兒。老頭兒把它緊緊地抱在懷里,儼然把它當成了一件曠世奇珍。飛哥從老頭兒手中接過瓶子,瓶子不重,比飛哥預計的要輕一些。跟同事們說了老頭兒的情況,負責稱重的工作人員就過來給瓶子稱了重量,又交到后面倉庫里去給瓷器件做木制包裝,這些要花小半天時間才可以做好。飛哥讓老頭兒在辦公室里坐下來,老頭兒接過飛哥遞過去的一紙杯開水,剛碰到嘴邊,就迎來了一連串的咳嗽,一陣咳嗽下來,老頭兒的臉咳成了豬肝色。
下午包裝做好了,計算好快遞費,飛哥告訴老頭兒,寄到安徽老家,需三百元快遞費。老頭兒的身體左右晃了一下,隨即答應下來。只見老頭兒從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零碎的紙票子。把紙票子在柜臺上面一張一張撐開,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分,分門別類地疊好。好一會兒工夫,總算整理出了三百元鈔票來。快遞運單上寫好了他老家的詳細地址,在一個鎮上。收件人是他年邁的老姐姐聞蘭香。
夜里九點多了,飛哥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飛哥以為是哪個客戶打來查快件派送情況的。他接起電話。原來是老頭兒。老頭兒在電話里說,他的快遞不打算寄了,要把寄的那個瓶子要回去。飛哥問他,為什么不寄?老頭兒說擔心搬運的過程中會把他的寶貝摔壞,想一想還是不寄。飛哥估計了一下時間,知道這一批快遞還沒有發走。他向公司說明原因,讓這個快遞先不要發貨。第二天上午,老頭兒來公司,取走了他的瓶子。
飛哥去郊區送快遞時接到公司里打來的電話。他從同事的電話中得知老頭兒又把他的那個寶貝瓶子抱來發快遞了。公司里的調度告訴飛哥,老頭兒一進門嚷著要見飛哥,說他要在飛哥手上發快遞。工作人員說讓別人負責他的快遞行不行?老頭兒堅決不同意。他坐在工作間的沙發上一言不發,非要見飛哥不可。飛哥從郊區送完快遞回來已經是下午了,老頭兒還沒有走,一直抱著他的寶貝瓶子守在辦公室里。走廊里來來往往的人都看著老頭兒,問老頭兒到底是誰啊,是飛哥的什么人啊。
飛哥進門時,老頭兒的臉上這才露出了笑容。坐的時間長了,他的腿部有一些不適。他是從椅子上滑下來的,半蹲著,蹲了一會兒,慢慢地向上站直身體。老頭兒瞅住飛哥一會兒,臉上這才打開一片半害羞半討好的笑容。老頭兒站直身體,伸手往自己的胸脯上一拍,說:“這次想好了,寄回去!”飛哥說:“你就不怕在運輸途中把它給碰壞了?”老頭兒十分肯定地說:“不怕,碰不壞,反正它已經是一個有缺口的破瓶子。”飛哥就說,他們公司以前也做過古董運輸,在做好包裝之后,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在運輸的途中碰壞的,這個可以放心。老頭兒說:“我相信你們,我相信你。”
早晨霧很大,馬路前方能見度不到三米。白茫茫的霧把這個早晨打扮得有幾分鬼魅氣。馬路還是昨日的馬路,因為霧大,出行的人少,路上的車也比往常稀。這樣的鬼天氣其實很容易出交通事故。飛哥的三輪車剛駛出胡同口,只見一個黑影向它撲過來。飛哥趕忙停下三輪車。黑影向他靠近,原來是老頭兒。老頭兒見車停下了,他搶上前來,“嘿,早上好!”老頭兒看上去樂呵呵的。飛哥發現霧氣已經打濕了他的頭發、眉毛和花白的胡須。老頭兒告訴飛哥,他天不亮就來這里等候。他是專門來會飛哥的。老頭兒說他要把昨天寄的那個瓶子要回去。飛哥問為什么又不寄了,老頭兒說他昨天夜里想了一宿沒有睡著覺,反復考慮過,這瓶子他還是不發了,他要留著這個瓶子在他的身邊,同他做伴。他在這座城市里沒有一個親人,只有讓這個瓶子同他做伴,要是把它寄回老家了,他又孤單了!飛哥嘆了一口氣。看了又看眼前這個年邁、疾病纏身的老頭兒,心里突然生出了一股酸楚。他趕緊給公司的發貨員打電話,告訴他那個瓷瓶子不發了,讓先扣下來。說完掛上電話,扔下老頭兒,一踩離合器,嗖的一聲便跑遠了。
飛哥想,這個老頭兒好像精神有一點不正常,以后還是少跟他來往了。有幾次飛哥騎三輪車從小區里經過,老頭兒跟他打招呼,飛哥只微微地向老頭兒點了點頭,就開著三輪車過去了。再一次見面時,飛哥假裝沒有看見老頭兒,就把三輪車開過去了。
從那以后,老頭兒就淡出了飛哥的視野。在小區的馬路上,在村道上也不見了老頭兒的蹤影。飛哥想,老頭兒不會再來糾纏了。這一下子,飛哥也覺得清靜了。
寒冬臘月,寒風不分晝夜地在這座城市上空呼嘯,路邊上枯萎了的楓樹葉子被刮得到處飛,被寒風裹挾著,像無家可歸的鳥兒在天空中游蕩,最后飄落在馬路邊不被人察覺到的黑暗角落里。
那只瓷瓶子第三次被送到快遞公司來的時候是一個傍晚,馬路上到處是忙碌著下班回家的人。飛哥的三輪車今天在送快遞的途中壞了兩次,為此飛哥的心情很郁悶。一回到公司,就看到那只瓶子擱在了快遞公司的柜臺上面。調度員告訴飛哥,這個瓶子是一個小時前被一個中年男人送來的。中年男人囑咐調度員一定要交到飛哥手里,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對飛哥說。調度員說著伸手從瓶子里掏出一張紙條,紙條上寫有一個電話號碼。
飛哥按照紙上寫的電話號碼撥過去。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小區里收破爛的河南漢子。漢子的語調低沉,他說讓飛哥到他那里去一趟,他有重要的事當面對他說。
河南漢子收破爛的攤位有了很大的變化。那臺舊磅不見了,象棋攤也收起來了。屋里原來大堆小碼的廢品也被清理一空,男人睡覺的單人鐵架子床還在,一盞海螺狀的節能燈管在拼命地發著光,是一只舊燈管,燈管靠燈頭處顯出一團淺淺的暗紅。一走進屋,一股鐵銹氣夾著油漆味兒撲面而來,屋內顯得又干又冷。河南漢子坐在一張小圓桌邊,就著花生米,喝著劣質的白酒,酒氣飄了滿屋。河南漢子見飛哥進來,也沒有站起來的意思,只是把目光往旁邊的一張空木椅上一丟,示意飛哥坐下,椅子靠背上也帶著酒氣。飛哥想一想,沒有坐,他站在椅子邊上。男人把半杯酒倒進嘴里,說:“老聞頭死了。”飛哥吃了一驚,趕忙問:“什么時候的事?”“三天前的上午。在附近小區里撿破爛,倒在地上就再也沒有起來。警察火化了老頭兒的尸體,只留下一小盒骨灰了。”飛哥心里猛地一沉,沒有想到這些天不見老頭兒,他就出了這樣的事。河南漢子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說:“老頭兒在一個星期前就開始犯頭暈。他告訴我,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樣。他還說,他要是有什么三長兩短的話,讓我把這一封信親手交給你。”河南漢子從床頭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把它交到飛哥的手上。飛哥的心里頓時沉甸甸的。
信封里裝的是兩萬元錢,還有一張字跡歪歪斜斜的紙。是一封寫給飛哥的信。信上說,如果他死了,請飛哥幫他把骨灰寄往安徽老家,就用這個瓷瓶子將骨灰安葬在老家村子后面的祖墳山上。老頭兒還在信上說,這只瓷瓶并不是他撿來的,是他花了二百元從一個城里人的手中買來的,目的就是想用它來盛放自己的骨灰。將自己的骨灰裝進這個自己最喜歡的瓶子里,這是他一生剩下的唯一愿望。看完這封信,飛哥的眼淚不知不覺就滑了下來。河南漢子沒等飛哥問,就從他的床底下捧出一個骨灰盒。“這是老頭兒的骨灰,是我從火葬場里捧回來的,現在交給你了!”說到這里,河南漢子把臉扭到一邊,飛哥發現他已經淚流滿面。
飛哥所在的快遞公司沒有托運骨灰這一項業務。老頭兒的骨灰只能成為一個問題郵件,只能當成一個特殊快遞處理了。老頭兒的老家只有一個年邁的姐姐,行動也不方便。沒有人來領取老頭兒的骨灰,老頭兒的靈魂將在何處安息?
飛哥整頓好行裝,背起裝了老頭兒骨灰的瓷瓶子,駕起一輛從同行那里借來的摩托車,車頭劃破黎明的黑暗,駛向了南去的國道,奔向那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山區……
[欄目編輯:韓愛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