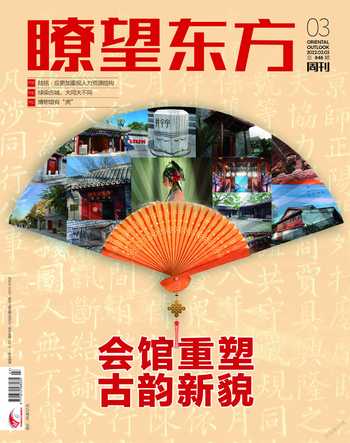館中滿乾坤

《桑梓之情——北京會館文化展》第一部分“歲月變遷”(北京會館文化陳列館供圖)
2021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院內,擁擠的自建房被陸續拆除——這是院落騰退后、修繕前的必備工作。
院落的本來格局得以還原,一塊被石灰抹進墻里的會館石碑露了出來。
“原來誰也沒在意,居民自建小廚房時就把它抹平在里邊了。要不是這樣,石碑可能也就沒了。”出生在紹興會館的法源寺社區原黨委書記、主任李景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紹興會館內歷史上有11塊牌匾和多塊石碑。如今,牌匾已經無存,記載其修建始末的“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石碑則存于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除房屋之外,那塊重新露面的石碑是為數不多得以保留在館內的原始文物。
石碑被抹入墻里,歷史被淹沒于記憶——這是北京眾多會館命運多舛的縮影。
長期以來,會館并沒有被視作一種特殊的歷史建筑而受到格外重視,這一狀況直到近年才發生轉變。為保護會館而奔走的各界人士仍在呼吁:是時候重新審視會館的價值了。
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朱棣做了一個決定:將會試、殿試由南京改為北京舉行。
各省舉子赴京參加會試,人數達五六千人之多。朝廷雖提供被稱為“公車”的車馬費,但舉子們的在京食宿問題還得自己解決。
會館應運而生。如今,北京仍能找到三座有據可查建于明永樂時期的會館。
通過會館,移民得以安頓落腳,同業得以整合組織,城市得以管理有序。在會館中,人們說家鄉話、聽家鄉戲,感受鄉情,并在祭祀先賢供奉神明、聯誼議事等活動中接受道德教化。
將“會館”二字拆開,“會”即聚會,也可以說是同鄉會、商業行會等組織,“館”即場所、房舍。以地緣為紐帶,旅京的同籍士紳官商自愿結成組織,建造會館“以敦親睦之誼,以敘桑梓之樂,雖異地宛若同鄉”。
“明清時期,北京會館最盛時達1300余座。”中國文物學會會館專業委員會會員、《北京會館紀事》作者劉征對本刊記者說。
如果說故宮、壇廟建筑、皇家園林代表的是一座屬于帝王的北京,那么星羅棋布的會館,則代表了一座屬于士紳、商人與平民的北京。
明清時期,首都的地位讓北京的城市移民人口迅速增長,但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極為嚴格,各地來京人員須有事由和投靠之所,否則便要被驅逐出去。同時,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各商業行會也在尋求更有凝聚力的組織形式以應對競爭。
會館便成為了時代與城市的共同選擇。通過會館,移民得以安頓落腳,同業得以整合組織,城市得以管理有序。在會館中,人們說家鄉話、聽家鄉戲,感受鄉情,并在祭祀先賢供奉神明、聯誼議事等活動中接受道德教化。
清朝時,內地十八省無不在京建館。乾嘉兩朝,各府縣在京爭相購買房屋、土地等不動產,以致北京外城房屋基地的價錢都因此抬高了不少。
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副教授張佰明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對于明清時期的各省州府邑而言,在天子腳下建會館的形制和規模,可謂是衡量一地經濟實力和對文化重視程度的最直觀指標。”
據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主編的《北京城市歷史地理》,江西、浙江、安徽、廣東、湖北、江蘇在京都有超過30所會館。這些地區文化昌盛,一代又一代走出會館邁入仕途的同鄉,都會不遺余力地在京城建起一座又一座神圣殿堂,讓家鄉人分享先輩在京城創造的榮耀。
若分類來看,會館可分為主要供官員舉子所用的士人會館,以及供商人行會活動的行業會館,前者集中于前門以西、宣武門以南,后者則集中于前門以東、崇文門以南。
這種布局,正顯示出了舊時北京的城市功能分區——宣南地帶,是士人云集的文化區;前門以東,則是商賈云集的商業區。
“會館是當時北京經濟繁榮的見證。如明代山西人創建的顏料會館,浙東藥商的四明會館,徽州茶漆商的歙縣會館;清代浙江銀商的銀號會館,山西煙商的煙行會館、紙商的臨汾會館、布商的晉翼會館。這些都是當年北京經濟活躍的表現。”劉征說。
北京會館文化研究專家白繼增、白杰父子認為:“在北京的城市發展史中,會館見證了從明永樂年間直至新中國成立的500余年歷程,而這500余年歷程恰是鑄就北京文化的最重要時期。”
如今,會館組織早已隨著時代變遷而消失,會館也喪失了原始功能,但會館文化仍然是北京的一種“影子文化”,歷經500年仍留遺痕。
地域文化正是以會館為依托,交融、升華于北京,從而輻射影響力,并鑄就了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兼容并蓄的城市性格。
以飲食文化為例,從南海會館中,走出了廣東風味的“譚家菜”;從安徽會館中,滯于京中的安徽舉子王致和首創了“王致和臭豆腐”。地方戲曲也通過會館進入北京,從“徽班進京”到京劇的誕生,會館直接參與其中。
劉征以街巷名舉例道:“北京以外埠地名命名的街巷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宣南地區,諸如福州館街、福州館前街、四川營胡同、順德館夾道、姚江胡同(原名姚江會館夾道)等,這些地名都與會館有關,說明會館鄉土文化已深深地烙印在了宣南這塊土地。”
會館給宣南留下的不只是地名,還有以士人文化為主要構成的宣南文化。在近代史上,從會館中蘊蓄出的宣南文化,亦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土壤。
展開宣南的會館地圖,就像展開一幅近代史畫卷。
先從位于西城區米市胡同43號的南海會館說起。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在此起草了“公車上書”之“萬言書”。
同在米市胡同,向南不遠的64號就是涇縣會館。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陳獨秀所創立的《每周評論》編輯部就在此設立。李大釗在此發表《新紀元》社論,提出“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并與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之爭。
在米市胡同以西,如今跨過菜市口大街寬闊的馬路,有譚嗣同曾居住過的瀏陽會館,院內仍保留著他生活過的房屋。
再向西,便是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1918年春,魯迅在館內的“補樹書屋”中寫下《狂人日記》。此后一發不可收,在《孔乙己》《藥》中發出“鐵屋中的吶喊”。
緊鄰南半截胡同的爛縵胡同101號里,則有青年毛澤東旅居北京時寄寓的湖南會館。

臺灣會館
將地圖再放大一些,圍繞虎坊橋路口周圍,還有林則徐籌資興建的福州新館,以及孫中山1912年宣布中國國民黨成立的所在——湖廣會館。
張佰明認為,縱觀新中國成立前的建都史,將北京南城稱為“會館之城”恰如其分,因為會館數量之多、密度之大、與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關聯度之高,沒有任何其他類型的歷史建筑可與之媲美。
“在北京前三門(北京城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的合稱)以南的中軸線兩側,會館區曾形成繁盛的商業中心區和全國知識人才集聚區,會集起數量龐大的社會精英人士,直接推動了北京的文化發展、經濟繁榮和政治變革,說北京會館是首善之區形成過程的直觀教材毫不為過。”張佰明說。
除了文化影響之外,在當代,會館還有哪些價值需要被認識?“談會館,不能忽略因鄉愁而產生的紐帶。”多位受訪對象對《瞭望東方周刊》如此說。
一座座會館猶如城市中的移民島,又在前三門以南匯聚成移民區,成為北京移民文化史的注腳。直至民國時期,會館組織已經瀕臨衰落,但會館仍然發揮著容納同籍旅京人士的作用。
《城南舊事》作者林海音生于臺灣島,幼時便隨父母遷居北京。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林海音都生活在福建籍的會館之中,《城南舊事》開篇的《惠安館》,便是以一處會館為故事背景而展開的。
1990年,林海音回到了闊別40多年的北京,走進南柳巷的晉江會館拜訪老街坊——那里是父親去世后,她與母親長期居住的地方。
林海音回憶,在她童年時,旅京的閩臺人士常常相聚于此,扶持了她們母女的生活。
“想起北平,就像丟下什么東西沒有帶來,實在因為住在那個地方太久了,就像樹生了根一樣。”對于同鄉們來說,晉江會館是共敘鄉愁的處所;對于后來的林海音來說,那里也留下了自己對北京的鄉愁。
如今,晉江會館已經被列為北京西城區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項目名單,并確定將作為林海音文學展示中心開放利用,成為兩岸血脈相通的實證和文化交流的紐帶。
在北京,位于東城區大江胡同114號的臺灣會館已經在發揮著這樣的作用——自1986年起,臺灣會館便交由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管理和使用,成為在京臺胞交流聚會的活動場所。
在劉征看來,實際上,北京的會館是以集群形態作為兩岸歷史文化紐帶而存在的。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清軍戰敗。第二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中國主權受損,民族危機之下,時值乙未科考,住在福建省籍會館的臺灣舉人“垂涕、刺血”,率先上書。
此后,廣東、湖南、貴州、廣西、云南、福建、四川、江西、江蘇、湖北、陜西、甘肅、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浙江等20省人士紛紛加入。短短22天,先后有3000多名住在各自會館中的舉子上書38次,痛陳利害,請愿隊伍長達一里多,反割臺奏章共140件。其中康有為、梁啟超聯絡全國1300多名舉人給光緒皇帝的“上書”最為著名,史稱“公車上書”。
北京的“公車上書”與臺灣抗日行動遙相呼應,兩大陣地影響全國,形成了一場前所未有、波瀾壯闊的全民反割臺斗爭。
“這是國人第一次針對臺灣的全國性、民眾性保衛運動,是‘全民中國臺灣認識’形成的劃時代標志,奠定了國人對臺灣的思想和情感基礎。它就發生在北京的會館群中,不僅僅臺灣會館是聯系臺灣的紐帶,可以說,京城每一座會館都是‘愛國保臺、心系臺灣’的見證。”劉征說。
白繼增、白杰父子在《北京會館研究論綱》中寫道:“如今會館的‘影子’依然在城市中大量存在,作為國家首都、世界城市的北京,城市文化之中早已深深植入了會館文化因子。這一文化因子不僅至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而且一旦與時代和城市需求相結合,便可孕育出新的組織形態、制度安排和城市文化。”
將其放在北京的城市發展史中看,會館發揮的作用并非是個體性的,而是整體性的。
“為了接待各地的科考舉子,各地都有在京的同鄉會館,涉及當時全國各省、上千個縣,為歷朝所罕見。由此便形成了一個群體,而不是某些會館的個體性存在。”劉征說。
因此,不少研究者呼吁,對于北京會館的研究、保護、利用,也應當秉持整體性的思路。

經過環境整治提升后,西城區南半截胡同的入口處,為胡同內紹興會館設置了文化標識(劉佳璇/攝)
張佰明認為:“為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首先要讓公眾知道會館的價值,這需要建立整體認知的概念,針對會館集中的特點建立會館文化帶、會館保護群,或許是切實可行的選擇。”
基于戲曲文化與會館文化的關系,張佰明認為,可以將安徽會館、陽平會館、錢業會館(正乙祠)、湖廣會館、顏料會館等五處帶戲臺的會館連綴起來,“這五處基本構成了現存會館的核心區域。如果能以這一區域為軸心輻射串聯起現存的一兩百個會館,統一編號并制作統一銘牌加以管理,必將以規模效應得到更多關注,充分展示會館文化區的獨特價值。”
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民盟北京市委一級巡視員宋慰祖也曾在2021年北京市兩會上建議,北京應建設會館保護集聚區,制定“會館保護與利用規范”,由市政府主管部門加強調研,實施普查,統籌規劃。
在北京老城南部,宣南地區與前門以東兩個地區,至今仍是會館最為集中、保留相對完整的地區。宋慰祖建議,依據北京市城市總規的定位,可基于此建設“城南會館文化歷史風貌保護區”。在歷史風貌保護區域里,以會館的保護與利用為龍頭,同時對體現戲院文化、故居文化、書院文化、宗祠文化、寺廟文化的歷史建筑進行全面利用,重現北京的各地文化交融、商業繁榮的歷史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