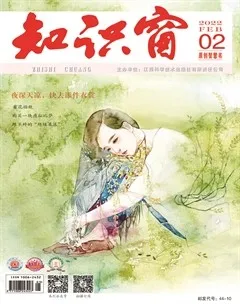以“紅”找“黑”
胡征和

康樂,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生態基因組學領銜科學家,在一次與青年學子的分享會上,他講述了一段關于蝗蟲研究的故事。
群居型蝗蟲是蝗災的根源,同是蝗蟲,群居型蝗蟲身披“黑馬甲”,散居型蝗蟲卻通體是綠色的,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別呢?這個黑色與綠色之別,多年來一直困擾著康樂。他教的研究生也多次報告,黑色肯定離不開黑色素,但沿著這個思路,怎么也不能讓蝗蟲的“綠衣”變“黑甲”。
一次,康樂反復看著群居型與散居型蝗蟲圖,來回尋找其中的差異。突然,他回憶起在中學畫宣傳畫的經歷。畫人的頭發時,他用黑色的顏料去畫。老師看后說道:“康樂,你不能這樣畫,用黑色的顏料畫出來的頭發太死板,就像假發,你要用紅、黃、藍三種原色去調出黑色,再畫人的頭發。”這一回憶把康樂徹底喚醒了。綠是什么?綠是黃和藍的組合呀!黑又是什么?黑不就是在綠的基礎上,調入紅色嗎!康樂馬上找到團隊里的學生,斬釘截鐵地說:“黑色素別找了,找紅色素去!”經過一段時間的尋找,他們終于發現,蝗蟲取食植物時,會攝入一種類胡蘿卜素,在散居型向群居型轉變的過程中,有一種酶上升了,這種酶叫β-胡蘿卜素結合蛋白,它和類胡蘿卜素一結合就是紅色,只要給群居型蝗蟲刺激,就會激發β-胡蘿卜素結合蛋白的表達,一表達身體就變黑了。
如果單從黑色素角度尋覓下去,以“黑”找“黑”,就有可能一條路走到黑。原來,蝗蟲體色的變化是物理三原色原理在生物中的應用。康樂研究蝗蟲,研究出了生命科學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就是表型可塑性。更令康樂高興的是,順著這個思維,他可以將蝗蟲作為人類疾病的模型——人類的許多疾病其實就是這樣的,比如痛風、高血壓、糖尿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逆轉的,這些病其實就是生物的表型可塑性在人身上的一個體現。
一片樹葉可以反映一個春天,一滴水珠可以折射一個世界。康樂對蝗蟲表型可塑性的研究,不僅有利于控制蝗災,還可以為人類的健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