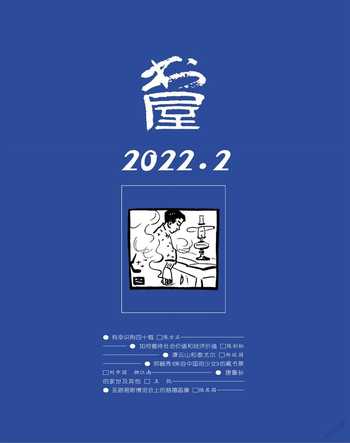抗戰時期葉圣陶的蓉、桂之行
劉偉
“始出西南道,川黔兩日間。鑿空紆一徑,積翠俯千山。負挽看揮汗,馳驅有慚顏。悵然遵義縣,未獲叩君關。”1942年5月15日,葉圣陶由川入黔,乘車過遵義,其時好友豐子愷任教于遷來遵義的浙江大學。老友多年未見,此時亦不能相會,葉圣陶頗為悵然,作詩寄之。該詩凝聚了葉圣陶對朋友的深摯友情,也是他蓉、桂之行的生動注腳。
在抗戰期間,地處西南的桂林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城。很多文化人、知識人云集于此,這其中就包括葉圣陶開明書店的同事們,如宋云彬、傅彬然、陸聯棠等。開明書店內遷后在桂林設有辦事機構,書店的出版經營有序開展,著名的《中學生》雜志也在1939年復刊。遠在成都的葉圣陶心系開明書店的出版事業,更牽掛遠方的朋友。平日他和朋友們書信往來,但見字如面畢竟別于晤談暢飲。時年4月傅彬然自桂來蓉,傅氏極力勸說葉圣陶和他一起赴桂,多種原因促成了葉圣陶1942年的桂林之行。
從1942年5月2日至6月4日,葉圣陶耗時一月有余,自成都出發前往桂林,行路艱難,頗費周折。在旅行中,葉圣陶花費在路上的時間近十天,其中從成都到重慶兩天,由重慶至貴陽兩天,自貴陽至桂林共四天半,車馬勞頓,實屬不易。在旅途中,葉圣陶還要面對車輛乘坐條件簡陋、路途坎坷、車輛難行等諸多苦處。“自古難行路,今難尚有余”道出了葉圣陶的心聲。
從成都到桂林當時行程共分為三段:首先是自成都到重慶,接著從重慶南下貴陽,最后由貴陽至金城江轉火車到達桂林。從成都到重慶,葉圣陶一行乘坐的是敞篷汽車。雖然車輛乃“新道奇”,車況不錯,但是乘坐條件較差,并無座椅,只能胡亂坐于箱子鋪蓋上,毫無舒適性可言,車輛行進中尚覺涼爽,但停車時“即覺日曬,熱不可當”。
當時重慶開往貴陽的汽車班次為每天一班,車票可謂一票難求。為此,葉圣陶一行決定乘坐傅彬然表弟瞿君的運貨車。運貨車開行須履行復雜手續,得到相關部門的批準。影響運貨車出發的原因很多,如汽油票問題等。汽油屬于戰略物資,戰時運貨車都由政府統一調配。成都、重慶、桂林雖然地處西南,屬于戰時的大后方,但是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每一個人頭上。在等待汽車開行過程中,葉圣陶情緒的變化如同坐過山車。聞聽開車消息便滿懷喜悅,當被告知車輛因各種原因無法開車則如冷水澆背。5月10日,在重慶盤桓一周后,葉圣陶得到瞿君消息第二日下午或第三日上午可以開車,葉圣陶“此出乎意料,為之心喜”。然其間又出波折,他們直到14日才登上汽車開往貴陽,在貴陽也同樣上演類似的漫長等待。
由川入黔,過綦江后山路漸多,汽車在山中蜿蜒而行,“登最高處下望,車路之線條如粗筆之涂抹,其曲勢殊難形容。汽車行駛其間,如甲蟲之爬行”。雖然風景優美,然而常常埋藏兇險,“一路見拋錨之車十數輛,有撞毀車頭車廂者”。經黔北釣絲巖,葉圣陶驚聞此處曾有多起事故,心有余悸。貴州常有“天無三日晴”之說,行車途中雨水常不期而至,令他們猝不及防。同行朋友淋成落湯雞,也讓未曾淋雨的葉圣陶心生不快。
更為兇險的是可怕的傳染病——霍亂和突然而至的日軍轟炸。霍亂發生在黔桂鐵路起點的金沙江,葉圣陶“聞人言金城江霍亂盛行,已死數十人,不免有戒心”,所幸他們一行人并無大礙。乘坐列車開往桂林途中葉圣陶遭遇日軍空襲,“詎意六時許車抵橫山即傳有警,車遂停止不進……同行之客則有避至旁山上者。等候兩時許始解警,車復開行”。有驚無險,最終安全抵達了桂林和多年未見的老友相見。
蓉、桂之行是抗戰時期葉圣陶流寓西南生活中的一個鮮活細節。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葉圣陶被迫攜家人離滬輾轉于重慶、樂山、成都多地。抗戰時期流寓各地的生活成為很多文化人的特殊記憶。他們赴各地的具體情形殊異,有的是個體的行為,有的是隨所屬單位前往。但不論怎樣,山河破碎,個體在時代的洪流中風雨飄搖。
葉圣陶此行在重慶、貴陽、桂林三地探親訪友。重游重慶,葉圣陶痛心于山城由于戰爭變得面目全非。朋友賀昌群當時任教于中央大學,他向葉圣陶抱怨生活艱難,以至于要讓夫人外出工作了。資深出版家王云五在白象街一間逼仄的屋子接待了葉圣陶,葉圣陶驚嘆王云五雖處境艱苦但依舊精神飽滿,工作勁頭十足。到貴陽后,葉圣陶拜訪了著名編輯、學者謝六逸,謝氏執教于大夏大學,隨學校內遷貴陽。見面后葉圣陶發覺謝氏比以前消瘦,而他的住房也很簡陋。生活的困頓成為當時流寓內陸各地的文化人共同的境遇,而友誼、事業、責任等又為他們增添希望,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