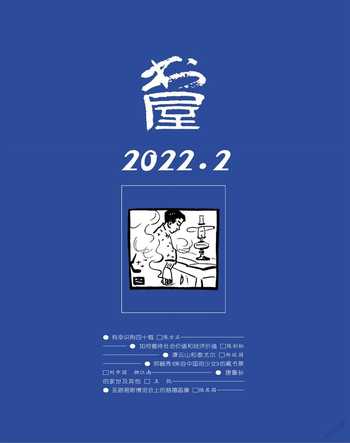唐魯孫的家世及其他
王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臺灣出現了一位新晉的老作家,叫唐魯孫。說他“新晉”,是因為過去從沒有聽說過他的名號;所謂“老”,是唐魯孫操刀為文時已花甲開外,是個不折不扣的老作家。唐魯孫還是個多產的作家,從那時起到1985年去世,出版了十幾部談論故鄉風物、市井風俗、飲食風尚和逸聞掌故的集子。這些集子雖然內容駁雜,但大部分都是以談吃為主。
對于自己的寫作初衷,唐魯孫歸結為一個“饞”字。據說梁實秋讀了唐魯孫的《中國吃》后曾經說過:“中國人饞,也許北京人比較起來更饞。”唐魯孫聽了幽默地回應:“在下忝為中國人,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可以夠得上饞中之饞了。”唐魯孫在親友圈里素有饞人之名,后來他出名了,媒體和讀者覺得再叫他“饞人”有點難以啟齒,于是便冠以“美食家”名號,對此唐魯孫自嘲道:“其實說白了還是饞人。”
唐魯孫出道前雖然籍籍無名,但其家族卻在中國近代史上非常有名。唐魯孫是滿洲鑲紅旗人,高祖裕泰是清嘉慶、道光年間重臣,曾任貴州、湖南巡撫和湖廣、閩浙、陜甘總督等要職,有四子:長啟、長善、長敬、長敘。長啟曾任直隸廣平府知府,長善官至廣州將軍和杭州將軍,長敬曾任四川綬定府知府,長敘官至刑部侍郎。長善膝下無子,弟弟長敬早亡,兩子志銳、志鈞皆隨長善讀書,志鈞后來過繼給長善為子。志鈞字仲魯,就是唐魯孫的祖父,“魯孫”之名即源于此。長敘有兩個女兒赫赫有名,她們就是光緒皇帝的珍妃和瑾妃。從輩分上講,珍妃和瑾妃是唐魯孫的姑奶奶,唐魯孫早年常隨長輩進宮會親,還見過老年瑾妃,因此他所寫的清宮逸聞大都是第一手資料,非道聽途說者可比。
唐魯孫的母親就是曾任河道總督、河南巡撫和閩浙總督的李鶴年之女。唐魯孫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所以他十六七歲就頂門立戶,成了家里的戶主。民國后唐家家道中落,唐魯孫不得不治謀生之學,中學畢業后到財稅學校學習,弱冠之年便已為生計奔波,先后流寓武漢、上海等地,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抗戰勝利后,唐魯孫渡海來臺,初任煙酒公賣局秘書,后在煙廠做事,1973年退休,當時已六十五歲。
退休后的唐魯孫暮年閑居,覺得無事可作消遣,于是提筆為文。至于文章的范圍,他自己這樣說過:“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別人也稱我饞人。所以把以往吃過的旨酒名饌,寫點出來,也就足夠自娛娛人的了。”唐魯孫先是為《中華飲食》和《聯合報》副刊寫稿,后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辟了一個“九老專欄”,邀約唐魯孫與文物專家莊嚴、畫家白中錚、民俗收藏家孫家驥等人一起撰稿。唐魯孫每周寫一篇,如此日積月累,不長時間居然寫了近二十萬字,這些文字后來由出版社結集出版,唐魯孫的寫作由此一發不可收。
唐魯孫文字是白描式的,沒有過多的修飾與渲染,樸實無華,娓娓道來,所寫所涉也大都是1949年前的舊事,這種文字讀起來,自有一股瓜熟蒂落、老成說故的味道,如他在《吃在北平》中所寫:
北平飯莊子,雖然以包辦筵席為主,可是家家都有一兩樣秘而不宣的拿手菜,到了端午中秋或者是年根底下,才把認為可交的老主顧,請到柜上來吃一頓精致而拿手的菜。一方面是拉攏交情,一方面是顯顯灶上的手藝,炫耀一番。
以東城金魚胡同福壽堂來說吧,端午節柜上照例請一次客,準有一道他家的拿手菜“翠蓋魚翅”。北平飯莊子整桌酒席上的魚翅,素來是中看不中吃的。一道菜,一個十四寸白地藍花細瓷大冰盤,上面整整齊齊鋪上一層四寸來長的魚翅,下面大半是雞絲、肉絲、白菜墊底,既不爛,又不入味,凡是吃過廣府大排翅小包翅的老爺們,給這道菜上了一個尊號,稱之為“怒發沖冠”。話雖然刻薄一點,可是事實上確然不假,并沒有冤枉他們。
人家福壽堂端陽節請卮的翠蓋魚翅,可就迥然不同了。這道菜他們是選用上品小排翅,發好,用雞湯文火清燉,到了火候,然后用大個紫鮑、真正云腿,連同劏(廣東方言,相當于“殺”)好的油雞,僅要撂下的雞皮,用新鮮荷葉一塊包起來,放好作料來燒,大約要燒兩小時,再換新荷葉蓋在上面,上籠屜蒸二十分鐘起鍋,再把荷葉扔掉,另用綠荷葉蓋在菜上上桌,所以叫“翠蓋魚翅”。魚翅本身不鮮,原本就是一道借味菜,火功到家,火腿鮑魚的香味全讓魚翅吸收,雞油又比脂油滑細,這個菜自然清醇細潤,荷香四溢而不膩人。不過人家柜上請客,一年一次,除非是老主顧,恐怕吃過的人還真不太多呢。
唐魯孫曾祖長善風雅好文,愛結交名士,在廣州將軍任上,曾招才子文廷式、梁鼎芬與志銳、志鈞一起讀書,后來四人都入了翰林。珍妃是長敘女兒,聰明伶俐,從小就隨伯父長善住在廣州,與志銳、志鈞、文廷式和梁鼎芬都很熟悉。
唐魯孫就是在這樣的家庭中出生、長大,家族里許多長輩如珍、瑾二妃都是晚清民初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個人的眼界、看法不免帶有身世和學識的烙印,唐魯孫出身大族,對豪門大族如何吃喝穿戴,如何禮尚往來,如何節慶典禮,如何詩會雅集,如何閑情娛樂,自然比一般人有更深的體會。成年后的唐魯孫足跡遍及全國各地,與文化巨子、政商名流甚至販夫走卒都有過交往,見多識廣。他的文字以美食為引子,寫花鳥,寫梨園,寫字畫,寫民俗,寫名勝,寫古董,寫煙酒……敘事,娓娓動聽;狀物,不厭其煩;寫人,栩栩如生——沒有歲月的洗禮,沒有生活的磨礪,沒有家學的傳承,這個境界一般是達不到的。
唐魯孫祖上是蘇北泰縣(今泰州)“謙益永鹽棧”的大股東,唐魯孫曾以股東身份寄寓泰縣,經營這家鹽棧。
淮揚多美食,中國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揚菜就出自此地。所謂淮揚菜是指以揚州和淮安為中心的淮揚地域性菜系,覆蓋揚州、鎮江、東臺、泰州、淮安等地區。淮揚菜講究火功,擅長燉、燜、煨、焐、蒸、燒、炒;原料多以水產為主,注重鮮活,口味平和,清鮮中略帶甜味。著名菜肴有揚州炒飯、清燉蟹粉獅子頭、大煮干絲、三套鴨、軟兜長魚、水晶肴肉、松鼠鱖魚、梁溪脆鱔等。淮揚菜天下知名,小吃和點心也風味獨特。唐魯孫雖然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經常在大江南北跑來跑去,吃過不少淮揚一帶的葷素甜咸小吃點心,他最喜歡的還是揚州的蜂糖糕。
蜂糖糕原名蜜糕,據揚州父老傳說,唐朝末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酷愛蜜糕,因為“密”“蜜”同音,大家為避楊行密名諱,所以改稱蜜糕為蜂糖糕。從清代至民國,揚州一直是鹽商薈萃之地。眾所周知,鹽商精于飲饌是有名的,歷史上乾隆皇帝幾次下江南,巡幸揚州,鹽商們供應皇差,打發得乾隆心滿意足。揚州有一鹽商聯合辦事處,叫四岸公所,有位廚子做蜂糖糕非常有名,唐魯孫小時候隨家中長輩去揚州辦事,吃過多次四岸公所的蜂糖糕。唐魯孫當時年紀還小,只記得一塊蜂糖糕比十二寸的蛋糕還要大,可能是籠屜有多大,糕就多大。成年以后,唐魯孫對四岸公所的蜂糖糕還記憶猶新,只覺著松軟香甜,入口根本用不著咀嚼,是甜點里最好吃的一種,后來每次去到揚州,都要去吃一兩回,而且還要買幾塊帶回北平饋贈親友。
唐魯孫去揚州大都是住在左衛街的“如來柱”,晚清、民國年間,左衛街一帶錢莊林立,是當時揚州的金融中心。距離唐魯孫下榻處不遠,有一家五云齋,他家做的蜂糖糕在揚州來說是首屈一指的,后來因為東伙爭執而關歇。五云齋關門后,揚州做蜂糖糕最有名的就屬麒麟閣了,麒麟閣本是經營南北雜貨的茶食店,可是因蜂糖糕做得精致,最后反而以蜂糖糕馳名京滬。當年上海有一家飯館專門以揚州面點招攬顧客,但美中不足的是沒有蜂糖糕,老板于是派人到揚州麒麟閣,想把做蜂糖糕的大師傅挖到上海來。據說上海老板開出了天價薪水,可大師傅重義輕利毫不動心,竟然一口回絕:“年近古稀的人,有碗粗茶淡飯就算了;還想了什么大錢,如果為了多弄幾文,還把老骨頭擲到異鄉,那才劃不來呢;何況老東家待我不薄,就在家鄉吃碗安穩的太平飯吧。”老輩人論交情講道義,一諾千金的作風,的確令人欽佩。至于做好蜂糖糕的訣竅,唐魯孫也打聽得清清楚楚,他在文章中專門記錄下來:“據富春茶社陳步云老板說:‘面粉要用細籮多篩幾遍,同時發面要用真正面肥(北方叫起子)。如果用發粉一類發酵劑發面,蒸出來的蜂糖糕,就像廣東的馬拉糕,發雖發得不錯,可是吃到嘴里,味道就差勁兒了。’陳老對于面點研究有素,所說的話是經驗之談,不是隨便說說的。”
全面抗戰時期,“謙益永鹽棧”被汪偽政權一些高級軍官據為公館,戰后唐魯孫去收回鹽棧,但這些人的眷屬依舊住在里面,一時無法全部收回,僅僅騰出幾間花廳供唐魯孫起居。
唐魯孫在泰縣時,他的一位舊仆啟東特地回來為他操持飲食。啟東是揚州船老板三擋子的外孫,三擋子擅做冰糖煨豬頭,馳名淮揚一帶,“啟東從小寄居外家,所以盡得其秘”。鹽棧有位叫金駝僧的清客,是泰縣有名的書畫家,常和唐魯孫聊天,有一天他向唐魯孫說:“我們讓啟東做一次冰糖煨豬頭來吃如何?”唐魯孫小時在北平聽過《窮大奶奶吃燒豬頭》的單弦,但一直沒有機會嘗一嘗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吃,于是便讓啟東做來一嘗,結果賓主盡歡。
據唐魯孫介紹,這道菜最好要選如東縣農家飼養的土豬,因為這里的豬豬頭皺紋特別少,并且皮細肉嫩,是做豬頭肉的上選,豬齡以將到周歲的幼豬最為適當。買回豬頭后,先用堿水洗涮,去掉豬毛,切成幾大塊,用濃姜大火猛煮,等水滾之后把豬頭撈出,用冷水清洗,換水再煮。如此六七次,此時豬頭已經爛熟,拆骨后放入砂缽,缽底鋪上干貝、淡菜、豌豆苗、冬筍,將豬頭肉皮上肉下放在上面。然后加入桂皮、八角、生姜、蔥段、紹興酒和上好生抽,加水蓋過皮肉,蓋子蓋嚴,用濕毛巾圍好。文火慢煨四五個小時后,掀蓋將冰糖屑撒在肉皮上,再煨一小時即可上桌。此時豬皮明如殷紅琥珀,肉酥而不膩,皮爛而不糜,筷子一撥嫩如豆腐,實乃天下之美味。
當時駐軍揚州的黃百韜與唐魯孫非常熟悉,每次來泰縣視察防務時,都找唐魯孫吃泰縣醉蟹和熬魚貼餅子,聽說啟東擅做豬頭,便約好來吃。恰好有人送來海南紫鮑,啟東誤以為要將發好的紫鮑與豬頭同燒,結果味道異常鮮美,多年以后,唐魯孫對這道菜猶念念不忘,還在《冰糖煨豬頭》中記了一筆:“結果原缽登席,熱鏊久炙,鮑已溏心,其味沉郁,無殊譚廚鮑翅也。恣饗竟日,無不盡飽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