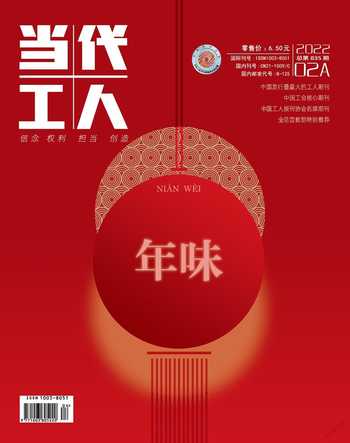一路“漂”鄉(xiāng)
陳年喜
【編輯留言】
千禧年以來,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數(shù)以億計的國人踏上遠行的列車,漂向霓虹燈下光彩奪目的城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達到3.76億,相當于每4人中就有一人漂泊在外。
時代宛若一條巨河,裹挾多少曾經(jīng)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從鄉(xiāng)村流向城市,從小鎮(zhèn)流向都市。在這浩蕩的生活之流中,一個“新身份”破殼而出:漂一族。
“流動人口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說明我們從‘鄉(xiāng)土中國’進入了‘遷徙中國’。”中國人民大學(xué)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表示。
然而,“漂”也是把雙刃劍。社會由靜至動的快速轉(zhuǎn)變,不僅帶來強大動力和人口紅利,改變了生活方式、就業(yè)方式和社會面貌,也隨著急劇變遷和城市現(xiàn)代化的推進,引發(fā)了關(guān)乎歸屬感的新問題,甚至一個時代的焦慮。這樣一份焦慮,似乎只有在新年里,方能煙消云散。實際上,在很多城市中,傳統(tǒng)熟人社會結(jié)構(gòu)正在土崩瓦解,不管是經(jīng)濟上抑或精神上,故鄉(xiāng)、家庭為我們提供的支撐力度都越來越弱。短暫的團聚,猶如繽紛的泡沫,我們從中得以暫時抽離,得到心靈休憩;隨即又要直面那些需要承擔的重量,重新投身路途之中。
一
農(nóng)歷臘月二十五,貴州省綏陽縣這座黔北小城,已經(jīng)有了濃濃的新年氣象。
早晨起來時,天還沒亮,遠山的峰巒和山腳的客棧籠罩著重重的霧氣,霧氣偶爾被吹開的地方,依稀可見青山蒼翠。
我?guī)祥T,匆匆趕往村里的客車點。昨晚已經(jīng)溝通過了,第一趟回縣城的班車6:30發(fā)車,先到先上,滿員即走。按說時間十分充裕,但眼下是回鄉(xiāng)客流高峰期,什么情況都有可能發(fā)生,更何況火車票一票難求,手里的票還是半月前網(wǎng)上搶的,錯過了,改簽的機會都沒有了。
綏陽-遵義-重慶西-西安-丹鳳-峽河,這是我回家過年的路線圖。要提及的一點是,我結(jié)束了四方為家的礦山打工生活后,開始在綏陽縣這家新開發(fā)的旅游區(qū)營銷中心做文案工作。多少年“地區(qū)+漂”的生涯里,回鄉(xiāng)的節(jié)點和事由各不相同,但歸心似箭的急迫心情永遠是一樣的。
從綏陽至遵義的國道上,返鄉(xiāng)的車流擠擠撞撞,像一陣陣波浪奔涌。從車牌看,它們來自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不同省份的不同地區(qū)。同座的當?shù)厍嗄暾f,這些都是成功的年輕人,他們在外面掙到了錢,有了事業(yè),車是他們的回鄉(xiāng)工具,更是身份顏面,只有那些混得一般的人才乘汽車火車,乘飛機和高鐵的多數(shù)也不如這些自駕的出息。
車窗外的細雨一路瀝瀝不斷,兩邊的田地里,油菜白菜小蔥碧綠如茵,這是南方最讓人羨慕之處——一年四季綠菜不斷。不得不承認,經(jīng)過這些年的發(fā)展,尤其是旅游業(yè)的大力投入,十萬大山的貴州早已不復(fù)王謝舊亭臺,城市的規(guī)模與燈紅窗碧自不必說,路途的農(nóng)舍建筑一律是別墅式的了,面積都很軒敞。偶爾幾棟古舊的木板式黔北民居風格老屋夾雜其間,作用似乎只在用以喚醒人們對這片土地過去的記憶與想象。
我下了客車,來到火車站。候車室人潮如海。車站是一個回歸和出發(fā)的地方,車票如一件信物或暗號,人們用它與下一個人或故事接頭。年關(guān)的時刻,似乎每個人背負的“接頭任務(wù)”都格外沉重。
二
劉鑫是陜西安康人,算是我同省不同地區(qū)的老鄉(xiāng)。陜西人習(xí)慣把老鄉(xiāng)稱作“鄉(xiāng)黨”,這是陜西的專用詞。我至今弄不清此詞的由來,大概是比老鄉(xiāng)更親近可靠一層的意思。
劉鑫38歲,看著30出頭,顯年輕。安康是陜西的南國,魚米之鄉(xiāng)水土養(yǎng)人,歲月的風塵在環(huán)境和人面前,就變得遲滯一些。他在貴陽一家酒吧做調(diào)酒師,此前在廣東、江蘇都混過世界。
遵義至重慶西,車程近3小時,劉鑫講了一路。從他的家庭一直講到工作,以及將來。
劉鑫只讀到高二就輟學(xué)了,以他的成績原本是可以上大學(xué)的,但高二時家里出了變故——那一年,他家的房子拆遷了,因為修高速公路,一下得了30萬元補償。20多年前,30萬元可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幾輩人都沒見過這么多錢。錢是壯膽物,有了錢,人的心就變得大了,不安分了,劉鑫的父親和幾位村鄰商量修發(fā)電站,那時國家上下都鼓勵創(chuàng)業(yè)。
本來,劉鑫父親不懂發(fā)電站的事,但他在甘南的白龍江上給福建老板打過工,算是有點兒見識。福建老板在白龍江上修了許多發(fā)電站,入了國網(wǎng),每度電補給2毛多錢,一天一夜發(fā)10萬度電,就是2萬多元,開銀行似的,錢嘩嘩地往包里回流。這是一勞永逸的事業(yè)。
村旁的河水遠沒有白龍江的流量和落差,這就需要修壩引流。大家請來了省里的專家,勘測、論證、設(shè)計、施工……用了一年多時間,集資花去了一多半,電站也建成了一多半。接下來要買發(fā)電設(shè)備,即機組設(shè)備,集資人沒一個人懂這方面的事,他們半輩子懂的只有莊稼。
悲劇正出在這里:他們通過熟人,聯(lián)系到廣東一家工廠,說是這家工廠專門生產(chǎn)這類設(shè)備,廠家也派來了人,考察了電壩,同意供給機組設(shè)備,但要一半現(xiàn)錢,余下的,可以邊發(fā)電收益邊給付。大家背水一戰(zhàn),把幾十萬元打到了對方賬戶上。接下來,結(jié)局如一些人所料,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家里賠光了錢,劉鑫選擇退學(xué),南下打工。這也差不多是同時期陜南無數(shù)青少年選擇的路。
車廂熱若蒸屜。人們脫了外套,敞開了衣扣。一些人在甩撲克,一些人在低頭看手機,一閃一閃的屏幕光映著神色各異的臉。行李架上堆的多是拉桿箱、雙肩包,幾乎已看不到10年前的編織袋、布包裹,這是物質(zhì)豐富和生活前行的實證。
我和劉鑫各要了一桶方便面、一袋烏梅干,在我翻錢包時,劉鑫搶著掃了二維碼,替我付了。
劉鑫說,這次回來就不打算再出去了,父母年齡大了,山坡地再也種不動了。他打算在縣城租個店,辦一個現(xiàn)代型酒吧。在外面闖了十七八年,錢沒掙下多少,要說收獲,就是還說得過去的調(diào)酒洋手藝。這是每天數(shù)百只酒瓶甩出來的,有時把胳膊甩得差點脫臼。
重慶西站到了,我和劉鑫以及一大群人提了行李轉(zhuǎn)車,更多的人繼續(xù)奔向成都、巴中、西昌、樂山,以及更遠的地方。
三
廣源,是陜川兩省的分野地,也是主要的交通站口,下車的人很多,上車的也很多。下車的由此轉(zhuǎn)車回川地,上車的多是在四川打工歸鄉(xiāng)的西北人,他們大包小包、擠擠捱捱,沒有南邊歸來的人群洋氣。地域的工作、經(jīng)濟狀況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乾縣姑娘小劉上來時,身上帶著一股冷氣,頭上頂著幾片雪花,她在車門擠了有一陣,才擠上來。車廂更加擁擠,車廂接頭處也站滿了人,廁所總顯示著“有人”。小劉頭上的雪花很快就化了,變成了水滴,她拿手用力擦了一把,有兩滴甩在了我的臉上,她抱歉地說了句對不起,我們就認識了。
小劉面容姣好,一雙有神的大眼睛。不相稱的是那雙手有些粗糙,這是野外長時間作業(yè)的結(jié)果。在閑話中,她說自己在一家預(yù)制品廠做水泥活兒,這讓我多少有些吃驚。她看出了我的詫異,一笑:“這有啥,既然是打工掙錢,哪行掙錢就干哪行唄。”我連忙說“是的是的”。
車過了安康,天漸漸明亮起來,另兩個人終于支持不住,趴下瞌睡了。窗外的雪更加緊急,也更加厚了,山坡上白雪皚皚,枝頭垂銀掛素。我一直擔心由西安至丹鳳的班車會不會停運,這是雪天秦嶺段常有的情況,就在朋友圈發(fā)了求助問詢,不一會兒,一位在商洛公路系統(tǒng)工作的微友回復(fù),昨天已封路了,今天有個別路線開封,中午時間丹鳳方向估計可通車。
小劉快到家了,顯得有些興奮。長期體力勞動的人,都有一副好體格,何況又年輕,雖是長途勞頓,她并無一絲憔悴。她問我老家哪里,我說商洛丹鳳,她更加有了興致,說她就在商洛讀的衛(wèi)校護士專業(yè)。
小劉說,她畢業(yè)回到家鄉(xiāng)的鎮(zhèn)衛(wèi)生院當護士,一干5年。她業(yè)務(wù)素質(zhì)很強,開始干得順風順水,后來就不行了,衛(wèi)生院分來了很多大專畢業(yè)的衛(wèi)校生,而她只是中專生,文憑上差著等級。后來醫(yī)院實行淘汰制,文憑越高,越有把握留下來,大家都無心服務(wù)病人,拼命復(fù)習(xí)去考級。小劉考了兩年沒考過,受大家白眼。而那些拿到高級文憑的,不要說用藥,扎針也找不到病人血管。小劉一氣之下,不干了。
到站了,告別小劉,終于擠上了開往老家的車。一路上,通往家鄉(xiāng)的每一條小路、每一座山、每一個溪水,還是那樣熟悉、親切。這些山這些路這些溪流,有我童年少年青年的悲喜在其中,我們這一代人,無論走得多遠,是永遠也走不出這些記憶和印跡了。而年輕人已全無這份感覺,他們是失卻鄉(xiāng)愁的一代人,記憶越來越短。或者說,他們的鄉(xiāng)愁已經(jīng)換了內(nèi)容和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