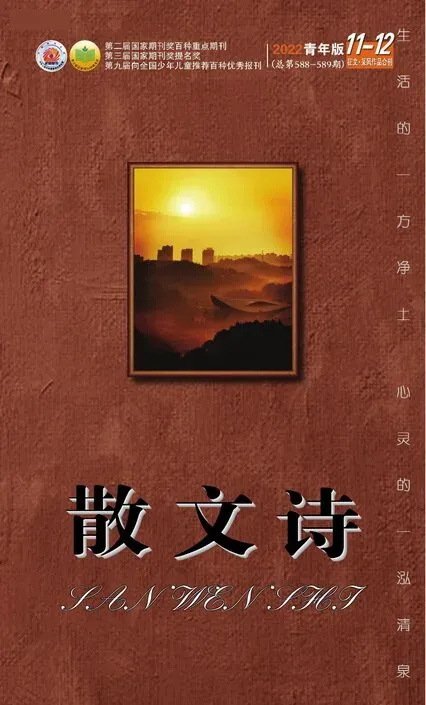腳手架上的螞蟻
陳 興
腳手架上的螞蟻
從農(nóng)村到城市
你有了一個(gè)新的名字
叫農(nóng)民工
城市的樓房再高,也是你們
一手一腳壘成
高高腳手架上
你如一粒螞蟻
在烈日下大聲吆喝
而在低矮狹窄的工棚里
你帶著汗味酣然入夢(mèng)
一次次夢(mèng)回家鄉(xiāng)
你說,城里的房子都太高了
要是矮一些,再矮一些
你翻山越嶺的目光,就能
望見夢(mèng)中的家鄉(xiāng)
望見家門口日漸老邁的爹娘
望見沉睡中,蜷縮著的孩子
城市的綠化地,都種下了
花草和樹木
卻沒有一棵你熟悉的莊稼
春天,你總是與一些
鮮艷的花朵擦肩而過
你甚至來不及與一棵樹話別
就要像一粒細(xì)小的螞蟻,爬上
高高的腳手架
你認(rèn)得那些葉子
每一片都暗藏著熟悉的鄉(xiāng)音
一座城市還無法安放
你睡夢(mèng)中的花朵
而你依然感激每一個(gè)日子
感激來自家鄉(xiāng)的風(fēng)
吹動(dòng)你的衣衫
他們?cè)跇涞紫滤?/h2>
一個(gè)外省漢子在樹底下睡著了
他赤裸著曬得黧黑的上身
只穿一件短褲衩
雙腳沾滿了泥巴
仿佛是剛從泥土里拔出來的
兩條老樹根
更多的他們,也在
這棵樹下睡過
像暮色中,一群疲倦的麻雀
回到了巢穴
不要去叫醒他們
每一聲粗重的鼾聲里
都深藏著一個(gè)遙遠(yuǎn)的故鄉(xiāng)
更多的時(shí)候,他們像一群
爭(zhēng)搶谷物的鴨子
伸長(zhǎng)著脖子,把雇主團(tuán)團(tuán)圍住
討要一份粗重的苦力
一年年過去了,仿佛只有那些
累人的活兒
才能叫醒他們命中的綠葉花朵
挑沙子的外省漢子
濕漉漉的沙子其實(shí)異常沉重
從一樓上到五樓,每走一步
他都十分吃力,肌肉
一塊一塊地鼓凸起來
仿佛就要從古銅色的身上
分離出去
但他卻一刻也不愿停歇下來
仿佛肩上挑著的
是一家老小生活的全部
這些和一擔(dān)擔(dān)沉重的沙子一樣
構(gòu)成了他生命中
所有的痛苦和歡樂
結(jié)賬時(shí),他慷慨地少收了尾數(shù)
這使我感到,其實(shí)一粒看似
粗糙的沙子,也有著它的光芒
結(jié)實(shí),沉重,而金黃
她,或者他們
每天,她和我一樣準(zhǔn)時(shí)上班
有時(shí)是走路。高跟鞋
在水泥路上,篤篤篤地
敲出清脆的響聲
有時(shí)也開著那輛奶白色小座駕
在晨光中發(fā)動(dòng),在晨光中出發(fā)
每次,她都走得那樣匆忙
有時(shí)還帶走了
幾聲蘸著露水的鳥鳴
其實(shí)他們的裝修公司并不算遠(yuǎn)
走路過去,也不過十多分鐘
她坐上那輛奶白色的小座駕
似乎是要一次次給自己提速
再提速
黃昏,當(dāng)她和他們回到
出租屋樓下,除了車尾箱里的鐵鏟、灰刀和卷尺
那些濃重的外省口音,也被
她和他們一道
大大咧咧地搬上了樓
20年
這座南方小城,我認(rèn)識(shí)一個(gè)
外省來的民工,至少20 年了
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20 年前,他和他的幾位老鄉(xiāng)
為我翻砸過舊樓板
挑一袋袋廢料下樓
我認(rèn)得他,不僅僅是
他的身板壯實(shí)得像一頭黑水牛
還因他似乎成了我庸常日子里的一份牽掛
每次路過橋頭
我都要看一看
他是否還在那里
20 年了,他的父母
可都還在世上?
他的孩子,是否
學(xué)業(yè)已成,或已成家立業(yè)?
20 年來,他沾滿泥巴的腳
在故鄉(xiāng)和他鄉(xiāng)之間奔走
走過了多少條漫長(zhǎng)的路!
一群民工在清晨喊口號(hào)
“為了老婆,為了孩子……”
每天開工前,他們
都要站成一小列
由領(lǐng)頭的帶著喊口號(hào)
那聲音并不很整齊
似乎還夾雜著
一些沙啞的成分,因而聽起來
似乎有點(diǎn)滑稽
我看了一眼夾雜在中間的那個(gè)
看樣子年紀(jì)還輕。每次喊到
“老婆孩子” 這一句時(shí)
就微微紅了臉
他的工帽前沿,比別人的
壓得更低一些,似乎是要
壓住一些青春期的秘密
每天清晨,他們都這樣
鼓足力氣地喊著
仿佛所有的幸福和寄望
都在喊聲里回蕩
仿佛故鄉(xiāng)親人也全都在喊聲里
仿佛他們一喊
故鄉(xiāng)的山水就會(huì)響起回聲
再一喊,老屋上的瓦楞草
就會(huì)在風(fēng)中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