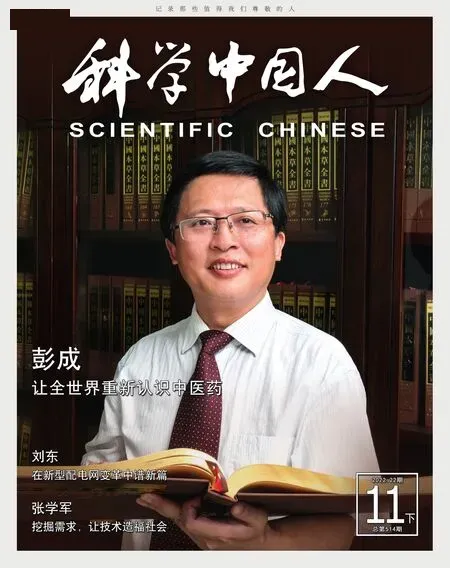求知探索,無問西東
——記中國海洋大學教授侯春朝
張錦玉
假如僅有1塊標準樂高積木,那它只是個長方體積木而已。但如果有6塊這樣的積木,就可以創造出超過9億種不同的組合。“拆開來看平平無奇,組合起來變化萬千”,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海洋大學教授侯春朝的研究對象——金屬有機框架材料(M O F),也是一種“樂高式積木”。金屬有機框架材料作為新一代多孔材料,憑借其超高的比表面積(可達10000m2g-1)、均一化孔道設計、化學可修飾性等眾多優勢在能源轉換、藥物載體、傳感反饋等許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當今研究的熱點。
作為一名功能多孔材料的研究者,侯春朝始終在基于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的可控設計及能源催化領域潛心鉆研,砥礪前行。經過多年探索,他像“魔術師”一樣,將金屬離子和有機配體這兩種“積木”拼裝成結構不同、性能各異的金屬有機框架基功能材料。在擁有無數種可能的微觀世界里,他創造出了一些獨一無二的新材料,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也搭建了一條通往科技高峰的攀登之路。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說文解字》中解釋道:“孔:通也。”多孔材料就是這樣一類由相互貫通或封閉的孔洞構成網絡結構的材料。作為最新一代多孔材料,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研究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末——科學家發現金屬離子和有機配體可以通過配位作用,制備出具有穩定孔道的結晶多孔框架材料;通過更換不同的金屬離子和有機配體,可以合成不同結構的框架材料。截至目前,有多達上萬種框架材料被制備出來。
眾多優勢使框架材料得以在人類化學史上書寫新的“網絡化學”篇章。但在電化學應用領域,框架材料一般是惰性的,需要化學修飾或結構改造。侯春朝就致力于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的電化學應用這一重要能源領域。2012年,侯春朝進入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由支志明院士領銜的“中科院-香港大學新材料研究團隊”,從事金屬有機框架基材料的設計、制備及電化學應用方面研究。2017年,他留學日本,先后在日本國立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 I S T)和日本京都大學化學能源開放創新實驗室(ChEM-OIL)學習和工作,師從日本工程院院士徐強教授(Prof. Qiang Xu)和日本學士院院士北川進教授(Prof. Susumu Kitagawa),這為他日后開發新型框架基材料在能源轉換和儲存方面的應用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侯春朝
在電催化領域,框架材料導電率低且在溶液中不穩定,極大限制了其在電化學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針對這一難題,侯春朝通過可控碳化制備了功能多孔金屬有機框架衍生材料。此類材料不僅繼承了框架材料的高孔性,又憑借良好的導電率和可控催化位點設計,在電催化領域大放異彩。圍繞“無損性多孔設計”和“精準活性位構筑”兩方面,侯春朝進行了一系列緊密相連的創新性研究工作,揭示了界面誘導作用對材料組裝合成和催化性能調控機制,提出了新原理和新概念,為制備新型能源轉換體系提供新思路和方法等。
元代詩人馬鈺在《踏云行·偶爾心明》中提到:“偶爾心明,自然靈感。”自然總能給人以啟迪,侯春朝也喜歡在自然中尋找材料設計上的靈感。一次研究中,他要解決這樣一道難題:傳統多孔材料顆粒之間物理接觸導電性差,若合成多孔聚集體導電性提高,孔道則會崩塌,多孔性下降。如何平衡兩者關系,“無損傷”合成超結構材料,讓材料“運動”起來,使其按照人的想法“順其自然”地自組織拼接成穩定的結構呢?一籌莫展之際,他決定出門走走。彼時,日本街頭開滿了五顏六色的繡球花。侯春朝注意到,這些繡球花上的小花朵層層疊疊地堆積著,卻沒有互相擠壓生存空間,每一朵小花都能自由地舒展它的花瓣、充分感受陽光的洗禮,甚至還通過互相支撐獲得了單個花朵所沒有的強韌,使其得以在風吹雨打中保持它的美麗。一簇簇大的繡球花,遠處看去,平平無奇,細處看來,內有溝壑乾坤,有著多層級結構——這不正像一個超結構材料嗎?基于這一靈感,侯春朝發展了“自下而上(Bottom-Up)”無損傷性金屬有機框架材料自組裝超結構新方法,首次揭示了“無損傷”合成對材料電催化性能提升機制。相關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上,得到了業內專家的極大認可,取得了很大成功。
當被問及如何取得這些創新性成果時,侯春朝回答:“我是個行動派,正所謂‘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對待化學,就是不停的嘗試加偶然的靈感,以前導師也告訴過我,‘化學就是實驗(Chem is try)’。”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
面向國家能源技術方面的重大需求,侯春朝持續深耕電化學儲能研究。當下新能源經濟中,形成了以鋰電池為代表的電能存儲利用體系,但面臨著鋰枝晶帶來的起火爆炸及鋰資源不可逆消耗、電池回收難等眾多挑戰。尋找可替代的高性能、高安全電化學儲能器件是最有希望的突破方向之一。

侯春朝(后排左四)在日本時的團隊合影
一般來說,電池能量密度高,但循環穩定性較差。而電容器有優異的循環穩定性,但儲能效果較差。能否將這兩者優勢互補,研發一種新型電化學儲能器件,使其兼具電池和電容器的優點呢?答案是有的,就是雜化電容器。“這種儲能器件十分特別,一半是電池,一半是電容器,能夠將兩者優勢完美統一。”但這種器件,特別是在水系條件下,要想運行起來,需要克服幾大難題:一是受限于水的理論分解電壓,電池電壓窗口較窄;二是電極材料對鋅離子吸附作用較弱且自放電嚴重;三是電極材料多孔性限制,傳質受阻。“說到底是材料的問題,傳統材料無法克服以上難點,制約了新型器件的開發和利用。”
針對以上重要科學問題,侯春朝利用開放性孔道的新型金屬有機框架基衍生電極材料,研發出了高性能高穩定性的新型水系鋅離子雜化儲能器件。大比表面積和開放性的孔道設計賦予了材料優異的離子傳質性能,其內部磷基鋅離子吸附位點的構筑,有效提升了鋅離子儲存能力,抑制了自放電問題。這種儲能器件能量密度接近常規鋰離子電池,實現了高電壓輸出(達到2伏)和超高的循環穩定性(循環達到30萬次),還具備超強的耐溫特性,在-25℃到40℃之間均表現出良好的性能。文章一經發表,便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在侯春朝看來,他之所以能不斷取得創新成果,一方面要感謝多年來妻子和家人的全力支持、導師的引導與啟迪、同事及學生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則在于長期打下的扎實功底、深厚積淀和永不言敗的精神。他說:“做科研是一場苦行僧般的修行,不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還要學會坦然接受別人的冷眼與質疑,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的精神。”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羈旅他國的這些年里,侯春朝始終關注著祖國的發展,牽掛著祖國的山河。學有所成后,他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回國,將自己所學運用到國家建設中。啟程之前,他請教自己的導師:“回國后,我是否還要繼續從事先前的研究。”導師語重心長地告訴他:“你如果繼續做這一方向,即使再做10年,也不過是在之前的成果上添磚加瓦。未來你一定要推陳出新,即使再難,也要做自己的研究,努力實現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而不是做從1到100的研究。”導師的諄諄教導,侯春朝銘記于心。
侯春朝在外這幾年,也是世界能源環境問題越發突出的幾年,發展清潔能源利用技術勢在必行。因此,他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山東,加入中國海洋大學,計劃將研究與海洋大學平臺相結合,在近海構建海上浮島型一體化制氫平臺,將海上豐富的風力和太陽能資源轉換為電能后,再利用框架材料催化技術從海水中提取綠氫。“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地區占據了中國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大部分,我的夢想是利用海上浮島型一體化制氫平臺,實現海洋到陸地的輻射,供應綠氫協同燃料電池等方式進入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氫能生態的構建。”
“前路漫漫,接下來的任務還很重,我們唯有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以后的路才會更穩、更寬。”侯春朝如是說,“在科研的道路上,將熱愛、身心傾注在你所期望的事物上,必有收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