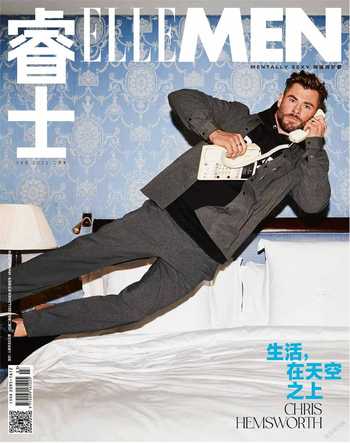普通人的車庫時刻
淡豹

十多年前有位學者看走了眼,建議我去當主持人。我怯懦,不擅長墊話,說不合時宜的話自己還毫無意識,笑的時候往往是出于緊張而不是友善,因此會笑得太滿太久,錯置了肌肉。這位學者是香港人,組織了一場聚會,讓我見見一家總部位于香港的衛視執行副總。
老板問我,平時喜歡看什么書?
我實話實說,小說。老板的失望,或者說輕微的鄙夷,有點溢于言表。
不愛看歷史或者人物傳記?
看得少。那時我還在學校讀書,也選了歷史系的課,歷史研究著作屬于閱讀材料和寫論文時要征引的對象,嚴肅得很,好像不太屬于“平時”的范疇。
副總看了看他的學者朋友,說,也許她可以做做旅行或者美食節目。
這也算是我的一個頓悟時刻——對許多人來說,小說早已脫離了八九十年代的高雅藝術范疇,屬于不太上檔次的愛好,恢復了它最初被發明出來時的大眾文化消費性質。它或者太俗氣,時刻等待著改編成穿越劇,或者太不接地氣,和現實缺少關聯。總之,在商學院的課間休息,除了關于曾國藩或地球改造的小說之外,其他小說都不會提起,都顯得過于女性化了。當時“非虛構”這個詞還不時興,否則老板希望聽到的答案,就能在統一名詞下得到概括了。虛構是女性的、幼兒的、懸浮的、非現實的、打發時間的;非虛構是男性的、成熟的、對現實有洞見能力的、具有生產性的。鄙視鏈大抵如此。
時鐘走到2022年,過去的十多年間綜藝興起,給許多人疲憊和孤單的時刻添上了一群熱烈的伙伴。聚會上我問,有誰看《一年一度喜劇大賽》嗎?朋友們靜了一下說,通常不看綜藝。我排了一下順序,有閑階級的空余時間要交給家庭、體育運動、有價值的愛好,偶爾分給電影或者美劇。國產電視劇,就像以前看小說那樣,太“女”了,太退休老人了。隊列里還排在它后面的是綜藝。在品位鄙視鏈上,看這些的人有閑,但恐怕不大有品,因此更說明其時間不太有含金量。要公開說自己看綜藝就好像說自己的愛好是上網沖浪,跟文藝扯不上太多關系,跟殷實富有、跟品位更離得遠。包年會員就更像甘于躺在泥沼中不打算爬起來,沒有那種“攀爬社會階梯”的能力和熱望了。
如果有機會為自己辯解,我會說,就像不是所有小說都是女主角貌美如花得到霸道總裁的愛那樣,不是所有綜藝都是嘈雜的背景音。《一年一度喜劇大賽》很奇妙,它甚至有點像電影《愛情神話》的調子,又善意又輕盈,里面沒有撕逼和你死我活,友情不需要地老天荒,愛情沒有一見鐘情,偶然也能結出不錯的果實,人的執著不太需要以傷害別人為代價。它也有一種關心吃穿用度的味道——這不是說所有的sketch都是現實主義風格下去一圈菜場便有了故事的意思,而是,你能看到這是一些平平凡凡生活著的人,在很卷的表演界,沒有成為明星,把手里的活兒干得很好,攢了許多才藝正如同職場中攢資格證書,輕輕地嘆息,“在我們這行,順利很重要”。這是職場人才會有的自覺,這和那些明星一起度假或完成挑戰時,編導硬去設計的“情商實驗”完全不處于同一類別。
也因此,這個綜藝反而更像日常生活中的戲劇。整部綜藝下來,它以它的整體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喜劇:一些平凡的好人,經歷過辛苦,也收獲了友誼,并帶給人快樂。
從本質上講,綜藝是給單身者看的。它從不追求完整,隨時可以間斷,因此最適合面對著泡面和外賣看,在地鐵通勤時看,周末邊收衣服邊外放出聲音。普通的婚姻關系下人不需要看綜藝,夜晚與周末總由孩子的作業、由家庭生活里那些聊天與談判、由家庭共同外出占據。但即便是在最“完整”的婚姻家庭里,普通人也需要一些車庫時刻。在那些想一個人靜靜同時又想沉入其他一些什么東西的時候,車庫之中沒法看一本小說,不如看一些人給出善意的、輕盈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