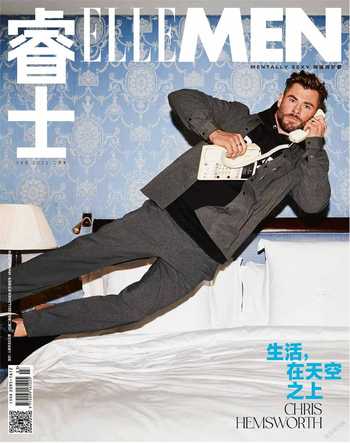為中國火箭拍寫真的人
加禾

空氣像是被撕裂了,巨大的轟鳴聲激蕩在海島上空。火箭發動機燃燒瞬間,2800°C高溫與噴發的火焰,將發射臺下數百噸儲水催為水汽,自兩側導流槽噴涌而出,席卷沙塵直上百米,短短兩個呼吸間,便升騰成遮蔽天幕的濃云。
“整個人毛孔都豎起來了”!站在距火箭發射塔約2.8公里的總裝廠房外,“80后”航空攝影愛好者肖海林覺得,聲浪升格成了具像的海浪,一波又一波,清晰地撞擊在他身體上。

這是中國新一代航天發射場、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龍樓鎮的文昌航天發射場首次發射任務,也是“長征”七號中型運載火箭首飛——2016年6月25日晚八點,在明亮火焰的推動下,“長征”七號遙一火箭自塔架升起,往靜謐的黯藍色深空遠去。
肖海林擠在烏壓壓的人群里,仰頭目送火箭穿云而去,他身邊突然響起了歌聲,漸漸地聲音越來越大,人們用力晃動手中的五星紅旗,“一起唱國歌,唱《歌唱祖國》”。肖海林扶著相機站在原地,“‘唰’一下,眼淚就出來了”。

這是三亞人肖海林第一次親歷火箭發射,在此之前,雖然在海軍航空兵部隊院里長大,但他對中國火箭的認知大多都源自“新聞聯播”。發射現場帶來的震撼感,完全超乎他的預期,“長七”沖上云霄的幾十秒間,擁有多年航空飛機拍攝經驗的他,甚至來不及留下一張自己覺得滿意的照片。
肖海林有些沮喪,他暗下決心,以后文昌每次有火箭升空,自己都要爭取留下照片。他的攝影圈好友、26歲的《航空知識》雜志編輯陳肖,則在發射塔架七公里外的爛尾樓樓頂見證了“長征”七號首飛騰空。不過,和幾位攝影好友蹲守近七小時的陳肖,同樣沒能拍下一張非常滿意的照片。
“因為我們不在火箭跟前,聽不到現場倒計時,只能靠眼睛看,但點火閃光那一下,對第一次看火箭的人來說,可能反應不過來。”當聽到火箭升空時的轟鳴,陳肖和幾個攝影發燒友才真切地意識到,火箭已經點火升空。隆隆巨響在他們耳邊炸開,陳肖只覺得像是有雷云從頭頂碾過。

這也是陳肖第一次拍攝火箭。火箭發射時間窗口短、尾焰亮度過高,因缺乏經驗,曝光數據難匹配,陳肖準備了三臺相機拍攝不同景別,但都沒有達到理想效果。火箭順利升空后,他和身邊好友復盤,討論下次文昌發射任務的拍攝計劃,也是從這次開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拍攝航空題材多年的陳肖決定轉向航天領域,成為中國火箭記錄者。
除開肖海林和陳肖這樣的現場親歷者,更多人是通過遠程方式參與到“長征”七號的首飛故事里。相較酒泉、西昌和太原三個內陸發射中心,地處低緯度濱海地區的文昌發射場,除了擔負著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大質量極軌衛星、大噸位空間站和深空探測衛星等航天器的發射任務,還具有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帶動科普旅游的重要社會作用,相對開放度更高。





“長征”七號發射當天,一些社會機構邀請了不少航空航天領域的KOL進行網絡直播,“90后”星空攝影師葉梓頤也是其中之一。不過,她進入內場時,觀測點已經擠滿了等待的群眾,幾乎找不到拍攝位,最后是一位西北工業大學的朋友給她讓出了空間。
在葉梓頤直播的社交媒體平臺,她的粉絲、正備戰次年高考的“攝影小白”謝元昊收看了“長七”升空的全過程。在這之前,自小愛看航天雜志、收集火箭模型的謝元昊對中國火箭的印象還停留在“長二那種尺寸的火箭”,待他“第一次見到中國新一代火箭”,心里油然生出一種自豪感。
作為中國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的基本型,“長征”七號捆綁了四臺長度為當時現役運載火箭兩倍的助推器,并首次啟用了六臺高壓補燃液氧煤油發動機并聯工作,較其前身“長征”二號F型,起飛質量增重百余噸,近地軌道運載能力從8.8噸提升至13.5噸。
看到葉梓頤分享的“長七”升空照片,謝元昊也對拍攝火箭產生了興趣,并順道記住了偶像口中一閃而過的“西工大”。
這次發射任務結束四個多月后,2016年11月3日20時43分,“長征”五號遙一運載火箭在文昌發射場點火升空,成功將實踐十七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長征”五號是我國現役體積最大、運載能力最強的火箭型號,它實現了液體運載火箭直徑由3.35米至5米的跨越,大幅提升了我國進入太空的能力,被航天愛好者們親昵地稱為“胖五”。
“胖五”飛天,意味著中國航天事業有了探索更遠深空的可能,也為空間站建設、月球采樣返回、火星探測等多項重點航天工程任務奠定了關鍵基礎。不過這次,另有工作安排的陳肖和在產房外等待小女兒降生的肖海林,都沒來得及趕到現場。

半年后,2017年4月20日,文昌發射中心第三次發射任務,“長征”七號再起航,它搭載著我國針對空間站設計建造的首艘貨運飛船“天舟一號”,共同組成了空間站貨物運輸系統,中國首單“太空快遞”正式發出。
兩天后,“天舟一號”完成了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的首次對接,我國載人航天“三步走”戰略第二步收官之戰正式打響,中國空間站時代的大幕正式開啟。
這年仲夏,謝元昊將西北工業大學填報為第一志愿,并順利被計算機系錄取。還未入學,他就申請加入了校攝影學會,成為了一位航天攝影發燒友。
雖然共同錯過了“長征”五號首飛,但陳肖和肖海林與“胖五”的緣分遠不止于此。
2019年12月27日,兩年前因芯一級發動機異常,發射失利的“長征”五號在文昌發射場復飛。在火箭升空穿云的一瞬間,龍樓鎮上的民房樓頂,陳肖拍下了它尾部拖曳著的明亮尾焰——因本科專業與發動機相關,又考慮前一次“長五”失利原因,他特意將鏡頭鎖定在了發動機燃燒時產生的火焰上。
“在此之前,中國沒有人專門拍過火焰。”陳肖記得,“長五”復飛成功,這張火焰照片也隨話題登上熱搜,被多家媒體轉載。
次年5月,“長五”遙四發射任務,因著多年從業經驗和之前的成功作品,陳肖成為國家航天局特約攝影師。這次,他和攝影好友肖海林合作,在文昌發射場外以東約10公里、海拔約300米的銅鼓嶺觀景臺上,拍下了長五升空的第二張火焰軌跡照片。

這是陳肖第三次赴文昌拍攝火箭,卻是肖海林第六次記錄火箭升空,文昌發射中心此前共執行了八次火箭發射任務,他僅因特殊情況缺席兩次。拍得多了,肖海林也有了野心。
“火箭展示的是科技和力量,但沒看到火焰照片之前,你會發現,國內大家拍的很多都是一模一樣,一個‘證件照’,一個火箭點火,一團煙。”作為資深航天迷,肖海林常搜集國內外各種攝影師拍攝的火箭作品,看到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發布的火焰特寫后,他被“深深震撼到了”,火龍肆意在照片上燃燒,連噴薄的紋理都清晰可見,“這帶來的是一種力量的沖擊和直觀的感受,你看到后會覺得熱血沸騰”!
肖海林反問自己,我們為什么不能有這種震撼人心的照片問世?他把想法和搭檔陳肖溝通,“外國有,我們沒有,這不合適”。對方卻早有同感,還定下目標:一定要拍出中國的火箭拉面(火焰特寫)。
六個月后,在國家航天局統籌協調下,陳肖和肖海林獲得了“長征”五號遙五發射的內場拍攝機會。這一次,“長征”五號任務重大,它將搭載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奔赴太空——嫦娥五號是中國首個實施無人月面取樣返回的月球探測器,作為中國探月工程收官之戰,這是當時中國航天領域最復雜、難度最大的任務之一。
得知本次發射消息后,陳肖和肖海林開始準備拍攝方案:研究火箭燃料特性、計算火焰亮度,設置相機參數……因為發射時,人沒法待在相機旁,他們還另設置了一套聲控快門,利用火箭發射時的轟鳴觸發連拍。為保萬無一失,陳肖還將這套方案預先在民用火箭發射現場試驗了一遍。
2020年9月下旬,“長五”遙五搭乘遠望運輸船隊,一路南下安全抵達文昌清瀾港,隨后通過公路運輸方式,被分段運送至文昌航天發射場;11月17日,火箭被垂直轉運至發射工位;11月23日18時30分,開始加注液氧液氫低溫推進劑。

23日晚,陳肖和肖海林在預定位置架設五臺相機,文昌天氣潮濕,天氣預報又稱當夜有雨,兩人只得先用防雨布罩住相機,再用家用帳篷地釘將三腳架拴牢,反復檢查多次后,才從拍攝點撤離。
11月24日4時30分,“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約2200秒后,將嫦娥五號運送至地月轉移軌道。
發射任務成功,指揮控制中心一片歡騰。只能陳肖一人前去回收相機,肖海林等在指揮大樓坐立不安——他既擔心相機捕捉不到精彩畫面,浪費了難得的機會,又怕它們被火箭尾流掃到。“五臺機器,每臺成本都在3萬以上,一下過去,就是快20萬沒了。”

直到陳肖打來電話告知“達到預定目標”,在原地反復踱步的肖海林才緩緩放下心,但又瞬間激動起來,“就特別開心,覺得什么都沒關系了,我都沒問他相機壞了沒有”。
這次拍攝到的“長征”五號火焰拉面照片,被各大主流媒體轉載使用,算是徹底“出了圈”。此后,肖海林常收到朋友的報喜:“他們說,‘肖哥,《人民日報》發你照片了’‘新華社發你照片了’‘《國家地理》也發你照片了’……”
但他記憶最深的照片高光時刻,是返回器安全著陸、嫦娥五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后,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給項目負責部門發來賀電,一本航天系統內部雜志刊載賀電時,用這張烈焰特寫做了配圖。遺憾的是,肖海林沒能要到實體雜志,只留下了幾張別人轉拍的照片,珍藏進自己的手機相冊里。
中國火箭終于有了自己的火焰特寫,陳肖把這張照片也發上了社交平臺。有國外攝影師給他發來私信,對方擁有多次外國火箭拍攝經歷,“他說想拍中國的LongMarch,想像我一樣拍,問我行不行”。
“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說外國人拍,您得找中國有關部門,我說了不算。”陳肖瀏覽著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屏幕上熟悉的火箭照片,想了想補充道:“我全部用中文回他的。”
對眾多中國航天攝影愛好者來說,第一次近距離拍攝火箭,都是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陳肖是,肖海林是,“95后”謝元昊同樣也是。
2020年7月23日,“長征”五號遙四火箭將搭載“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升空。已經成為西北工業大學攝影學會副會長的謝元昊和幾位同學結伴,一行十人提前趕至文昌。
這次”長征”五號遙四任務,發射時間是在正午。熱帶海島七月的陽光蟄得人睜不開眼,按下相機快門的那一刻,等待在距離發射塔架約5公里沙灘上的謝元昊,已經“被曬得站都站不穩了”。
但他認為挺值得,在現場見證火箭發射的震撼,遠非收看電視直播和網絡視頻可比擬。“最不同的是火箭發射的聲音,只有到現場才能體會到。”就像是身處音效最好的杜比影院,“完全360度環繞著的聲音”。
首拍成功,謝元昊和同學把作品發上了社交媒體,被圈子里的“大神”陳肖看到,一來二去,幾人加上微信,成了網友。他們剪輯制作的4K視頻《天問·問天》,在年輕人聚集的B站很受歡迎,收獲了7.5萬次播放。謝元昊還因此結識了兩位志同道合的攝影好友,一道成立了“Space Lens云上天鏡”,由“一群追火箭的青年”組成的航天愛好者社群。很快,更多參與者被吸引而來,他們有的與謝元昊年齡相仿,有的比他還要年輕。

2021年4月,謝元昊所在的西北工業大學攝影學會受西安交響樂團之邀,將為他們4月29日在淇水灣海灘舉行的“大國重器·飛向太空交響音樂會”進行拍攝。這一天,“長征”五號B遙二火箭將搭載著中國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奔赴太空。
天和核心艙發射任務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又一里程碑——標志著我國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成功邁出了第三步,天和核心艙作為空間站成功發射入軌的首個艙段,昭示著中國空間站在軌組裝建造全面展開。
為完整記錄中國航天事業的又一關鍵時刻,謝元昊和他的“Space Lens”首次策劃了聯合拍攝,從銅鼓嶺山頂到淇水灣海灘,他們安排了多個攝影機位,還啟用了很多新設備,嘗試拍攝高清視頻。
4月29日11時23分,海灘交響音樂會現場,曾在中央電視臺多次直播航天發射時陪伴火箭升空、被航天愛好者視為“中國航天祖傳BGM”的《Positive Outlook》前奏緩緩響起。提琴悠遠,圓號低柔,五公里外,“長征”五號B遙二火箭搭載著天和核心艙緩緩升空,奔向它預定的太空軌道,去開辟由美、俄、日、法等16個國家共同建造、運行和使用的國際空間站外,中國人自己的太空家園。
謝元昊和攝影學會的同學在不同機位,記錄下了火箭飛升與交響樂齊鳴的畫面。當火箭沒入云層,《歌唱祖國》的旋律蓬勃響起,謝元昊忍住自己想要參與合唱的沖動,將相機瞄準了歡呼的人群,搶拍下一張經典照片——擠滿觀眾的海邊礁石上,兩面五星紅旗飄揚在一群搖晃著的手機屏幕中,遠處,湛藍的天海連接成一線。“國家每次重要事件,都應該有國旗出現!”這正是謝元昊在腦海中構思多次的畫面。

這次發射任務是陳肖在文昌停留最久的一次。十天里,他全程跟拍了“長五”B遙二火箭的垂直轉運過程,一路將火箭送至發射塔架。
目前,文昌擁有中國最長的兩條火箭垂直轉運軌道,連接著兩座垂直總裝廠房和發射塔架,分別適配“長征”七號、八號和“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火箭在總裝廠房經過起豎、對接、裝配、測試等一系列環節后,將在專屬活動發射平臺上,直接被整體垂直轉運至發射工位,再實施燃料加注、點火發射。
這種“新三垂一體”測試發射模式,可確保箭地接口保持不變,簡化了發射流程,大推力火箭在轉運三天內即可發射,極大提高了發射效率。
“長征”五號的轉運軌道長約2.8千米,完成轉運需要兩個多小時。陪伴“長五”前進的過程里,陳肖拍下了軌道旁揮舞著紅旗標語的中國航天“小藍人”、發射塔架前合影的群眾和腳邊草叢里盛開的花朵。
路上還設有“萬無一失、穩妥可靠”的四字巨幅地標,陳肖發現,“大家都喜歡在‘穩’字那拍,(發射)就是求穩”。雖然視角還算新奇,但他覺得,這種體驗有一次足夠,“因為你還得走回來,能熱得和‘狗’一樣”。
近距離拍攝火箭發射能獲得十分震撼的畫面,但和之前幾次不同,“長征”五號B升空時,陳肖卻第一次將拍攝點選在了淇水灣海灘,“站到普通觀眾的視角去拍了”。遠離了發射場和自己的媒體同行,他的心情更輕松,在海灘遛達時,還遇上了“網友”謝元昊和他的幾位好友。陳肖驚訝發現,這群拍攝火箭的年輕人臉龐比他想象的“更稚嫩”,他們帶著“不顧一切”的創作熱情,從五湖四海奔赴而來。
最讓陳肖詫異的是這群年輕人給他的答案——什么是航天初印象?陳肖出生于1989年,在他初擁有記憶的時代,中國航天事業正處于整理期,他的答案是:美國“土星”五號運載火箭、“阿波羅”登月計劃、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留在月球表面的“大腳印”。
但輪到這幫“95后”“00后”,“航天就是楊立偉,就是中國空間站”,這一刻,陳肖清晰意識到,時代的記憶已經改變了,“現在這代孩子從小的認知就是,中國有空間站,我們自己有‘天宮’,而天上,有中國人”。
文昌位于海南島最東端,2009年9月,中國在此建設首個低緯度濱海發射基地。2014年10月,位于文昌市龍樓鎮的新航天發射場基本竣工,陳肖所在的《航空知識》雜志專門制作了一期題為“文昌:中國的卡納維拉爾角”的稿件。
位于美國東海岸的卡納維拉爾角(卡角)是世界最負盛名的航空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卡納維拉爾空軍基地皆位于此,人類探月第一步的“阿波羅”計劃、近年來的明星火箭“重型獵鷹”,都是從這里啟程。文昌發射場初建時,因與卡角同處海灣,在地理、氣候及旅游資源上有幾分相似,常被媒體和航天愛好者們稱為“中國的卡角”。
“給你們看一眼卡角是什么樣子。”陳肖拿起平板電腦展示卡角的圖片,數十個發射工位密密麻麻沿著海岸布設,“真是太壯觀了”!他接著調出文昌的衛星地圖,指向海邊:“以后這、這、這,全要建新發射工位,未來也會建成卡角的樣子,我們要造更大的火箭!”不過陳肖不再愿意把文昌稱為“中國的卡角”,“就是中國的文昌,未來,我們有自己的‘角’”。
自2016年正式投入使用,截至2022年1月1日,從“胖五”到“快八”(“長征”八號),文昌發射場已經執行了15次“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發射任務。眾多關鍵節點,都有陳肖扛著相機的身影。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記錄者”,見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高速發展,也直觀感受著這組宏大跳躍著的時代音符,如何在一個偏遠漁村敲擊出神妙回響。
2019年12月27日,“長征”五號時隔908天復飛成功。彼時,新聞直播畫面中,發射指揮大廳里身著工作服的年輕姑娘對著屏幕喜極而泣。而陳肖在龍樓鎮民房樓頂,看到夜空被煙花徹底點亮,耳邊是此起彼伏不辨方向的爆炸聲,“整個龍樓鎮都在放鞭炮、燃煙花”。
中國航天的發展步調,正和這座城市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肖海林的妻子是文昌人,他對變化的感知更細膩,“她們(本地人)之前介紹家鄉會說,文昌是著名的僑鄉,有文昌雞,還出過國母宋慶齡”。而現在,一定會加上一句:“我們文昌有火箭發射場”。
與三個內陸發射場相比,文昌緯度更低,火箭發射能更充分“借力”地球自轉,同等條件下,地球同步軌道衛星運載能力比西昌提高10%~15%,衛星壽命也可延長兩年以上。同時,火箭射向1000千米范圍內全是海域,消除了火箭殘骸掉落時的安全隱患。
此外,文昌海運便利,能突破鐵道運輸時隧道寬度對3.5米以上直徑火箭的限制。類似“長征”五號這類大火箭,組織發射前,會由運輸船護送,自天津港出發,經渤海、黃海、東海、臺灣海峽、南海、瓊州海峽等海域,運抵文昌清瀾港,再經由公路運送至發射場總裝廠房。
對航天愛好者來說,文昌更是一個好去處。“太原根本進不去,西昌在涼山,酒泉下了火車,還要在戈壁上再走一兩百公里。”肖海林對比著,文昌地處旅游勝地海南,交通食宿十分方便。“你可以玩兩天吃吃雞,順便看一個十幾億的大家伙發射,不是很美很香的一件事?”
這兩年,火箭發射任務密集,龍樓鎮也成了名副其實的“航天小鎮”。鎮上隨處可見與航天有關的元素,航天大道、航天社區、航天小學、航天酒店,還有各種路標與擺件。每次火箭發射,都是航天愛好者們相聚的盛會,圈子私下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海南是中國的,三亞是世界的,文昌是宇宙的。”
還有更多人找到肖海林,詢問什么時候有發射,去哪里觀看更好?“有以前的同學,也有社會上的朋友。有做生意的、當老師的,有公務員,也有普通打工的……他們多是外地人,最遠的在北京”。肖海林挺詫異,“沒有想到就為了看十幾秒這個,就算進不去(發射場),他們也愿意來看一下”。
龍樓鎮上的民房,樓頂至發射塔架直線距離約4公里,擁有觀看火箭發射的好視野。每到有火箭發射的日子,想在鎮上找個民宿都相當困難。“價格可以媲美海口的四星、五星級酒店”。不單是住宿價格翻了近十倍,“如果去晚了,你想吃(文昌)雞都吃不到,早賣完了”。就連他和朋友之前常爬的爛尾樓和民居樓頂,也有帶紅袖標的龍樓群眾值守,為保游客安全,“現在都不太讓上了”。
肖海林的生活也被火箭改變了。拍火箭人辛苦,器材折損也大,他前后投進去十多萬,妻子一開始挺有意見。“家人覺得火箭每次發射不都一樣嗎,拍一次不就行了,怎么每次都要去呢?”
每次拍攝,陳肖和他都絞盡腦汁琢磨新視角、新技術,時間一長,妻子看到他們的新作,也會夸上一句“拍得確實挺好”。再后來,火箭發射時,肖海林反成了家里多余的那個,接送孩子都不需他考慮,妻子主動催他:“去吧去吧,不要再煩我們了。”
肖海林書房的墻上掛著“長七”和“長八”的火箭拉面照片,這是他與陳肖合作拍攝的得意之作,上面分別留有“長七”總設計師范瑞祥、“長八”總設計師宋征宇的親筆簽名——這是陳肖在一次會議上,特意請兩位總師簽下的。
“范總本科在北航上的,是陳肖的學長。老學長設計的火箭,小學弟拍出了拉面”!肖海林特意將兩張簽名照分享給讀初中的大兒子:“這是老爸拍的,得到了總師的認可。”
兒子是肖海林的火箭拍攝故事最忠實的聽眾,在熱血沸騰的孩子面前,他借機訴說自己對火箭的情感:“你們追星是不是也想要簽名照,我也追星,只不過我追的是這些大國重器的科研工作者。”今年41歲的他用上了一句流行語:“他們才是我心中的YYDS。”
在“長征”五號首飛那年降生的小女兒,剛上幼兒園,還不太能理解照片上噴出火焰的“大白棍棍”意味著什么。不過,“我女兒在家能翻天,但她知道墻上這兩張相框,只能看,不能動”。
采訪時,鬧騰的小女兒正纏著肖海林玩鬧,被他一把撈上膝頭,逗弄著:“你喜不喜歡火箭?”
“喜歡。”女孩的聲音從電話那頭,清凌凌地傳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