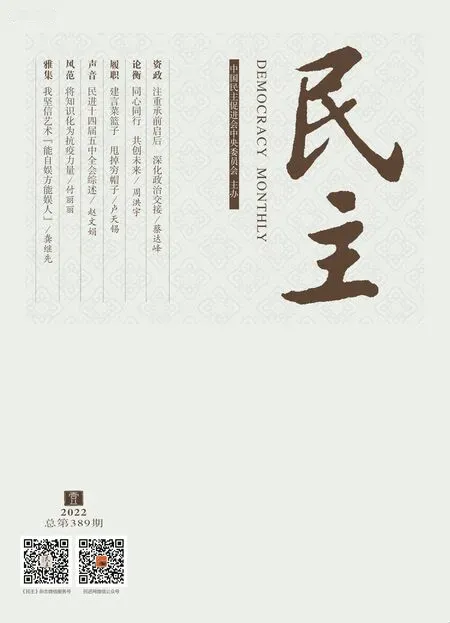我堅信藝術“能自娛方能娛人”
□龔繼先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巖 撰稿
我在中央美術學院讀書的時候,已經開始閱讀藝術類書籍,書法的、建筑的、園林的,甚至武術的都讀。看多了,覺得中國藝術都是一個道理,叫“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后來再看很多畫論、畫史仍然脫不開這個說法,也就是說,無論如何創新,畫畫必須先有規矩。
中國人講“道法自然”。萬物皆有規律,自然中四季輪回,春種秋收。藝術也是一樣,必須守法自然,先了解規矩,否則再怎么創新也無濟于事。許多世界級的大畫家,印象派的也好,現代派的畢加索也好,中國的齊白石、潘天壽,都是功底扎實,傳統繪畫爐火純青之后,才尋求突破,開宗立派。他們看似已經進入藝術的自由王國,沒有規矩了,其實都是在規矩中做到最大的自由。從爐火純青走向登峰造極,勤奮也好,天賦也罷,始終離不開藝術規矩。
所謂知易行難,道理明白了,還有個落筆入畫、踐行于紙的過程。有句話叫“眼中有神,腕下有鬼”。總是做不到,但是努力去做,就會靠近一點。過去我們看京戲,譚老板的《烏盆記》,老藝術家披著黑紗上場,閉著眼睛就開唱,搖頭晃腦,韻味十足,看不到一點規矩。但他也是規矩中來的,熟能生巧,才能信手拈來。梨園圈里,小徒弟少年學戲,每天勤練苦功,拉云手稍微差點準頭,師父的戒尺就落身上了,下手毫不留情,提醒弟子遵從規矩和分寸。
中國的藝術原理相通,詩詞也是這樣,五言絕句,七言格律,各種詞牌,平仄就是其中的規矩。沒有平仄就沒有藝術性,韻腳都不押,已經不稱其為律詩了,更何談藝術。
我剛讀中央美院第一天,系里讓每個人交一幅畫,裝框掛在走廊給大家欣賞,我交了一幅1957 年仿八大的畫。苦禪先生看到了,對我說:“你年紀太小,不要學八大。”老師的話就是藝術規律,他要我先扎實打牢基本功。
遵守藝術基本規律之外,還要博采眾長。在藝術道路上,我比較幸運。讀大學時跟隨苦禪先生、可染先生、雪濤先生、淺予先生學習,聽各路名家講座,看齊白石先生的畫,研究漢魏碑拓,由此打下了扎實的北派筆墨和審美功底。到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后,開始接觸海派,看謝稚柳先生和唐云先生畫花鳥,也很喜歡任伯年、吳昌碩的作品,能看懂其中的精彩之處。
南北藝術兼容并蓄的機會求之難得,機遇使然,我碰上了,自然倍加珍惜。我一直秉承一種堅定的藝術態度,就是抓緊時間多看多學。
我愛古人,也愛今人;愛江南的平淡秀潤,也愛北方的質樸雄渾。同樣畫花鳥,江南的畫法與北派全然不同。北畫氣魄宏大,壯闊古樸。但萬事都有個度,所謂過猶不及,如果過了,就顯粗野。南畫靈秀滋潤,俊逸輕盈,這是江南煙雨,空靈山水的滋養。但需避免瑣碎、小家子氣,不能過分甜俗。孔子說,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就是江南的靈秀雅致,質就是北方的渾厚壯闊,畫的氣韻全在于度的把握。
這就是哲學上辯證統一的道理。中國畫的發展同中國的書法、篆刻、詩詞、戲劇、建筑一樣,都是基于中國的傳統哲學和美學。它反映的是中國獨特的宇宙觀和審美理念。縱觀中國數千年的藝術理論,雖然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發展變化,但總的一點還是離不開藝術辯證法。

先人認為宇宙是由一陰一陽、一虛一實組成的整體,太極這一圖式恰好樸素而本質地表現了宇宙生命的根本規律。在其指導下衍生的形象、筆墨、虛實、節奏,正是作品內在的生命力和氣韻的體現,一種對立和諧的整體結構。
近些年,我書法寫得多了,體會到中國畫和書法同是一種空間的創造。書法是類似音樂舞蹈的節奏藝術,具有形線之美,有感情和人格的表現,每個字通過點畫構成一個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單位。若字寫得好,用筆得法,就創造出一幅有生命有空間的藝術品。若字與字、行與行能“偃仰顧盼,陰陽起伏,前后相承”,這幅字就有了生命之態。
所謂氣勢、結構,所謂力透紙背,都是表現書畫的這一空間意境,因為一切動作都以空間為條件。畫境與書境相通,一筆下去,猶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由此筆筆相隨,筆筆相生,在自由的空間里使情感通過筆墨得以更好發揮。因而,創作花鳥,我喜歡簡潔利落的京劇式表現。因我很早就明白,花鳥的創作并非僅限于表現自然本身,更多是以此為媒,“緣物寄情”“借題發揮”,以表達畫家的人格感情和審美情趣,其早已超越了花鳥本身的描寫。
數點桃花寓意著無邊春色,二三水鳥啟示著自然的蓬勃生機,一花一鳥間,可以發現無限,表現無限。它是超脫的,但又不是出世的;是空靈的,又不是寫實的;以氣韻生動為理想,但又充滿著靜氣。總結下來,就是超越自然,又最切近自然、最心靈化。笪重光說:“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這種傳統的空間處理方法,不僅使畫面更加空靈,也給欣賞者留有更多聯想空間,一幅書畫,沒有了想象空間,就失卻了靈魂。
我堅信藝術“能自娛方能娛人”,自己都不信、不認可,怎能讓他人接受?畫花鳥尤其如此。我畫大寫意、小寫意、工筆、指畫,均是興之所至,手隨心動,想畫什么就是什么,始終抱著一種游戲的心態,不為名利所累。但這并不妨礙我在藝術上做艱苦的探索和努力。所謂“得之雖苦,出之須甘”,搞藝術的,要始終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
書畫是心畫,個人閱歷修養性格追求審美不同,畫出的畫自然不同。我們常說“真”“善”“美”。作為一個畫家,畫出本心是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的事。心存淡泊,不與人較高下,潛心作畫,求真存善,自然能創作出時代不同的美的作品。
再來說藝術突破的問題。我讀書的時候,孫墨佛講孫過庭的《書譜》,有句話我印象深刻,“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這是書法學習的過程,于繪畫哲學相通。直白地說,就是事物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一個不斷揚棄的過程。
我最早學于非闇先生的工筆,后來學小寫意、兼工帶寫,再跟苦禪先生學大寫意,我的興趣愛好非常廣泛,一段時間對某一項感興趣總是集中練習,練一段時間,但有時好久都沒進步,似乎到了山窮水盡之處,我就停下來思考,看書看畫冊。我買了很多畫冊,大多在這個時候才去看。邊看邊想,往往又有領悟,倘再動筆,或許能上一個臺階。思考和動筆并行,是進步和突破的基礎。我常說,畫一張成一張,特別順手,有時未必是好事。畫不下去了,也許是遇到瓶頸,是突破的前夜了。
從事半個世紀的繪畫之后,創作中我越來越傾向于用減法,去除冗余,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之境。我追求單純,卻在豐富上下功夫;追求雄渾,卻在含蓄上下功夫;追求靜境,卻在筆墨靈動上下功夫;追求充實,卻在虛白處下功夫;追求骨力雄強,卻在水墨暈章上下功夫。
成為畫家的道路漫長而修遠,要過寫實、傳神、妙悟三關,要走過由生到熟,再到生(天趣)三個階段,這是畫家綜合修養自然發展的結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絲毫勉強不得。藝術的創作是一種砥礪,更是一種享受,但真正能達到妙境的大家少而又少。其實對藝術家來說,無論是誰,只能是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