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舉人七百進士文化解讀
龐思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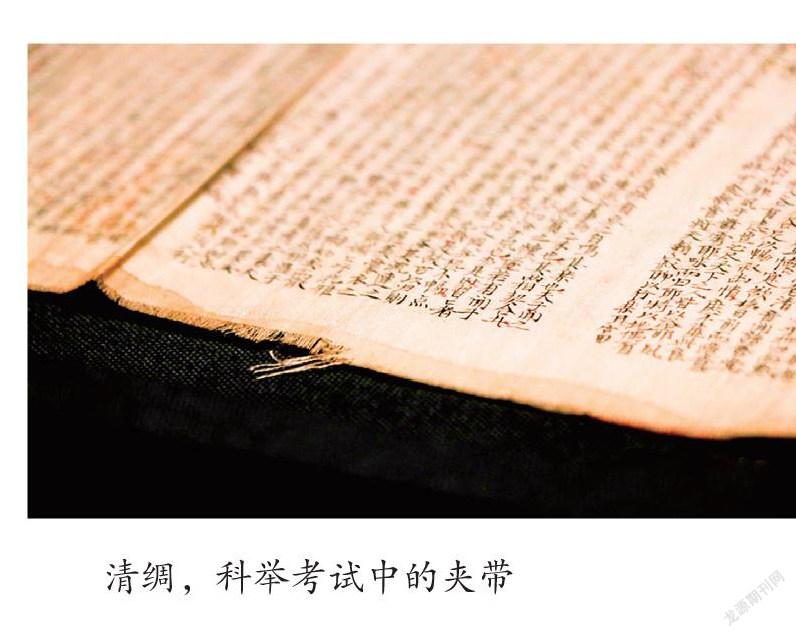
明清之際,貴州人才蜂起,廣大貴州士人以“萬馬如龍出貴州”之勢,角逐于華夏的科舉場上,創造了“七百進士、六千舉人”“三鼎甲”的驕人成績,被人譽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當人們驚異于貴州的這一文化現象時,不難從歷史中得到答案:那就是歷史的際遇造就了貴州,是貴州日顯重要的戰略地位造就了這一文化現象。筆者就此一一解讀。
明代的治黔方略
貴州在元代分屬湖廣、四川、云南三個行省,沒有獨立的身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元軍殘余勢力之后,下令在通往“滇之喉”的驛道一線設立衛所,屯兵二十萬,實行軍事管制,旨在鞏固云南邊防及穩定西南政局,并在今天的貴陽設立最高軍事機構——都指揮使司。永樂十一年 (1413年),貴州“建省”,標志著明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高度重視,亦標志著貴州新時代的到來。
朱元璋頗有頭腦,治國有術。在其君臨天下之后,便把教育作為基本國策,作為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他曾說:“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對于經濟文化落后的貴州,他在加強政治、軍事統治的同時,強調“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之為先”,責成駐黔官員“廣教化,變土俗,使之同于中國”。
功不可沒的治黔官員
在明朝歷代派駐貴州的巡撫、按察使、提學副使,以及府、州、縣、衛較低級的官員中,大多數官員遵循國家的大政方針,以振興黔中文教為職志。他們建文廟、辦書院,大力提倡儒學,以此“作養人才”。其中最為黔人緬懷的有提學副使毛科、席書、蔣信、徐樾、吳國倫,巡按御使王杏,以及巡撫王學益、林喬相、阮文中等。值得一提的是,貶謫黔中的官員王守仁、張翀、鄒元標,他們在黔期間,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著書立說,興學育才,從而推動了貴州文教事業的發展。
正是在入黔各級官員及謫官的不懈努力和助推下,貴州文教勃然興起,各地相繼創辦了二十余所書院。據記載,從明初至崇禎三年(1630年)的二百余年間,貴州共建官學四十七處,各府、州、縣、衛、司“偏(遍)立學校,作養人才”“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臺諫之選者,往往文章氣節與江南才俊齊驅”。
反哺故土的貴州籍官紳
在這場文教振興的運動中,不少貴州籍官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興隆衛(治今黃平縣重安區)周瑛,致仕后在家鄉創辦明代貴州第一所書院——草庭書院,培養桑梓人才;再如思南府水德江長官司(治今德江縣)田秋,鑒于貴州士子赴云南鄉試行途艱難,疏請朝廷在貴州開科鄉試,此舉是貴州文教的轉折點;又如思南府水德司(治今思南縣)李渭,是王陽明再傳弟子,貴州著名理學家,有“中朝理學名臣”之譽,其辭官還鄉后著書立說,并在思南創辦中和書院,開黔中講學之風;再如清平衛(治今凱里市爐山鎮)的孫應鰲,亦是王陽明再傳弟子,系明代“四大理學家”之一。在其以病辭官歸里后,專事著作,并在家鄉建“學孔精舍”,弘揚陽明心學,教育家鄉子弟;又如王陽明再傳弟子馬廷錫,致仕后主講于貴陽文明、正學、漁磯三所書院,畢生以培育黔中士子為己任;又如都勻衛的陳尚象,在朝不畏威權,在野熱心貴州文教,凸顯貴州士人的稜稜風骨。在其罷為庶民的日子里,不僅與同門弟子創辦南皋書院,而且參與纂修萬歷《貴州通志》……這樣的官紳不勝枚舉,他們熱愛桑梓、反哺故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
貴州進士、舉人之翹楚
翻開歷史的畫卷,不難發現,自明正統四年(1439年)貴州赤水衛(治今畢節縣赤水河)人張諫中進士后,黔中才俊紛紛走出“蠻陬之地”,來到京華問鼎科名,書寫了一百零七名進士的不俗成績。正如清末貴州詩人陳田在《黔詩紀略》中所說的:“貴州自成祖開省迄于神宗,閱二百年,人才之興,比于上國……”在這些進士中,不少人成了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國運的舵手。如赤水衛張諫,思南府申祐,平越衛(治今福泉縣)黃紱,貴州衛(治今貴陽市)徐節,貴州都司興隆衛(治今黃平縣重安區)周瑛,平溪衛(治今玉屏縣平溪鎮)侯位,思南府水德江長官司(治今德江縣)田秋……他們猶如一顆顆明星,在華夏的星空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據史冊所載,明代貴州鄉試舉人達一千七百二十名,他們之中不乏優秀人物。如“橫槊賦詩”的將軍詩人越其杰,譽滿江南“詩書畫三絕”“崇禎八大家”之一的楊文驄,統率南明王朝西南五省被譽為“南天一柱”的抗清名將何騰蛟,被孔尚任驚為“其人”“其詩”酷似屈原、杜甫的吳中蕃……他們出眾的才華,嵚崎磊落的形象,改變了華夏士人對貴州的偏見,凸顯貴州士人的風采。
清代入黔官員的貢獻
清襲明制,為治政所需,統治者更加重視教化。康熙初年,貴州巡撫田雯疏請在永寧、獨山、麻哈三州及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今鳳岡)、銅仁、永從(今從江)九縣建學育才。之后又陸續在各府、州、縣、廳設立學校。至此,貴州所轄的十一府四十州、縣均設有官學。自康熙、雍正年間中央政府在貴州實行“改土歸流”后,完全打破了過去土司、流官并治的局面,官學得以深入到“王化未及”的苗疆。這是貴州第二次文化勃興的政治因素。其次,清初為追擊南明殘余勢力及平定三藩后,大批軍人、官員及移民紛紛涌入貴州,他們帶來了先進的耕織技術和經商方式。這些移民在各地興建的會館,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這是其經濟因素。
另外,清政府派往貴州的巡撫、提督學政及知府中,不少人是飽學之士,如田雯、鄒一桂、洪亮吉等。他們不僅學識淵博,而且致力于貴州的經濟和文化。以洪亮吉為例,其人系乾隆年間著名的詩人、史地學家和散文家。在其擔任貴州學政時,為振興貴州的教育,洪亮吉走遍了黔中的山山水水,視察了各地的教育狀況。乾隆六十年(1795年),貴州乙卯科鄉試揭曉,洪亮吉獲悉貴陽貴山書院生徒中舉27人的喜訊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即興賦五百字長詩以賀。
家族文化與師承關系
清代貴州的人才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并以家族、親緣和師承關系為主導。究其原因,是這些豪門大姓掌握著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重視家學、家風的傳承,視獵取功名為正途。為此,筆者查閱和研究了貴州的一些名門世家的資料,發現不少人家人才輩出,屢登科名,現將不完全的統計抄錄如下:
明清兩代,貴州的世家為科舉輸送了大批的舉人、進士,帶動了貴州文教的振興,為明清貴州的科舉史增光添彩。銅仁的徐穆、陳珊兩大世家,前者有《銅仁徐氏十二世詩集》傳世,后者其家科甲鼎盛,子有“八英”之譽;貴陽有潘潤民、王尊德、徐卿伯、許一德四大世家,其中的潘潤民,居官清廉,民諺有“潤民不潤己”之語。有清一代,貴陽的何孟熊世家大放異彩,涌現出九位進士,為黔中之冠,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進士”之稱。“黔南士族冠冕”周奎家,“一門七進士”,被貴州巡撫賀長嶺大加贊賞。
除了家族文化外,還得提一下師承關系。清代省城貴山書院有“舉人進士的搖籃”之譽,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嘉慶十一年(1806年)的54年間,先后由陳法、艾茂、張甄陶(福建籍)、何泌、翟翔實五人執掌教席。由于他們學養淳厚,道德高尚,致使“士行蒸蒸日上,文學、科名日盛,貴陽人士遂冠于西南”。為了緬懷他們對貴山書院的卓越貢獻,后人譽其為“三先生二山長”。
清代的貴州進士與舉人
“君看縹緲綦江路,萬馬如龍出貴州”。這是清代四川翰林趙堯生在《南望》詩中評價貴州大詩人鄭珍的《巢經巢詩集》的兩句詩。趙堯生以“萬馬如龍出貴州”來比喻黔中才俊氣勢恢宏地沖出故鄉,到華夏廣闊的天地中去尋求發展。正如趙堯生所言,清代貴州中進士621人,中舉者6000千余人,而且出了“兩狀元一探花”。和四川、云南兩省僅出了一名狀元相比,對于一個被世人視為“蠻夷之地”的貴州來說,不僅值得驕傲,而且令華夏士人為之嘆服。
清代貴州的進士不乏優秀人物,而且才華橫溢,頭角崢嶸,如“中興名臣”丁寶禎(織金籍),一生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誅殺宦逆,整頓吏治,興修水利,興辦洋務,是一個“清絕一世”的“中興名臣”。再如李端棻(貴陽籍),他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倡導者,戊戌變法的堅定支持者,他畢生致力于中國的憲政改革,是貴州的民主先驅。
明清貴州“六千舉人七百進士”,是貴州秀麗山川孕育出的嵚崎磊落之士,亦是我們華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歷史證明,這些貴州士人的精英分子,他們恪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理念,在人生的道路上“立德、立言、立功”,他們的勛業偉績和人格魅力,已載入史冊,成為貴州人民的精神財富和動力,鼓舞著世代黔人勇攀高峰,再創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