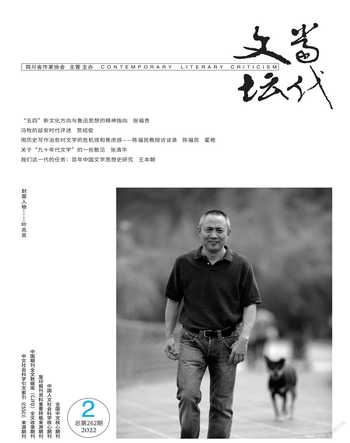夏商小說的戲劇性
張靈
摘要:夏商的小說特別是中短篇小說常常表現出一種戲劇性的藝術特質。這種特質可以從其小說呈現出的對生活片段的截取、敘述姿態或故事形態的舞臺現場感、尖銳的主體間性沖突或人性分裂以及對人類生活的一種無法逃避的悲劇性基因——偶然與無常的執迷與敏感等角度來表征。也正是這種戲劇性使他的小說具有了更大的張力與強度,小說的篇幅或體量減小了,但其思想情感容量和藝術沖擊力反而更大。這既反映了現代小說的特點,也顯示著夏商在小說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兩方面竭力探索的先鋒姿態。
關鍵詞:夏商;戲劇性;主體間性沖突;人性分裂
夏商的小說,特別是他的中短篇小說常常表現出一種戲劇性的藝術特質,它們并不追求對一個故事作從頭至尾的和盤托出,而是善于截取生活中富有戲劇性的情境或心理事件來構筑作品,人物的那些從萌生某種感覺到產生激烈的欲望和行動的心理過程等等的內在體驗①,常常成為作品的核心構成,小說的篇幅或者說體量減小了,但它的容量反而更大,更有了藝術的沖擊力。黑格爾曾經“把悲劇看作一切藝術形式中最適合于表現辯證法規律的藝術”②,稍作變通,可以說作為對生活的一種想象與透視,戲劇或戲劇性的小說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生活與人生領會與剖析的巧妙與犀利。夏商小說的這種戲劇性是他追求小說藝術的整體品質所取得的效果,正像有的評論所指出的,夏商的作品已經剝離了“純粹形式上的游戲與個人的自娛自樂”③。因此,戲劇性也只是我們研究夏商小說整體思想藝術的一個角度。
一? 對生活片段的截取與對人生百態的濃縮
一般來說,沒有事件就構不成情節或者故事,戲劇和一般敘事類作品如小說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對生活片段的截取。戲劇必須在有限的事件和場景場次中展開情節,它可以包容“不在場”的時空,但它所能直接展開的時空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意味著戲劇對于“事件”的講述、描寫是截取的與濃縮的。像戲劇似的裁剪、呈現“事件”可以說是夏商小說“戲劇性”的特點。這是夏商小說的一個普遍的藝術特點,它們散布在夏商的絕大多數作品之中。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作品之一是完成于1999年的《零下2度》。
兩個主人公的遭遇完全是戲劇性的,這種戲劇性是外在的,因為他們完全是互不相識的偶遇,但這個契機卻有力地把兩個人的戲劇性人生濃縮、集中在了一個特殊的、極其有限的時空,兩個家庭原本的戲劇人生已經充滿了內在張力和對人生百態、個體命運的合情與蹊蹺的展示,而兩個家庭戲劇的巧妙結合又形成了新的蘊含了深刻思想的“戲劇鍵”,推演出新的戲劇情節,從而把人生意義、生命情誼、家庭婚姻等盤根錯節的問題,通過新的碰撞和嵌合而起的反應做出了新的衍生:女司機曾經還有心問縣城哪里有打胎的地方,當時,她直覺中想的可能還只是切斷自己與丈夫的紐帶;同樣,馬德方與妻兒散伙后想以手表相抵打車回縣城,原本只是要回到自己的人去室空的家里,并未對人生的未來作出新的考慮。但與女司機的意外相遇,某種意義上使他與她關于人生的、關于婚姻家庭的悲觀的看法和情緒于無意中在這個漆黑寒冷的夜晚里產生了新的“共鳴”,只是兩個本應同病相憐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在積極的意義上獲得情感乃至思想“共鳴”,并使這“共鳴”在兩個生命主體間發揮正面的人生意義,卻相反地使他們無意中領受了“共鳴”的消極后果——連同出租車一同駛入野河赴死。馬德方和女司機的相遇和同行、同歸,其實只發生在短短的兩三個小時間,但卻濃縮了他們各自幾十年的人生。除了馬德方自己人生的戲劇性之外,女司機人生戲劇性的展開或者更準確地說發現,偶然至極。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夏商對人生問題思考的深入和對戲劇性情節構思的精妙。
當然,馬德方和女司機的相遇和共鳴如同他們的人生故事那樣雖然充滿了蹊蹺,卻也具有充分的生活依據或行為邏輯的支撐,但他們的相遇和共鳴也并非沒有走向正面、積極的結局的可能。他們的命運的一致和心思的互相傾吐,本身即已使他們之間具有一定深度的“情意”相投,在各自故事的講述中,也能看出他們原本珍重生活、努力人生的態度,兩個同樣遭到伴侶拋棄的人并不是意味著如馬德方所言是徹底“被生活拋棄的人”。因此,他們完全可以因同病相憐的命運而互相取暖、逐漸建立友誼乃至相濡以沫,走出生活的陰影,共同開啟新的人生乃至有可能成為懂得生活、珍重情感、相親相愛的一家人的。小說雖然不是為了引向這個結局、而完全是為了一種對人性與人生把握的立體與準確,也有意無意書寫了這樣的可能的表現。其實,某種意義上,女司機如果不是剛剛經歷了自己的人生悲摧的戲劇,如果不是因為攬活的習慣(而她此刻當然是沒有心思攬活的),她未必會注意到馬德方一家散伙告別的一幕,她注意到馬德方家的情形,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因為自己的遭遇;而當馬德方沒有打車錢、女司機不接受他的手表而他準備離開時,女司機又主動表示可以用表抵押,這其實也是出于對馬德方的不自覺的同情,這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自己的同情的外溢。于是,馬德方上了她的車,從而這兩個同中有異的“戲劇”就被“鍵合”在了一起。而且,她沒有直接進一步表示不需要手表、免費送他回去,也是出于現實的見識,怕令他覺得莫名其妙而不敢上車,進而失去他、使她自己的同情心理不能得以展開而采取的謹慎、巧妙的措辭和舉措。這里也可以看出夏商對人性體會的深入、細致與準確。因此,讓這兩個偶然相遇的男女最終真正走到一起成為一家人并非是不可能,這只是需要夏商對小說展開更多筆墨的構思、想象與情節的落實。那么,夏商為什么沒有選擇這樣一種可能呢?顯然,這只能說明,在關于人生,關于婚姻愛情、家庭問題,夏商更愿意取一種悲觀性的態度,如同小說的結尾那樣。
當然另一方面,小說畢竟又不是生活本身,對小說家來說,展開關于生活的思考,比給出生活中的問題的答案更重要;關于人生與生活的答案畢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作家不必去窮于應付,而將問題引向深處、引向深刻、啟人深省,這才是最重要的。標題《零下2度》透露的像是客觀的自然信息、無關人生社會,然而既給出了情節發生的一個重要的背景,也強化了作品的悲涼情調。
二? 敘述、戲劇與現場感
小說本是在時間中流淌的講述,但戲劇化的小說卻給人造成強烈的現場感、舞臺感,讀者閱讀故事卻像是在一個劇院現場目睹故事直面展開,給人以強烈的沖擊感,當然這種感受與故事內容的內在戲劇性也密切相關。短篇小說《開場白》(2000)在一個狹小的篇幅里容納了極具戲劇性的多個人生故事。它的講述效果更直逼讀者而來。它的敘述視角就富于戲劇性,讓一個殺人犯在短暫的火車旅途中道白殺人的故事。這個殺人犯果然在為人處世的態度上就異乎尋常、講話口吻驚世駭俗、令人生寒。作品以快刀斬亂麻、手起刀落的“生鐵”作風所講述的幾個故事,凝聚著強烈的內在戲劇性。
小說中,李偉曾是一名技校生,為了一個女生令情敵致殘,刑滿釋放后,在小區搭了一間屋子出租,居委會制止,他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剁掉了一截,用它換了那塊地皮。新的情況下,他的小屋又有了危機,妻子引誘了負責拆房的警察,又告倒了警察。這個警察出獄后殺死了李偉的妻子。李偉對面臨槍斃的警察說這正好摘了自己頭上的綠帽子……在李偉身上有著深層悖論:如果說致殘情敵是違背倫理的極端的“青春莽撞”行為的話,他為了生存,為了得到自己的生財之路、生存之路而把自己的手指剁掉,雖然可以說是一種“丟卒保車”的選擇,但畢竟自殘的是自己的身體和重要的器官,那么也可謂是以自殘而成全自己的“自養”之舉,其悖謬性在語言中即可見到:一旦自殘即意味著“不全”,但這卻是為了“成全”,這是多么的悖謬?我們暫且撇開社會道德的倫理評判,李偉的舉動里蘊含著多么深刻的悲劇性疼痛?李偉的妻子也是以女人的特殊方式踐行了一種“舍我救我”的悖論性存在還送掉了性命。
另外幾則殺人者故事也無不透露出人的動物性訴求與人的道德倫理等超越性訴求在個人身上的邏輯性沖突表現出的強大的毀滅性力量。作品最后,殺人者說:現在,“我”已經下了火車,來到了人群的中間。這個游戲殺人者不是像惡魔那樣被收進了寶瓶,相反,他此刻來到了人群中,這里正好呼應了小說的標題“開場白”,言外之意“故事”還在后面。讀到這里,似乎殺人者正朝著讀者撲面而來,這完全是一個戲劇性的時刻、令人膽戰心驚的戲劇性時刻。
與《開場白》近似,極具舞臺感的同類問題劇小說是《貓煙灰缸》(2017)。炒股發了財的老靳迷上了酒吧小姐米蘭朵,在他許諾的婚姻應該成為現實的前夜他玩了失蹤。半路上羊水破了、胎兒沒有保住,米蘭朵被醫院救下但瘋了。她的電話通訊錄里只有一個老公。醫生打通了老靳的電話,他承擔了一切費用,并在精神病院旁租下房子開了這家阿朵酒吧。現在實習醫生第五永剛在阿朵酒吧里聽了這個故事。他第一次單獨走進了酒吧,被這里的瑟琳娜迷住了,她靈機一動,對他提出挑戰,只要他把茶幾上的貓煙灰缸偷出去,她就跟他走。他是聰明的,成功把煙灰缸帶出了酒吧。這個城鄉接合部的酒吧和精神病院本身構成了一個奇特的戲劇場面,背后的故事也更有悲劇性。現在,實習醫生在這個舞臺上重新上演那個悲劇性的故事。當然也可能上演成喜劇或正劇,但作者的迷思在于人性與人生的戲劇性本身。
《正午》的標題給出了戲劇發生的時間,而地點就是正在舉辦的一年一度展銷會會場。舞臺上演了三幕,陳明和她的男朋友嚴小晚,酈東寶、他的女兒嘟嘟和前妻任嫣,瞎子阿財、搶劫的歹人等,三組人物,交叉出三組戲劇。關鍵在酈東寶這里,他曾出于某種自私——盡管受到傷害的人也承認了他的這點自私“并不過分”——而離棄了任嫣,但現在因為一點無私的仗義卻丟失了女兒。這無疑是一個雙重的婚姻家庭悲劇。而陳明和嚴小晚的未婚而“性”的不一樣的煩惱,也折射出情愛婚姻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另一種價值沖突。至于瞎子的被搶,主要是用來為這個戲劇的上演提供背景和契機的。當然也表現了人性中的自私與仗義的雙重可能性的糾纏。展銷會的會場的確是個人生大舞臺,正午的陽光下正好展示人類生活與人性的戲劇的一幕。
三? 尖銳的主體間性沖突或人性分裂
將故事和社會生活內容截取或壓縮在有限的時空場次——這是戲劇性的重要特征,即使我們不必如法國古典主義的 “三一律”戲劇觀那樣苛嚴地看待這一問題。這一時空要求,當然是外在性的,而戲劇的內在性則在于戲劇所展現的主體的人性分裂和主體間性的情感價值與權利沖突以及政治或宗教觀的沖突等等。
《沉默的千言萬語》(2000)里桂小龍和劉永原先都是劉永父親的徒弟,一起學習裁縫。桂小龍看上了胡菊花,他以先強奸后求婚的手段使胡菊花和自己結婚,他們生了個兒子桂崗,小日子過得順順當當。劉永如法炮制卻被韓莉告發而坐牢。現在他被釋放了,但生活已經破落。他去找了韓莉,原想再強奸她一次,但離婚后獨自蝸居的韓莉現在又瘦又黑又丑,他很容易地脫光了她的衣服但自己的身體卻毫無興致,而那個女人并沒有反抗。他問那個女人,假如當初自己耐心地追她,她會嫁給他嗎?那個女人只是搖著頭、淚流滿面。劉永對桂小龍說其實自己原來喜歡的是胡菊花,但是卻被桂小龍搶先了。桂小龍告訴劉永自己倒并不知道劉永也喜歡胡菊花。劉永終于咆哮了:你不過是碰到了一個不愿意告發你的女人!至此,劉永一直沉默著的千言萬語終于還是脫口而出。從社會意義上說,愛情婚姻的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同一與背離問題在這個多角關系中得到了一次形象的展示,而桂小龍夫婦與劉永之間的糾結也展示著主體與主體之間利益的沖突與人生處境對比而生的甘苦差異,顯示了人性與現實的復雜的戲劇性的一面。另一個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當初桂小龍和劉永都想借助人們的道德心理而劫持女性、成就自己的婚姻,當然結局是一成一敗;而現在,劉永又在以另一種道德心理敲桂小龍夫婦的竹杠,至于他對韓莉再次施暴,更是一種粗野無知的報復行為和心理發泄。
《集體婚禮》(1998)寫季有城和蔣怡琴參加一場百對新人的集體婚禮。季有城發現一個新娘正是自己大學同學荊一丁曾經好過的飯館女員工。荊一丁得手后不要人家了。但不久荊一丁就被一輛飯盒車撞死了。從眼睛中看得出對方也認出了季有城,在跳舞環節他邀請她跳了一支,然后就像誰也沒見過誰地禮貌而別。“對這兩個原本就是陌生的人來說,永遠別見面是避免難堪的最好方式。”但他們卻在這個集體婚禮上再次邂逅。這就構成了一種跨時空的戲劇情境:對于愛恨的對立與轉化給出了尖銳的對比呈現。對人生及兩性關系的復雜和愛恨的相依與轉化的人生境況發出深長的感慨喟嘆,生命的恍惚與無常、相互的尊重與輕慢都值得思索。原本喜慶盛大的集體婚禮在兩位參與人的心中投下了血腥凄慘的暗影。令人進一步深思的是,婚禮上的自由邀舞雖然是一個既定的節目環節,但季有誠并非必須要去邀請堡式發髻的新娘去跳這尷尬的一曲,他去跳這一曲是要給她過去的過分殘忍一個提示與譴責,還是通過這一舉動表達一種“坦然”和“豁達”:不回避這次尷尬的邂逅,但是彼此忘掉這次的難堪的邂逅可能引起的聯想與猜疑!?也許作者更傾向于前者,因為季有誠在洗手間的淚流滿面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更合情合理。不管荊一丁和堡式發髻的新娘各自的錯誤或惡德有多么嚴重,但欲望與愛情、權利與尊嚴、道德與生命之間的同一與錯位以及主體間性的沖突與一致,更是一個永恒、難解的問題。
四? 一種人類生活無法逃避的悲劇性基因——偶然與無常
如果說主體間性的沖突和人性問題,更多牽涉到個體的道德把握的話,有些人生或社會的“戲劇”特別是悲劇的發生,卻也是導源于偶然性,常給人以人生無常的感嘆,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希臘戲劇中的命運悲劇的類型。
《今晚》(1999)也是一篇短小精悍,甚至可以說空靈迷離的戲劇性小說。企偉的妻子沒有從抽屜里摸到要用的膠皮套,于是企偉在午夜時分第一次猶猶豫豫走進了對面街邊的這家門口有個大大的霓虹“愛”字的商店,也許由于羞怯他抓起自己所買的東西轉身出門的瞬間慌張地踩到了一個年輕女人的腳,交涉的結果是他拿出兩張十元的紙幣了結。企偉原準備趕緊回去,但身后傳來了高跟鞋的聲音,他轉頭看到就是剛才那個女人,他放慢了一點腳步,那女人超過了他走到了前面的橋頭,她抽著一根煙,顯然在等他,最后女人把他帶入了無邊的暮色中,而企偉就此卻永遠消失了。小說的結尾透出一種詭秘、腥艷的悲劇性。企偉自己在這個夜晚的意外的小小“偏離正軌”也無疑是這個悲劇發生所不可缺少的元素。
《今晚》的偶然悲劇也源于雞蛋的裂縫給了蒼蠅一叮的機會,但《飛車走壁》(1998)就不一樣了。跟隨美術課老師到植物園寫生的三年級學生石俊輝同學在玩耍時丟了父親的手表。手表被一家正在植物園臨時搭臺演出的外縣馬戲團的表演飛車走壁節目的青年撿到昧了下來。小男孩最后在情急之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塊會飛的石頭撲向了飛車。小說的情節也是戲劇性的,巧合與突然的舉動、變故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力,以悲劇性的形式展示了男孩內心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保護家人財產的強烈責任意識和沖動情感。
《一個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1996)這篇小說里,懷抱皮球的憂傷少年不小心沖進年輕的音樂課女教師的懷里的時候,女老師說:“皮死了,搞得這么臟,看看你,鼻子像一只愛冒汗的小蒜頭。”這句話大大傷害了少年的自尊心,他甚至變得恍惚。女教師其實很喜歡這個學生的,而她也是少年心中朦朧的偶像。一場電影《畫皮》制造的恐怖與燈下女教師鏡前修眉的情景發生了某種心理效應,少年突然一聲慘叫、仰面倒在窗下的水泥地上,放大的瞳孔里充滿了恐懼。小說里的戲劇性中可能包含多種隱蔽的沖突和心理錯位,但少年的死亡彌漫著一種人生的“無常”之感。
《金色鑲邊的大波斯菊》(1999)寫從北京出差到上海的謝文和當地朋友江術臨時隨意到了一家夜總會和招來的兩個姑娘玩樂。謝文看到薇薇背上有個漂亮的貼上去的文身——一朵漂亮的鑲金邊的大波斯菊,他執意撕下來的時候才知道里面隱藏著一個秘密——那里是一個很長的刀疤。然后薇薇就不聲不響起來穿衣服,流淚而別。他們就去找飯館吃飯聊天,這時他們共同的朋友在成都的方小方打過來電話,得到一個壞消息,方小方得了癌。他們安慰一番,方小方希望江術和謝文再去成都相見并與兩個好友電話上一番玩笑。有一家飯館看著不錯,但和他們一起的莉莉希望換一家,因為這家的老板是自己的前男友。這時江術的手機又響了起來,他聽到了方小方女友的哭訴,就在剛剛方小方從十六樓跳下去了。江術和謝文在街頭抱頭哭了起來。在短暫的場景轉化中,表面的“百無禁忌”和“時尚華麗”的“社會布景”背后展開了幾重人物的悲劇性生活經歷。在華美的生活外表之下是人生的歷險與無常。
如果說《金色鑲邊的大波斯菊》透露的主要是社會性的悲劇問題的話,《美麗幼兒園》(2010)的旨趣倒不在社會的批判。無意中聽說了讀書會活動信息的警察敏銳地嗅察到讀書會幕后主持陳小山是一個剛剛釋放出來的問題青年。于是讀書會被取締,而陳小山借機追到幼兒園美麗教師的美夢也宣告破碎。這是一出“黑色幽默”的“灰色喜劇”,折射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管理情況和社會青年們的思想、追求和心理情感問題。
結? 語
盡管我們已經嘗試從多個角度去觀照總結夏商小說的戲劇性,但這種戲劇性的表現也并不限于以上這些,尤其是表現了某種戲劇性藝術特質的夏商小說更不限于以上這些,窮盡性的追索并不討巧也無十分的必要性。而更值得我們考慮的是,夏商小說何以具有如此濃厚的戲劇性,或者說夏商小說的這種戲劇性特質具有怎樣的藝術旨趣或價值?
小說本是故事或以故事為本,然而戲劇也是敘事體,也是以故事為本的,不同的是小說是直接用來閱讀的,或者通過朗讀給他人聽的,這就意味著小說接受并不太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而戲劇因為首先是用來舞臺演出的,這就意味著它的傳播接受受到時空的限制,必須在有限的時空之中完成對故事或社會生活的反映,而且這種有限的時空必須落實在有數的幾個場次的人物言行的表演展開,這就決定了戲劇對人物故事的展開,往往選取故事情節當中的關鍵性環節來實現,這就意味著戲劇對人物故事或社會生活必須截取,所截取的往往是最能表現人物性格或內心深處的部分或展現人物之間及社會生活重要本質的內容的所在,而這樣的內容或部分往往就是所謂內心或人際沖突或社會矛盾最集中尖銳的時刻和場合的情景與過程。因此,如果我們忽略真正的戲劇和小說的故事性展開的區別之處,而觀照它們的“戲劇性”的“異”外之“同”的話,它們都指向一種情節的緊張或激烈、人物內心或人物之間(包括人物與群體或社會之間)沖突的深刻或強烈以及觸及與揭示問題的復雜與尖銳,或者說戲劇性體現著作家所關切和所要表達的問題的肯綮之所在,也是作家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的核心和深度之所在。換句話說,當夏商將小說構筑為富有戲劇性的一種特征的時候,意味著他的小說擁有了小說話語的自由性之外還形成了戲劇般的精煉特征和濃縮效應,因此,夏商小說的戲劇性特征體現了他對生活表現和人物刻畫更為注重思想錘煉和藝術形式刪削改造與重組變形的探索精神和藝術追求,體現著一種感性與思考、詩性與哲性的同一,也即荷爾德林存在論詩學所說的“美與真的統一”④。
20世紀的文學大師弗吉尼亞·伍爾芙在《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里曾對傳統小說不厭其煩地描寫環境以及人物之外的種種事物的細致刻畫給予了徹底的否定,她指出“透辟的一言兩語要勝過所有這些描述”⑤。一句話,現代小說追求著更深刻、精煉的展示與表達形態。盡管追求“戲劇性”不是現代小說達到這一藝術目標的唯一手段,但是“戲劇性”品質正是現代小說的一個重要的藝術追求。而夏商的小說正是鮮明地體現了這一藝術趨向。因此,無論我們在上面針對夏商小說的內容或形式所歸納的諸如尖銳的主體間性沖突或人性分裂、人類無法逃避的悲劇性基因——生命中的偶然與無常的陰影以及敘述姿態或故事形態上的舞臺現場感以及故事情節上對生活片段的截取與對人生百態的濃縮,都表征著夏商小說的突出的戲劇性特征。這也顯示著夏商在小說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兩方面的全方位的一絲不茍的竭力探索的先鋒姿態。
注釋:
①[德]古斯塔夫·弗萊塔克:《論戲劇情節》,張玉書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
②汝信、楊宇:《西方美學史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6頁。
③葛紅兵、王環環:《城市敘事的自覺寫作——夏商短篇小說藝術論》,《南方文壇》2010年第3期。
④田艷:《荷爾德林存在論詩學中的美真統一》,《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⑤[英]弗吉尼亞·伍爾芙:《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見伍蠡甫主編:《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頁。
(作者單位:山東外事職業大學綜合學院、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與法治建構的互動關系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BZW187)
責任編輯:劉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