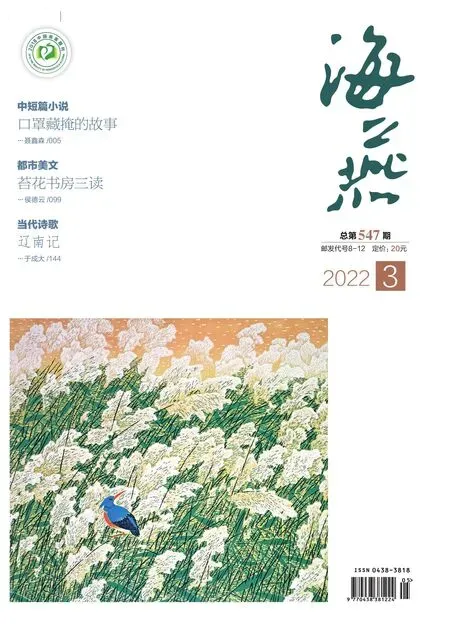老木匠的葬禮
文 尚 元

老木匠死的時候六十三。村里人認為,他陽壽未盡,不該早早下世。但老木匠確實是在這個歲數撒手人寰的,而且最后三年臥床不起,抱憾而終。
老木匠是村里的大輩分,人見了都要喊他一聲爺。叫習慣了,直接叫他木匠爺。老木匠下葬的那天清晨,山地里來了很多人。鄉下極少見這樣大的陣勢,村里留守的人全來了,村外腿腳方便的人也來了。更遠的地方,受他恩惠的人騎著摩托車,或者叫了汽車,頂著一頭寒露早早趕來為老木匠添一锨土。天地的混沌剛剛分明,人們已經站滿地頭,鬼影子一般。男人們嘴咬紙煙,袖著手,胳膊彎里夾著锨把兒,站在送葬隊必經的圪塄上,只要八人抬的棺木經過,他們便跳進人群,送老木匠走完最后一程路。圪塄邊上的紙煙一明一滅,有人蹲下去,黑影便在幽藍的天空下矮成幾個豁口,像老木匠笑時露出的下牙槽。
村子遠離墳地,出門沿著往日割麥的機耕小路,轉幾道彎就上山了。路比以前窄了,真難以想象,這樣的路多年前能跑拖拉機。現在老木匠的棺材還能不能過得去?半小時前,成殮儀式剛剛結束,是在老木匠生前挖的三孔窯洞的東窯舉行的。院門口除了掛著招魂幡,還綴著一盞二百瓦的大燈泡,孤光亮影里孝子賢孫們紛亂的身影仿佛一團投火的飛蛾。三孔窯洞的莊院早些年很流行。蓋房子需要攢錢攢糧食,還要請匠人和幫工,打土坯、備木料、燒陶瓦,選動土的吉日良時,門道多著呢。而且,屋里得有個能干的女人,里里外外照應。挖窯就沒有這么多講究了,憑一點經驗和一身子力氣,還有就是,要有一股子死磕到底的心勁兒。老木匠挖了窯洞,住進去,整整四十年,從沒有挪過窩兒。今天他就要被人裝進棺材抬出去了。
老木匠出殯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小意外。一部分莊客站在地頭等得不耐煩了,想看老木匠最后一眼,便偷偷下山去。他們是一群指手畫腳的家伙,埋怨從集鎮上買來的松木棺材質量太差,薄得像牛皮紙盒子,榫頭松動,棺板縫里能插進去兩根手指頭。還有,他們說這棺材太小,不一定能把大個子的木匠爺裝進去,老人家活著時給人做棺木,從不偷工減料。執事的總管名叫新民,按輩分管老木匠叫大伯,他罵那些說風涼話的人,都這個時候了,要操心老早干啥去了。大家立刻住口,看著被糖紙一樣好看的彩旌簇擁著躺在舊門板上的老木匠。
老木匠穿著綢布老衣,嘴巴被面團堵著,一張草紙蓋在臉上。要上路了,新民命令在場的人搭手,結果只上來三個人,都是些年輕的后輩,沒見過挺尸的場面,舉著兩只手不敢靠近。新民怕這肅穆而又神圣的時刻出現意外,急得喊門外的閑人。往日,這事都是老木匠干的,新民打下手。現在老木匠死了,由他代理總管事宜,竟有點不知所措。
新民喊來幾個與他年齡相仿的人,抬頭的抬頭,抱腰的抱腰,搬腳的搬腳,才把僵硬得像一根椽條的老木匠裝進棺材。棺材匣子看起來小,但老木匠躺在里面剛剛好,頭頂著天,腳蹬著地,像為他量身定做的一樣合體。一個像竹竿兒一樣瘦的孝子跪在大門口,扯開嗓子哭了一腔:“大啊……”新民總管上前戳他的后腰。瘦竹竿兒似乎明白這時候還不能放開聲哭,便回頭看新民有何指示。新民遞給他一個祭奠老木匠用過的瓦罐,里面裝滿這樣那樣的飯食。瘦竹竿兒站起來,將瓦罐摔爛,一顆豬肉丸子滾進鼓樂班簡易的棚子,停在長條板凳的凳腿下。
哀樂響起。鼓樂班子三男一女,女的能唱秦腔《三娘教子》,幾個男的其貌不揚,高個的那位戴著火車頭帽子,兩只耳沿伸在半空忽閃忽閃。他的腮幫子鼓鼓的,好像昨天酒席上吞進嘴里的半個饃還沒咽下去。高個的嗩吶領銜,其他人的二胡、板胡一起開奏,人們便知起喪了。女人胸前掛著一面紅色的西洋大鼓,邊走邊敲,送葬隊的人便踏著鼓點兒上路,步伐竟出奇得整齊。
八人抬的棺材,前面四人,后面四人。前后都綰著麻繩,繩扣里穿過橫木,兩邊吊著豎杠,這樣走起來自由靈活,轉彎也方便。大伙兒一窩蜂往山上走,到了上坡轉彎處,抬棺的人小跑起來。后面人“哎吆哎吆”喊,“木匠爺想走快一點呢。”前面人回轉不過,急忙叫道,“木匠爺太重了,恐怕是不想走,慢一點呀。”隊伍里的人一起上來搭手,外側的路好走,人也多,差點把老木匠的棺材掀翻。這時候人們聽見咯吱咯吱的聲音,那是繩子與木頭的摩擦。新民喊道:“都抬好了,一個木匠爺你們送不上山嗎?”
送葬的速度慢下來,人們的步子又踏到了鼓點上。鼓樂隊和瘦竹竿兒走在最前面,抬棺的人跑得再快,也不能超越引魂舉喪的人。等候在路邊的鄉下人漸漸多起來,一個個跳進送葬的隊伍。這時候,天幕變白,光線發亮,能看清人的面目了。一伙人,四五十個,中間的披白戴孝,外圈的黑衣老襖,像一團螞蟻舉著個蟲子殼,一齊往山上蠕動。到了山咀的堡子旁,人群驚動了藏在草叢里的幾只長尾雉雞,聒叫著,沒命似的飛下山去。棺材發出一陣嘶啞的呻吟,大伙兒嚷嚷著。新民喊:“都抬好了,抬不住換肩。”不知誰眼尖,突然說,“哎呀,木匠爺不肯走,腳都掉出來了!”
新民罵:“胡說啥話哩!”他還是低頭去看,結果就看見棺材的底板真的張開一條縫,老木匠被綁著的雙腳戳在外面。白棉襪子,尖尖的方口老鞋,很像老木匠活著時用過的大墨斗。恐怖的氣氛瞬時襲擊了送葬隊,人們的頭皮麻麻的,難道真是老木匠不想走?新民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曾經跟著老木匠把村里的老人一個個送上山,人前人后指指戳戳,從沒見過這等怪事啊。如果老木匠活著就好了,還可以問問他的意見,讓他來定奪這事怎么辦。新民的鼻腔一陣酸楚,差點落下淚來。于是喊:“上繩,快上繩!綁也要綁到山上。”繩子是提前備好的,下葬時用。幾個后生們尚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沖上來,就看見新民的眼睛里盈滿清亮的天光。還是那幾個老家伙能指派上用場,事關重大,他們撲過來,身手麻利地將繩頭甩過棺蓋,有人自告奮勇,撥開密密麻麻的人腿爬進去,抓住繩子,兩頭一用力就把棺材底兜住了。
新民心里裝著話:“伯啊,您就將就著吧,別怪我們心狠,今兒個把您送上山,后頭還不知誰送我們呀。”他的心涼涼的,泛起一陣難以言說的悲哀。山旮旯里被白霧浸透的小路上,荒草嗚嗚哀鳴,幾顆酸棗在冷風中掙扎。新民見過很多死去的人,都走這條路,順順當當的,唯獨一生馴良的木匠爺要摔在路上了。
幾天前,老木匠還有一口氣。“伯啊,你今天狀態好,別動,就這樣躺著,金平賢弟把你照顧得多好,屎尿都給你擦。金平的媳婦懷了孩,肚子大得像頂著一只碌碡,等他的日子好起來,就接你下山。”老木匠的臉上顯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譏笑。“這窯是你一?頭一?頭挖出來的,住在里面,比住洋房心情舒坦。一個人從生到死,都鉆在黃土里,黃土能把一個人洗滌得干干凈凈。”老木匠的眼睛像兩顆野毛桃,喉嚨嘶嘶作響,艱難地說道:“多活了歲數,受罪。刑期滿了,我就該走了。”新民聽見老木匠說話,深感意外。自從他臥床之后,就如同風中燭火。人活著不過就是一口氣,有的人走得干凈利落,一夜之間就沒了。那樣短暫得用不了一鍋煙的工夫,來不及生離死別,來不及托付后事。只知第二天,陽光照常穿過高窗,在深邃的窯洞里斜刺進一道金色的光柱,那個人的生命已然塵埃落定,世上的冷暖再也與他無關。但是,老木匠沒有這樣幸運,三年前他患上突發性腦溢血,后來,命算是保住了,人卻躺進了自己親手挖的窯洞。有時候他聽見窯外落了一院麻雀,那些小東西是來搶金平曬在場院里的谷米。老木匠不能動,只聽得它們吃飽喝足后,嘩啦一聲跳上南墻頭,再嘩啦一聲飛到旁邊的老山楂樹上。墻外有一叢矢竹,墻內是一大片芍藥,花開之后滿園清香。可人到末路,連一個麥草樁子都不如,即使老木匠站在那里,麻雀也不再害怕他。有時候,他聽得大孫子回來了,踢一只皮球膽子,砰砰砰,撞壞了嵌在墻穴里的蜂箱,擊落了經年陳舊的爛酒瓶子,一陣哐當破碎的聲音。雞呀貓呀狗呀的小畜生都不見了,有時候院子安靜得如同一座寺廟。后輩們都搬到山下去住了,在大馬路邊蓋了房子,經常是金平,要不就是金平的媳婦來送飯。金平起了五間大磚房,累得腰都彎了,人本來就瘦,成了一尾蝦。娃娃們年輕,盡守著山下過日子,他就待在親手挖的土窯洞里,哪兒也不去。住在這兒好,就像新民說的,一個人在這黃土里,會被洗得干干凈凈。等走完上山的那條路,就再也不給娃娃們添麻煩了。他們的日子,麻煩已經夠多了。

插圖:王譯霆
老木匠有時候覺得他已經死了。人死之后不也是躺在那個漆黑的墓穴里嗎?一孔小小的窯洞而已。這種悲觀的想法產生之后,他覺得生命的盡頭遙遙無期,仿佛生和死連在一起,成了一個相通的概念。除夕之夜,金平和幾個堂姊妹哭哭啼啼的,在老木匠的窯洞里生起了爐火,把炕燒得滾燙。老木匠想,他死了也不一定有這樣的待遇,大伙兒上墳燒紙,帶來寒衣和酒肴。孩子們走后,他便陷入一個人長久的安閑之中。這時候,老木匠是活著的,他轉動眼珠觀察院里的任何一絲動靜,有時候他甚至能翻動身體,盡管他的身體已經像一艘傾覆在大海里的小船。有一次,窯面上掉下來一條紅頭綠身的菜花蛇,從門縫里游進來,吐著黑黃的信子,兩只眼睛死死盯著他,充滿了對人間的好奇。老木匠平生最怕蛇,那東西帶著一股妖風,令人心驚膽戰。菜花蛇爬到炕腳下,豎起小腦袋,老木匠想喊,聲音卻從喉嚨鉆進肚子,他自己都糊涂了,一個等死的人怎么會怕一條蛇呢?
他聽見窯外呼呼的風吼,一只黑貓躥進來,弓著腰,脖頸上鋼毛豎立,像一把拉滿弦的弓。黑貓隨即發動進攻,一爪子拍在蛇的腦袋上。此時他看到了奇幻的一幕,老貓發起威風,警告這條蛇不可輕舉妄動。小畜生被趕出窯洞,便在地上撒潑似的打起了滾,噼噼啪啪在地上摔打身體。另一個生靈救了他,老木匠明白,大限未到,自己所受的痛苦不足以抵消這一生犯下的罪孽,還沒有資格走上山的那條道。
老木匠躺在病榻上,眼淚滾滾。他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過往的歲月,像拉開一個多年棄用的老抽屜那樣,把違心的往事一件件拿出來懺悔。他明明是個善人,鋪路修橋,念佛吃齋,一生沒干過什么缺德的事啊。村里老人們的棺材都是他做的,除此,他還操持鄉民的喪葬禮儀。年輕時力氣盛,幫別人打墓,只要東家沏一壺老茶就行。那不算個啥活兒。后來他還給人做壽木,有口好棺材就好比在這世上住過一座好宅院一樣風光體面。老匠爺不圖什么,人嘛,他常說,都是上世來贖罪的,說不定哪天就沒了。但是,他為什么要受這個罪呢?他是慚愧,也許是那件事吧。除此之外他實在想不起來自己的一生還犯過什么過錯。
他動過廟里的募捐。想到這一點,老木匠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真是一生難以洗刷的恥辱。他主持修建的那座廟院就在堡子上,他把布施得來的七百塊香火錢挪用給了金平蓋房子。金平這小子是當年一個逃荒逃到村里的瘋女人生養的,小得如同一只鞋底。女人生完孩沒出月子就跑了,留下一個無辜的、嗷嗷待哺的生命給他。也不是瘋女人向他托孤,而是他最先在飼養站的爛窯里撞見這個粉紅色的嬰兒。那時候的老木匠還是個大小伙兒,真不敢想象,他就這樣稀里糊涂給一個身世不明的孩子當了爹。為此,老木匠一生未娶,四十年來,眼瞅著一棵稚嫩的苗子長成了樹,而他也被缺衣少穿的日月熬白了頭。他分明記得自己還是個大小伙兒呀,力氣旺盛,有一身結實的腱子肉。金平長大,娶妻生子,如果當年沒有這檔子事,他也會像現在的金平一樣過著平凡的生活。這小子被一只奶羊哺育長大,身子骨單薄,眼下又被一座莊院壓垮了,欠了一屁股賬。討債人的手指都快戳到他的鼻尖了,總不能每次都叫人家兩手空空回去吧。于是,老木匠挪用了廟里的香火錢,但很快又還了回去。金平喬遷之喜,請客吃飯。鄉人慫恿,說大平房子蓋好了,把老木匠從半山腰接下來,趁著房空屋大,該比劃比劃身后事了。老木匠一輩子給人做棺材,這下該給自己割一口好壽木。老木匠牙齒掉成了豁,走氣漏風,笑聲跑了調兒。他很少這樣開懷大笑,仿佛在苦難的童年別人塞給他一把甜糖,笑得涎水都流了出來。人的一生兩頭短中間難,娃娃們掉牙,老漢也掉牙,真是奇妙。他不會下山,老木匠惦記半山上的雞呀狗呀豬呀牛呀的命命。老木匠對給自己打制一口好棺材的提議動了心,是啊,他也想要一口好棺材。
那天多喝了兩盅酒,也許不止兩盅,他記得自己沒喝多少,站起來去小解,在貼著洋瓷的沖水茅廁里,他感到罪孽又加深了一重。現在的人啊,這樣光光堂堂的屋子,竟然用來屙屎!老木匠想到院外去,一出門,便感到天地反轉了。他聽見往日熟悉的聲音,金平的大腦袋遮住日頭,大家又喊又叫,好像他死了一樣。事實上,那會兒他在穿透黑暗的光影里看到了許許多多曾被他親手送上山的老人們,牛娃他爹、黑子他大、貴財叔、滿堂爺,吳家灣里的寡婦奶奶說著一口四川話,他們背靠黃土圪塄,在日頭底下悠閑地歇著,向他微笑,揮手致意。土地和陽光都是同一種和煦的金黃,除此之外,他看到的世界黑白兩色,雜亂無章。
老木匠把這話告訴新民。他口齒不清,但精氣兒回來了,像少年時割完了一場麥子。渴啊,餓啊,困啊,他想抱住瓦罐喝一肚子水,四五個軟軟的白面蒸饃,然后再昏天暗日地睡上一宿。新民說:“伯啊,你好好養著,祖宗保佑,要不然,三年前早就沒有你了,能叫你現在躺著和我說話?”老木匠的眼睛亮了一下,像天上的月亮掉進了澇池。老木匠說:“刑期滿了,這三年的牢,贖了我一生的罪。”他又說:“我給人做了一輩子棺材,誰給我做呀?那年你還是個娃娃,喚作給我當徒弟,終是沒如我的愿。”新民很愕然地望著老木匠,看他如炬的眼眸漸漸暗下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以為木匠爺早忘了。
現在,一群人抬著老木匠上山。棺材被五花大綁,發出一陣悲壯的沉吟。繩子纏在木頭上,也就把老木匠對人世間的留戀和不舍捆死了。不知誰在堡子的岔道口放了一堆火,麥草受了潮,冒著乳白的濃煙。送葬隊的人行色匆匆,老木匠想走還是不想走,他們已經沒有心思去考慮,只想趕緊把他送進墓穴埋掉。終于到了地頭上,新翻的黃土冒著冷氣兒。腋下夾锨的人有些急不可耐,在他們看來,埋葬老木匠就像種一窩子土豆一樣簡單。金平率領的孝子賢孫撲倒在墳地前,哭聲像雨點兒落下,到了痛哭流涕的時候,他們自然鉚足了勁兒。這時候不哭,恐怕往后就再也流不出動情的淚水。新民的心隱隱痛著。好吧,就這樣吧,上路吧,去另一個世界瀟灑快活,你斷你的塵世苦,我念我的度人經。其實,他很想為木匠爺最后整理遺容,但棺蓋被釘上,就不能再打開。那時候,他已經掉不出一滴眼淚,只好強忍住悲傷,一心想著把死去的人埋掉,入土為安。新民站在新鮮的黃土上指揮大家,看到老木匠即將躺下去的墳坑,他突然發起了火。圪塄下墓穴洞開,仿佛鑿穿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隧道,他和送葬隊的人都站在門口。他發火的理由是墓坑挖得太淺,不盈六尺,如果瘦竹竿兒一樣的金平站在里面,也許還能露出半個腦袋。人總會走到這一步,也許過不了多久就該輪到他們當中的哪一個了。可是,真想不到會這樣慢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和生,都是不應該潦草的。死人無法挑剔自己的墓地,這個時候了,還能說些什么呢!新民黑著臉,跳下土堆,按照鄉下的禮儀,做了簡易的法事。但是,老木匠的兩只腳還露在外面呢。新民走到棺材前,有人抱怨,快抬不住了。很多人都過來幫忙,他們就一直把木杠扛在肩上。新民內心慚愧,對棺材里的老木匠默默說道:“伯啊,你就將就一點吧,也許我們以后都住不上你這般像樣的宅子。娃娃們會把我們燒成灰,裝進石頭匣子,也不知擱到哪個地方。你老有福氣,還被我們抬上山了!”然后,新民彎下腰,像關心襁褓里一個嬰兒的冷暖,把老木匠伸出來的腳使勁兒往里面掖了掖,大聲喊道:“下喪!”
漆黃的棺材落進墓坑,大小也剛合適。鼓樂隊開始發揮作用,嗩吶適合演奏大喜大悲的調子,在老木匠的棺材吊下墓坑的那會兒,高個兒的嗩吶手把悲傷的送葬曲吹得歡快而又奔放。
抬棺人扭動肩膀,深深松了一口氣,他們終于解放了。一位瘦小精悍的莊客跳下去,前前后后檢查一番。這時候,鼓點兒響了起來,和著嗩吶的曲子,中西合璧,分明是一首進行曲的節奏。該哭的人放聲慟哭,金平哭了一會兒,首先從地里站起來給大伙兒發煙。天色已亮,地面上刮來一股黃色的風,人們像深秋里掉光葉子的樹,禿禿地站在山地里,也像睡了一宿的雞,木然地抖了抖羽毛,迎接新的黎明。新民掏出手機看時間,然后微微點頭,連他都沒意識到這樣的動作暗示了什么意義。于是,腋下夾锨的人們在他的授意下,飛撲上來,搶著往墓坑里填土。有了音樂和哭聲,他們的動作分外帶勁兒。松軟的泥土落在金黃的棺蓋上,變成黑色,猶如潑了墨。很快,老木匠的棺材就被沉重的黑色掩蓋上了,像一只小船沉沒在浩瀚的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