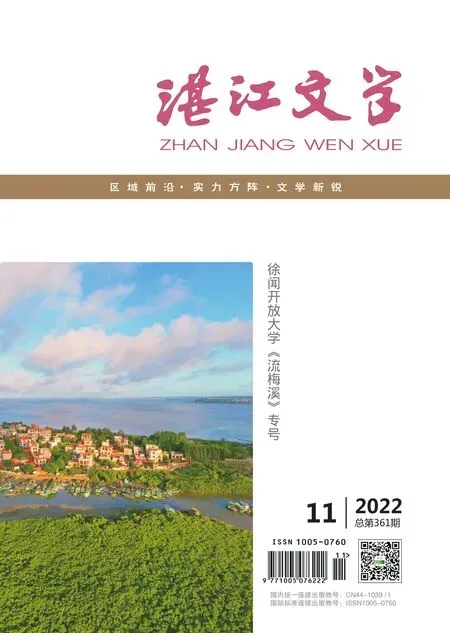蔣浩詩選(六首)
◎ 蔣 浩
藍色自行車(給馬雁)
你把自行車放在廚房里,
自行去了上海,
自行走了。
你蹭飯,
還老說我做的不好吃,
特地把辣椒從成都帶到沙峪口。
什么東西里總要有點辣才對頭。
四川人喜歡在雅正的細節中添加
一些邪乎的刺激。
比如對花椒的鐘愛,
那種癱瘓全身的麻卻被他們用來疏通全身,
還大喊不夠痛快。
當然,你固執地往鍋里碗里添辣加麻,
你還不是辣妹,
永遠也不像是。
但精神上似乎遇到了大麻煩。
如果那就是精神,
我寧愿說那是過于認真的任性。
瞧,魯迅蓋起了藥堂。
好在好的烹飪絕不是捧人棒人,
你不挑剔食物,
只糾偏味道。
顯然你也很喜歡這周邊果園里各種水果
中
簡單樸素的天賦:
不是酸,就是甜。
絕對不麻不辣。
你介意的只是一日三餐
我們自己能創造和創造出的滋味。
有時,是味道引起了反胃,
進一步提煉了反思。
記得我們在小南莊認識不久,
你就說你一直困惑一個問題:
“我為什么是一個回族?”
我當時笑笑,說:
“你姓馬呀!”
至少馬和自行車都是交通工具。
而且,馬還很有可能是自行車的前身。
你為了糾正我,
從成都買了本《古文字詁林》。
寄到海南時,
我卻自行去了新疆。
那時我已換了好幾輛自行車,
每一輛最后都被偷了。
只有回到沙峪口,
我從不敢在城里騎車的妻子
還會和我在鄉村公路上騎著她
到八公里外的上苑看我們的朋友。
有一次秋夜回來,
在引水渠邊掉了鏈子。
我們推著癟胎的車頂著腫脹的星光,
走了兩小時回到藝術館。
第二天,我妻子說她有夢中得句:
“數完天上的歸鴉,
都是些瑣碎的話。”
2016年9月23日,海口
注:馬雁(1979-2010),四川成都人。遺作有《馬雁詩集》(冷霜編)和《馬雁散文集》(秦曉宇編)。
六月十六日,登五指山(給梅國云)
泠泉如蛇,在山腳
疊出一個個腳趾蓋似的鏡潭。
上山如登堂,先照照衣冠,
往壺里多灌些水,
給鞋帶上的結加一個結。
山路要比這崎嶇漣漪陡峭得多。
一段山林后,是片竹坡。
竹間路稍緩于林間路,
竹間風也涼于林間風。
而半山腰的熱帶風更是涼如甜釉。
走完木棧道,開始手腳并用,
抓鐵索,踩鐵梯,
在山壁上垂直爬。
累了,杜英樹的屏風大板根
為我扇動我的肺腑氣,
坐在橫道的木蓮上嚼饅頭,
看蝴蝶停上野生蘭花,
似懂非懂地出神。是的,
我把鳥巢蕨下的靈芝
誤作了石階縫里的蘑菇的
扁平老年的影子。
雖然風格如此提煉了風骨,
總有那么一點點不得已的釋然。
我為我的力不從心找到了發力處——
用手機拍攝有趣的樹名:
烏墨,坡壘,鴨腳木,母生,
子京,中平樹,筆管榕,黧蒴,
鵝耳櫪,水翁,水同木,異形木,
粗榧,山荔枝,蝴蝶樹,三叉苦,
苦梓,油楠,重陽樹,陸均松……
記住名字就像認識了本尊。
認識了本尊就像有一部分出于自尊,
有一部分屬于我。
比如,母生就是母親生的樹,
黧蒴是山下膚黑的黎族,
粗榧就是粗暴的樹中土匪,
異形木來自塞杜斯星,
陸均松像是我的水滸兄弟呀,
也合這里的氣氛;
而水同木可以是火同土、金同銀,
有點三同契之玄學了。
我想著這些混亂的組合和歧義,
樹上的銘牌就像一塊塊碑,
立在周圍干凈的負氧中,
等待辨認和不朽。
在當地流行的傳說中,
五指山原名五子山,
是熊豹蟻蜂鳥們搬來泥土和石頭,
為五個被海盜殺死的孩子們
壘起的美麗的墳。
……爬山像是憑吊。
山鷓鴣怎么悅耳也變不了傳說。
我比別人用心深、用力勤。
山頂始終在頭上,
像頭和心保持著始終的距離。
顯然,今天的爬山不是為了看山。
我看到山頂上很多的云,
風又把他們搬運到遠處別的山腳了。
歷史和傳說稍有不同,
我爬上去,
這山巔也不同于樹巔。
2016年6月30日,海口
茶源夜談(給高春林)
詩心不古。意料中的
意外:
才離開武夷山卻喝到大紅袍,
才看了林語堂就來拜蘇東坡。
汝水煎茶,比這冬夜濃釅些,
消化著牛肉之紅和面道河洛,
真的很難說,
是好興致正好趕上了壞年頭,
還是新社會遇到了老相識?
2007年,車過平頂山,
我和森子、永偉、簡單被你
拉去三蘇園,半道上,
卻糾結于廣慶寺沒大沒小的細雨
是否要輪回到他年今夜。
后來去葉縣看山谷道人,
那里的葉公好我光頭灼灼,
在縣衙里審判詞語時,
奪胎換骨,
堅持要把詩關進學院派的大牢里。
咔嚓聲卻把我們關進了相機。
那囚在舊照上的眼神,
看你像看紅石山腰
那片象征主義的高春林。
得之失之?我現在還迷糊呢。
再后來,和老多多爬到了山頂,
四望蕭然,城市森林公園的計劃,
正在伐林修路、毀樹造房,
說是要把新詩移植到后現代消費景觀
中。
這點上,信仰不如友誼
神奇,你看神農山輕輕一躍,
把銅鼓嶺從南海中擰出來,
放在這茶海上的茶寵中,
被澆灌得濕漉漉的。
詩顯然被她的溺愛者世俗化地繼續嬌慣
著。
剛才在好吃的吊三鍋,
你的女兒和我玩游戲:
找出三枚硬幣的藏身處。
她是你的詩,
不是你的詩之光。
不如這夜半中原,街道含輝,
月亮多余得像此刻你我之間的法鐳,
正在給兩個暗黑的影子
加了一把鎖。
清冷之快,鈍于耳語。
2018年11月19日,海口
注:茶源,河南郟縣龍山大道茶葉店。2018年11月17日,與高春林、楊小濱夜飲。
北運河東(給阿西)
水不錯。從中南海出來,
稍作澄清,向東,再拐彎,向南,
在燃燈塔尖稍作徘徊,
流進這云南銅鍋里。
羊來自千里外的內蒙大草原,
羊肉來自身邊的數控切片機。
自然卷的邊緣,
護佑著肉體中心冰冷的空寂,
在盤里壘起金字塔。
逝者如斯夫,
羊我所欲也。
落日的舌尖舔向長堤,
在唾沫中分泌金融和資本,
把對岸長鱗的樓盤壓在了自否的
舌根。喲,快看,快看,
亮起來了,
壁燈在壁燈之光中坐禪,
炭活在一種復燃的死灰里。
湯呢?加了蔥段和姜片,沸騰的,
是綏芬河,是涪江啊。
來,干一杯!酒水相逢,
給這欸乃夜色哐當一擊,
給這此岸彼岸浮白一揮。
酒在水中蹀躞,見到河灣
都要作揖點贊。說,“吃啊,吃啊。
好味道!”味之,道之?但味,
味在哪里調情呢?
韭菜花敷衍著芝麻醬的犟。
甜蒜填起了腐乳之乳。
香油在生抽和酸醋中平衡清濁之辯。
蔥花和香菜各擅手段。
書房里的克隆人會愛上廚房里的仿生羊
嗎?
河面飄過的畫舫
和臨窗扔下的酒瓶,
終點不再是阿里巴巴的杭州,
是海南。嗯,海不錯。
2019年9月14日,海口灣
外 灘(給古岡)
外灘以外無世界。
你的發型熟悉你。
你是會計,
為了算出每撇波浪的斤兩,
借口去公司找算盤,
卻在圖書館數臺階。
一級一行,
詩并不一定
總那樣遷就你。她說,
阿個暈,阿個暈。
隔江伸過手來。
你的替身迎上去。
晚餐像灘涂,
未必好看,
英國人卻從未來著眼,
在和平飯店,
用叉子替下筷子,
插進這微溫的,舔水的
舌頭。
2020年8月15日,海口灣
注:阿個暈,上海話“押個韻”的意
思。
為西渡作
早晨在萬綠園散步,突然想起二○○六年我們在喀納斯湖度過的夏日
1
似乎該做點什么?
比如,把喝光了橙汁的紙杯
扔進那堆泡沫般
突然膨脹的灌木叢。
風一再地擰緊
掛在斜坡的樹冠。
斜肩的毛巾,
像薄霧圍住早醒的松林。
針葉漏下的光,
沿著虬根往上爬:
看似那么輕的
領悟,
有意要迷失在本性中。
而光之一端攥在你手里。
2
現在,腦子里欠缺的山巒,
靠盤子里凸起的面包
來補形。
雪峰和冰川,
繼續給周圍的咸濕空氣
樹立榜樣。
湖水因低溫而清澈,
鏡頭濾過的青春
在水底燃起灰色的
淤泥:
你相似于你的出神,
不如你相反于你的甜。
指尖在水面挖出一個洞,
邊愈合邊分解。
但漣漪接續山之脈,
又隔開跳動在手心的
兩個客觀。
3
敦厚不是天賦。
修補性格,
從不從于假借的補充。
慫恿我的缺陷吧!
鼓動我偏執!
隱在半山的云團:
冒著熱氣,
像個刷白的道觀,
或教堂。
海被囚在經卷里,
持續通脹,
浪之毛邊,
從石頭和樹皮上
采集句子。
聽到你用眼睛談人性,
真好,比看到你的風景,
多了律變之險。
4
海鷗突破了潑墨榕樹
和凜戟椰林,
在草地上專注滑翔。
翅膀起伏,
連綴兩條發白的街道
一起通向浪之層褶。
今天缺點霧,
也就少了點神秘。
昨夜的暴雨在草根上
筑起一個個透明的
水立方。踩上去,
鞋濕了像船吃水。
這里與那里最大的不同,
是天熱,蚊子多。
叮咬大海的皮膚時,
才想起在湖邊打水漂,
投石問路,
彼和此是內應。
2021年7-8月,海口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