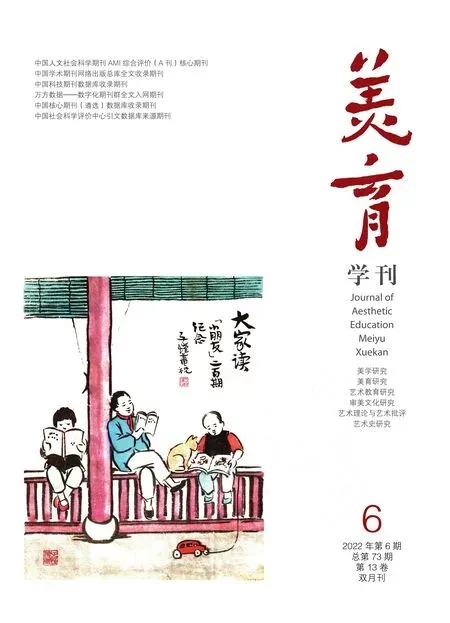在考古與藝術之間
——滕固的美術考古實踐與民族藝術復興理想
韋昊昱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滕固(1901—1941)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奠基學者之一,他的學術工作推動了中國藝術史學在研究目的、敘述史觀、歷史分期、關注題材、史料運用與書寫方式上的極大轉型,標志著現代形態藝術史本土傳統的理論自覺開始出現,對我們理解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學科獨立具有重要意義。
實際上,滕固生前還極為重視對美術考古與國內外重要美術文物遺跡的考察保護工作,這甚至要早于他自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的對中國繪畫史的關注。他的美術考古實踐既有為個人搜集查考一手文物和圖像資料,嘗試打通傳統畫學、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學科界限,從而服務于自身藝術史學術研究的目的,更大程度上亦飽含著因近代中國國勢衰微,文物盜掘外流、文化侵略局面所激發出的一份強烈的民族文化憂患意識與擔當精神。自20世紀30年代后,他更是借助中國首位留德藝術史博士的學者身份,深入參與了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國考古會、中國博物館協會、南京古跡調查委員會、北平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等文物研究與文保團體的籌建,借助行政力量,多次與文博界的其他有識之士一道,在全國各地開展古代美術文物遺跡的考察與保護,系統提出了“辦、掘、保”相結合的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工作規劃。
然而,受史料缺失的影響,目前學界卻較少有針對滕固美術考古與文物遺跡保護活動的深入論述,僅在年譜中有一些對其田野調查時間與地點的簡單羅列,尚停留在籠統粗略的研究層面,且往往語焉不詳,一筆帶過,存在許多關注盲區與缺漏之處,可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文將對滕固的美術考古與文物考察活動加以梳理,揭示以滕固為代表的中國新派學者,借助西方考古學“新知”與國民政府文物保護領域的行政力量,運用物質文化遺存材料,擴展思考視角、研究議題與討論空間,重構中國古代藝術史的書寫敘事,進而建立國民文化身份認同,復興民族藝術精神的治學理想與努力。
一、從留日到留德:滕固美術考古觀念的形成背景
滕固美術考古觀念的逐步形成,與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求學經歷息息相關。1901年滕固出生在江蘇寶山(今屬上海)月浦鎮的一個文人世家,自小受到深厚的古典家學熏陶。1920年10月,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后,滕固東渡日本,進入東洋大學專門學部文化學科就讀。留日期間,他曾感嘆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研究中國藝術,沒有一部統系的書,很是缺點。西洋倒有中國一部分的藝術書。我想將來從中國歷代帝王建都和有名的地方,考察藝術的作品,做成一部大著作,這總是非一朝一夕的事情”[1],已然顯示出其重視文物遺跡調查,并有意識將其融入中國新藝術史書寫的觀念。
隨后在日本長達4年留學期間,滕固多次利用假期前往京都、奈良等古跡集中之地游覽考察,沿途還作有日記和繪畫速寫。他注意將文物遺存放置在藝術史的發展長河之中,作為獨立的“藝術品”加以看待和分析。1922年4月5日,滕固和友人朱小虯一道游覽京都東部音羽山中的清水寺。這是京都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公元778年,其大殿主堂由139根圓木立柱支撐,聳立于陡峭的懸崖之上,氣勢頗為恢宏壯觀,滕固不禁感嘆宗教藝術蘊含其間的創作虔誠與獨特魅力,認為“帝王的藝術、宗教的藝術,這種藝術美姑且叫他權威——教權帝權——的美;無論東方西方的藝術史上,都占了很重大的位置”[2]。4月12日,他又在獨自游覽奈良東大寺時直言,“奈良也是日本的古都,他們稱作文化的發祥地,比較京都還古,在日本的歷史上,美術史、宗教史上都占了極大的位置;他們又稱作南都的,又美其名曰圣地的”[2]。而更為重要的是,在日本游覽考察的同時,滕固的心中還時時飽含著一份對中國人忽視本國古物收藏保存的痛惜之情。當他在京都太極閣外的商品陳列所參觀時,看到日本人精心收藏展出的中國明代絲織品、唐代造像和古代文房用品,深嘆“我很慚愧,那些東西在本國人手里,當是破爛貨不值錢的;落了日本人的手,便稱希世之寶了!使本國藝術的思慕者,發生無限的失望”[2]。而在奈良博物館參觀時,他又看到日本人對文物藏品的選擇和陳列都極為細致,“每一件東西,詳考說明,一方面預備外國人看,譯成英文;而且都加上‘國寶’二個字”,這使他聯想到當時中國人自己對文物保存與研究意識的淡漠,感嘆“我們中國的國寶,國人沒有識得,所以不當國寶的;他們古寺的牌額,也是國寶,也陳列博物館,也有許多考古家定為某朝的遺物。若是在中國,早當柴燒了;我看了,我細細的想去,背上的汗,不住的流下了”[2]。
1925年回國后,在上海美專任教的滕固又和校長劉海粟專程赴山西大同考察云岡石窟。山西和北京的收藏家還向劉海粟贈送了古錢、晉瓦、琉璃瓦獸等一批古物,劉海粟借此在上海美專設立了“古物學教室”加以陳列[3]。1926年4月,上海美專又集中劉海粟歷年所藏文物和校董徐朗西的捐贈文物,開設了“美術史研究室”,由教授滕固和金石考古學講師顧鼎梅指導學生觀摩研究,并對社會各界開放,兩人還對“所藏各品詳加稽考”,編輯出版有《中國美術史料集萃》一書。總之,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留日后至赴德前的這一時期,滕固已經初步形成了對于古物古跡的現代考古研究意識,明確認識到“先民遺制以及金石文書等,不特資好古者之觀摩欣賞,尤可助篤學者讀史時之證發稽考,厥功偉矣”[4]。
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德國留學時期,更是滕固深受北歐考古學,尤其是“譜系類型學”體系熏陶的關鍵階段。1930年5月,時年30歲的滕固初到歐洲,就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國家博物館和鄰近的龐貝古城考察參觀,并撰寫游記《意大利的死城澎湃》一文予以記錄[5]55-64。自18世紀中葉以來,歐洲人對龐貝古城遺址進行了有計劃的發掘工作,增進了后人對古羅馬文明的了解和認知。滕固在文中也極為重視龐貝所出土的考古材料,坦言:“澎湃的歷史沒有文書浩瀚的記錄,要明白它的生長繁榮,考古學家不能不從其遺物里揣摩。這似乎太專門了,然而我們除了考古學家的推斷以外,再不能找出其他容易敘述的資料了。”[5]他參考那不勒斯大學建筑與裝飾美術專業教授費希蒂(Fischetti)所著《澎湃之今昔》一書內容,詳盡介紹了龐貝城市發展的5個歷史分期階段、社會生活概況、考古發掘歷史等方面,并在文后結合龐貝的建筑、雕刻與壁畫文物遺存,分析了其在藝術史上的意義。因此,滕固的此次龐貝考察之行,使他目睹了通過近代考古學知識復原古代文明的經典實例,逐步意識到“那末所發掘的上至高樓大廈下至竹頭木屑,無一不可以參證時代遞變生活情況,這大規模而專門的研究,叫做澎湃考古學(Antishita Pompeiane)”[5]59,體現出其對考古學之于歷史研究重要地位的認知(1)滕固好友譚正璧多年后也曾回憶初到歐洲的滕固,“那是他開始從事于考古的工作,曾專誠去訪過‘美術的都城’羅馬的邦貝,著有《羅馬之游》一文,登在東方雜志上,字里行間,充滿著懷古的幽情,他那時的胸懷全是超現實的”。引自譚正璧:《憶滕固》,載《萬象》1941年第3期。。
1932年2月,已在柏林大學攻讀藝術史與考古學博士學位的滕固,又再次前往意大利羅馬、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瑞士日內瓦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環游,以求進一步深入實地探尋歐洲文物古跡。他曾參觀達·芬奇繪于米蘭圣瑪麗亞感恩教堂修道院餐廳墻壁上的傳世名作《最后的晚餐》,感嘆“一切贊詞不但非過飾,且不足以形容之也”(2)1932年4月13日滕固致留德好友馮至的明信片。。在環游之中,滕固始終對歷經滄桑的殘垣斷壁及其間飽含的歷史深意抱有濃濃溫情,在羅馬時曾在致留德好友馮至的明信片中自言,“今日開始探幽,此系梵師塔利祠堂及楷斯篤樸羅克神廟之遺跡。弟曾低回其下,摩挲其斷碣殘碑,零雕碎刻”(3)1932年2月4日滕固致留德好友馮至的明信片。,足見其徜徉古跡時的懷古之思與沉醉之態,這也對他回國后在考察云岡、龍門、安陽寶山等中國古代石窟造像時所時刻秉持的一種比較藝術眼光的養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柏林大學求學期間,滕固在考古學一科上還師從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古希臘羅馬藝術史家格哈德·羅登瓦爾特(Gerhart Rodenwaldt)教授(4)滕固在自己的德文博士論文Chinesische Malkunsttheorie in der T’ang und Sungzeit(《唐宋畫論》)“前言”中,就明確感謝“時任帝國考古研究院主席的格哈特·胡登萬德(Gerhart Rodenwaldt)”的幫助和鼓勵,見滕固:《中國美術小史·唐宋繪畫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146頁。,并曾受邀參加過柏林考古學會關于亞洲藝術的講演活動。總的來說,在留德期間,滕固逐漸養成了親歷遍訪歐洲各地歷史古跡與文化名城的治學習慣(5)在1932年6月11日因申請博士答辯,而撰寫提交給柏林大學哲學學院的簡歷中,滕固自稱“在大學假期期間,本人出于研究的目的曾在法國待過2個月,在意大利待過3個月”,柏林洪堡大學檔案館藏。,正是同為留德好友朱偰所回憶的“(滕固)其在歐游蹤極廣,嘗西游巴黎,南訪羅馬,所至探求古跡,結交名士,尤以所學為藝術史,故對于文藝復興時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羅娜(Verona)、米蘭(Milan)——尤三致意焉”[6]。這使他有機會超出當時國內舊學一派所謂考古學僅為“證經補史”之史學附庸的普遍認識,直接奠定了滕固此后始終注意將考古出土材料引入藝術史研究的學術基礎與治學眼光。
二、國家級文保機構的出現:滕固與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成立
1932年冬,滕固自柏林返回上海,自此之后直至1941年逝世前,他憑借著自己的留德學者身份,始終積極參與國內一系列的文物遺跡調查保護、博物館學、考古學、檔案學、現代藝術教育和中歐文化交流等領域的官方事務與民間工作。
1933年5月14日,滕固與蔡元培、劉海粟、葉恭綽、王濟遠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考古會(初名“藝術考古學會”),并與鄭午昌、董作賓等6人被推選為委員會委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國內新派學者對考古學的認知,已經由自晚清以來一個與地質學、地理學、古人類學等聯系密切的模糊化西學知識,進一步深入認識到考古學是一個具有系統方法,能夠嘗試與傳統史學文獻互為補證,甚至超越史籍記載,研究人類進化、人種起源和早期中國上古文明,彰顯民族文化博大遺產的重要“科學性”工具。這種觀念的普遍確立當然也受到了20世紀20年代一批田野考古發掘活動尤其是20年代后期中國人開始獨立進行田野發掘的影響(如1921年的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1926年的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1928年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和1930年至1931年的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發掘等)。這使得重視實物性的古物研究在中國現代新史學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成為追求重建歷史客觀真相的重要利器,受到了這一時期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中國考古會便是“以搜考歷代遺物,發揚吾國文化為宗旨”[7],提出了一套偏重于考古成果展示與文物保護的工作設想(6)中國考古會成立時所提出的主要工作計劃包括“(1)搜集考古各項資料(2)發布古物之復制品及關于考古論著(3)舉行關于考古之展覽及講演(4)籌設考古研究與博物館(5)接受政府與公團之委托辦理考古的設施事宜(6)協助保存古物”,見《中國考古會成立》,《申報》1933年5月15日,第11版。,并集合了中國文化界、學術界、教育界與文物考古界的重要學者共70余人。在由包括滕固在內的發起者寄給其他學者們的邀請通函中,系統陳述了這一學術團體對中國文物考古與保護事業的呼吁與期許:“中國歷代遺物,非僅欣賞美術之所宜珍襲,抑亦研究歷史之必要資料,無論政府社會,皆有維護搜討之責。顧比年以還,災事迭興,勝區零落,現存遺物與夫出土寶藏,不罹自然銷亡,即遭海外劫奪,社會人士,深痛惜之。蔡孑民、葉譽虎、劉海粟、顧鼎梅、關百益、王濟遠、滕固諸先生有鑒于此,特發起中國考古會,期以群力搜考先民遺澤,維護前代文化,切磋流通,相觀而善。”[8]這段話亦可看作是這一時期滕固及其同仁對開展中國美術考古工作必要性的整體思考。
兩年后的1935年年初,時年35歲的滕固完成了對瑞典國立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奧斯卡·蒙德留斯(O.Montelius)《先史考古學方法論》一書的翻譯工作。該書是1903年蒙氏所著德文專著《東方和歐洲的古代文化諸時期》(Die?lterenKulturperiodenimOrientundinEuropa)一書中《方法論》部分的摘錄,滕固直接從德文原版翻譯而來,首次為中文學界貢獻了“體制學方法”這一考古學新術語,并隨著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而在國內學界流傳漸廣。20世紀80年代,新中國考古事業的領導人夏鼐就曾回憶自己早年閱讀過蒙氏《方法論》的日文譯本和“從德文直接譯出的漢文譯本”[9],顯然指的就是滕固的這部譯作。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際,國內學界還未有關于“譜系類型學”的準確中文譯名,仍然在照搬英文的“Typology”一詞。如1926年4月16日李濟在清華學校大學部的講演中就是這樣處理的,并聲明“這個名詞,尚沒有一個好的漢譯,所以暫用原文”[10]。從這一背景來看,滕固德文考古學譯作及其創制新名詞的學術貢獻,在民國考古學史中的先驅意義當不容低估。滕固的翻譯秉持著自藝術史研究出發的視角,坦言“譯者于先史考古學原非專攻,但在學習藝術史時,對于古代部分不能不涉覽先史學者之著述,資以辨證疏通,正巧蒙德留斯博士之著作,對于藝術史學者最有幫助”,他還在列舉了蒙德留斯的一系列考古學著作后高度評價,“沒一種不是并世藝術史學者引為最善的參考材料”[11],于此可見彼時已然成為藝術史家的滕固,力求采補西學,“資以辨證疏通”藝術史(尤其是偏重關注造型與紋樣等藝術形式的風格學取向)與考古學兩大新興學科與研究方法的希冀與努力。
而相較這些來自滕固個人的學術翻譯工作與籌建民間社團的自發行為,南京國民政府針對文物遺跡考古與保護的官方舉措無疑更為實際有效。1932年6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第82次會議正式通過了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決議,聘任李濟、葉恭綽、黃文弼、傅斯年、朱希祖、蔣復璁、滕固、傅汝霖、董作賓、馬衡等13人為委員,滕固還當選為委員會常務委員,由傅汝霖任主席。
從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名單中不難看出,這一由南京國民政府官方領導的文物保護機構,云集了一批民國時期南北方重要的考古學家、文物學家、歷史學家與文博學術機構負責人等專業學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史語所考古學組主任李濟、專任成員董作賓、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北平研究院考古學組主任徐炳昶(與馬衡同為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成員,亦為1927年至1935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長)、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專任研究員黃文弼(曾撰寫《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等田野考察報告,后于1935年4月任中古會駐西安辦事處主任)、上海市博物館董事長葉恭綽、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舒楚石,都身居委員行列。這顯示出20世紀3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為代表的國立學術研究機構,與委員會在學術理念旨趣和發展方向規劃等方面的內在聯系,使得委員會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在嘗試結合田野考古實地調查與文物保存陳列等多方經驗,力圖成為一個涵蓋文物遺存從科學發掘保護到科學陳列與研究全過程,面向文物發掘與保護法規制定、統籌指導各地方政府文物保護行政力量、調動各大文博學術機構研究群體等諸多環節的綜合性中央決策機關,而親身接受過德國學術訓練,且唯一具有專業藝術史學科背景的滕固,始終是活躍其中的核心成員之一。
三、“辦、掘、保”相結合:滕固美術考古思想的具體認知與實踐
1934年至1936年間,作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的滕固,代表政府官方集中開始了多次河南、陜西、山西文物考察之行,先后與黃文弼、董作賓、陳念中等學界同仁,親赴江蘇徐州,河南開封、安陽、洛陽,陜西西安、咸陽,山西大同等古城。他在每一站都注意前往當地的文物古跡、博物館與考古發掘現場作實地考察,整理撰寫日記體游記《視察豫陜古跡記》(1934年)、《訪查云岡石窟略記》(1935年),公文報告《視察汴洛古物保存狀況報告》(1936年)等,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和各地方政府提出了諸多有關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的真知灼見與工作規劃。
(一)對考古出土文物性質的看待
1934年12月,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現場的考察中,滕固明確表達了自己作為一位新派學者的現代文物觀,強調了在發掘過程中對文物出土原狀現場保護的重要性,認識到出土文物如脫離原初語境,則會喪失大部分的藝術史研究價值,顯示出對考古地層次序的重視。同時,滕固明確提出了文物國有的方針,指明出土文物作為“證經補史”的重要新史料,理應歸國家與公眾所有,而一旦如古代那樣繼續流入古董家秘不示人的私藏之中,則無異于石沉大海,其他學者亦無法經眼和展開研究,這直接關系到現代學者對中國古史系統的重構問題。此外,滕固還清醒地認識到文物遺存是民族文化的結晶和載體,而放任文物外流無疑是“國家之重大恥辱”[12],展現出維護本國珍寶的堅定決心。
(二)“辦、掘、保”相結合的考古發掘與文保規劃
1936年11月,在第二次洛陽文物考察中,滕固敏銳地觀察到此前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河南地方,都對文物的出土發掘頗為積極,而對制止文物流散盜掠的工作卻多屬消極,缺乏系統性的工作規劃與文物保護陳列的專門機構。基于這種現狀,滕固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建議,明確提出了一套“辦、掘、保”三管齊下的文物發掘與文保規劃。在“辦”的方面,1936年11月20日,委員會在洛陽正式設立駐洛辦公處,聘請傅雷和考古學者荊梅丞兩人留駐洛陽,擔任正、副主任,以“會同地方軍政機關辦理制止該地毀損古跡古墓,計劃保管古物,并登記龍門石刻各事項”[13]13-14。在“掘”的方面,滕固強調了出土文物歸屬權的問題,認為應由國家組織公開的考古發掘工作,杜絕私人盜掘行為,并提議由已有相當考古發掘經驗的中央研究院和河南古跡研究會等單位在洛陽開展考古工作。在“保”的方面,當時河南僅有在開封的河南博物館一處機構,但文保設備和條件已顯簡陋,鑒于這種現狀,滕固提出了在洛陽建立古物陳列館的設想,“以期負集中保存便利研究之責”[13]13。
(三)對實物材料的個案專題式研究
滕固的歷次文物遺跡考察都貢獻和啟發了許多他寫作專題論文時的切入視角、研究思路與史料準備,促使其將關注重點開始放在了陵墓雕塑、畫像磚、瓦當、建筑構件、神道石柱、碑刻裝飾等非繪畫性的物質文化遺存材料上,如在先秦至漢魏六朝雕刻裝飾藝術與域外風格影響研究專題中,滕固就先后撰寫發表了《霍去病墓上石跡及漢代雕刻之試察》(1935年)[14]、《漢代石造圓雕之形式的觀察》(A Few Notes on the Forms of Some Han Sculpture,1935年)[15]、考察報告《六朝陵墓石跡述略》(1935年)[16]、《燕下都半規瓦當上的獸形紋飾》(1936年)[17]、《西陲的藝術》(1936年)[18]、《南陽漢畫像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1936年)[19]6篇中英文論文,翻譯英文論文《漢代北方藝術西漸的小考察》(1935年)[20]1篇,并先后發表了《六朝石刻與印度美術之關系》(1925年)、《茂陵和昭陵的偉大史跡》(1936年)、《中國古代樂舞》(1937年)3次公開學術講演。
滕固善于對研究對象逐一作細致的圖像內容描述,并按照風格與紋樣的演進過程加以分類,依據其圖像特點差異進行年代排序、總結和定名,具有鮮明的考古學譜系類型學的方法論意味。通過立足文化史根基的比較藝術學眼光的運用,他積極引入中亞、印度、歐洲等外來文明的不同類型材料予以比對參證,注意找尋彼此之間的關聯節點,力圖在中外文化混交的理論框架之下發現研究對象的風格史脈絡,為空間與時間上的歷史坐標定位,從而將中外藝術混交匯融的“長時段”歷程逐步可視化。在各項專題研究中,他還注意提煉研究對象在中外文化史、藝術史上的價值意義,踐行他要“使吾民族之藝術業績,在世界文化上獲得更正確之評價”的治學理想[21]74,并進而試圖以藝術作品形式風格的自律性變化來論證對應時代的審美趣味、審美主題與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異性,這背后顯然帶有了一種圖像志色彩的思想史意味。
但與此同時,滕固也并非一概而論地將中國本土藝術風格的形成簡單視作是對外來影響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于實地考察與個案專題研究相結合的問題意識,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客觀實證態度,將“二重證據法”應用于中國藝術史研究中,初步打通了不同類型實物材料遺存之間的內在關聯。他絕不亦步亦趨地輕信、迷信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歐洲學者有關“中國藝術西來說”的先行研究結論,在對戰國瓦當獸形饕餮裝飾紋樣、漢代石刻動物雕塑風格溯源等研究上,都有著自己明確的獨立見解,甚至認為中國本土的裝飾樣式還出現了對外輸出傳播的現象(如他的譯作《漢代北方藝術西漸的小考察》即有此種觀點),這都使得他極為清醒地不去忽視先秦以來中國自有藝術風格傳統對后世的傳承影響。
四、結語
通過參與國內的考古發掘、文物考察與文保工作,滕固得以大力宣傳文物盜掘外流對于學術研究和國家聲譽的損害,積極實踐歐洲考古學理論與文物保護方法,并加以思考如何與自身研究相結合,處處尋找著符合自己新藝術史眼光與期待的重合點。這些思考正伴隨著他一生藝術史研究方法逐步成形定位的關鍵時期,這一階段滕固在中國古代繪畫史研究中面臨實物不足,仍然不得不大量依靠畫史文獻敘述的尷尬兩難境地,這是促使他注重轉向關注美術遺跡調查、推動考古學和現代文保事業在近代中國建立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而他對出土文物與圖像新史料的重視,反過來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風格分析和考古類型學方法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中的探索實踐。這種學術趨向顯著推動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藝術史研究,開始由傳統畫學過多倚重傳世文獻研究一路,逐漸轉向文本與實物(包括書畫、器物、金石碑刻、古跡名勝等多種物質遺存)研究的結合,將不入古代畫史記錄的邊緣對象作為中國藝術史研究問題的一部分來看待處理,同時引入域外文化史、藝術史的材料與研究視角,通過中外藝術史問題的比照思考,使得這一學科所納入討論的空間與時間維度都大大增加延長,有關中國藝術的歷史解釋自此開始變得更為豐富和多元起來。
在美術考古的研究方法上,滕固則轉向了實證與闡釋并重,將研究問題專題化,注意田野實地調查和對古物“原境”現場的還原,形成現代“田野”研究意識。這也啟發了隨后王子云、常書鴻、史巖、馮貫一、岑家梧等人在20世紀40年代組織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敦煌藝術考察團等針對西北、西南地區古代美術遺跡調查與研究的追隨之舉,一場在抗戰內遷背景下由中國新派學者和藝術家所共同發起的“本土西行”“發現西部”的文化尋根運動由此展開。
這種不辭勞苦的美術考古實踐,正凸顯著中國學者以民族藝術研究事業復興民族精神的堅定決心。1936年,滕固在《西陲的藝術》一文結尾中便不無激動地反問道:“西陲的探險,嚴格地說,自前世紀末至今世紀,凡四五十年之中,俄國、英國、德國、法國及日本,屢次派隊前往,掠取珍貴的遺物而畀歸于其國家。雖然憑藉他們的這種壯舉,使我們對于西陲的認識,日益增加光明,但我們反省起來,真覺得奇恥大辱。第一,在我們的版圖內的邊陲要地,為什么讓他們任意角逐?第二,這種學術的探險工作,我們為什么不搶先去做?我們可以從酣夢醒過來了,我們應該趕上前去洗雪這種被侮辱的奇恥。”[22]1937年滕固在中國藝術史學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上,則再次強調了自己近年來的觀察,“吾國藝術珍品,被攫取捆載以去,而散佚海外者,亦不可以數計。今吾人于探討之時,若干部份須采其印本以為參考,或竟須遠涉重洋以求目驗,恥孰甚焉”[21]73,從中不難看到,那些溢于言表的“慚愧”“憤慨”甚至是“奇恥”的痛疾之語,恰恰正是驅動中國學者在孜孜以求的學術事業耕耘背后的情感關鍵詞。這一時期又正值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日本對華北在軍事和政治上施加空前壓力的階段,日軍侵占華北、蠶食中國的野心可謂昭然若揭,華北地區重要古跡集中之地的文物保護壓力,自然也在無形中增大,不能不引起各方憂心,而此時中國學者不遺余力的文物考察與文保努力,則更帶有了一份捍衛中華文明,重拾民族文化尊嚴的雪恥色彩。
因此,滕固的美術考古與文物遺跡考察保護工作,無疑與近代中華民族國家的概念建構、民族文化的轉型傳播,以及民族藝術精神的復興理想緊密合拍,守住民族文化的遺產財富并加以保護,傳之后世,就成了找尋族群意識、建立國民文化身份認同、宣揚國族昔日輝煌的應有之義。20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民族本位文化建設的倡導(7)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圣、章益、陳高傭、薩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要使中國在文化領域抬頭,必須從事中國民族本位的文化建設。,彰顯出“整理國故”運動思潮之下學者們強烈的文化憂患意識、認同自許與擔當精神,也反過來推動了近代中國藝術史家對物質文化遺存屬性、史料性質與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更新,為當下的中國美術考古事業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體制性遺產,給予當代學者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