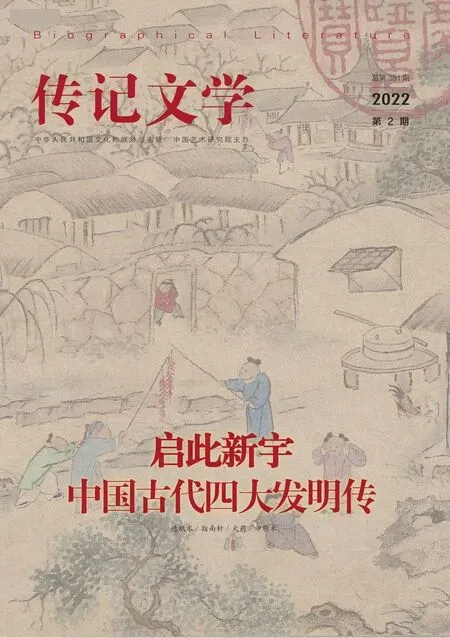“途中的鏡子”
——邁克爾·霍爾羅伊德《利頓·斯特拉奇傳》中的重構與同構
鐘 芳 梁慶標
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英國傳記家邁克爾·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1935—)從伊頓公學畢業后便進入律師事務所工作,隨后入伍,自1958年離開軍隊后專注于寫作,但他一直強調梅登黑德公共圖書館才是他真正的“母校”,他感興趣的是人性而非法律條文。或許正是此種生活歷程和認知讓霍爾羅伊德有別于其他學者型傳記家,賦予其傳記書寫以別樣的筆觸。實際上,20世紀40 至60年代,事實性和學術性傳記取代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傳記和后斯特拉奇式的人性化傳記而主導著生命寫作,它們犧牲了分析闡釋和美學上的完整性,轉而強調傳記的事實細節和客觀有限的闡釋。在這樣的潮流下,霍爾羅伊德的傳記無疑也帶有嚴肅細致的學術性,但又不同于一份冰冷的研究報告,而是帶有溫度、可讀性強的散文式傳記,內里尚有動人的情感力量,足以喚起讀者的同情與對傳主命運的思考。霍爾羅伊德的第一部傳記《休·金斯米爾傳》(1964)反響平平,隨后因其為利頓·斯特拉奇、奧古斯都·約翰和喬治·蕭伯納撰寫的三部傳記而聲名鵲起。其中,兩卷本《利頓·斯特拉奇傳》(1967—1968)是關于斯特拉奇的權威傳記,獲得1968年《約克郡郵報》圖書獎()。后來,因大量相關材料的涌現和普通讀者對長篇累牘傳記的敬而遠之,此傳被重新審視和刪改,并最終以一卷本《利頓·斯特拉奇傳》(,1994)的形式出現。諷刺的是,恰恰是霍爾羅伊德的傳主早在1918年就發出預言:“保持精簡,是一個傳記家的首要責任。”1995年,克里斯托弗·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將其改編為電影《卡琳頓》(),將斯特拉奇和卡琳頓兩人的愛情故事搬上銀幕,很多觀眾深受感動,霍爾羅伊德也由此名聲大噪。
《利頓·斯特拉奇傳》(以下簡稱《斯特拉奇傳》)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重點介紹了斯特拉奇的家庭環境和從劍橋大學畢業前的求學生涯。在這個部分,霍爾羅伊德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認為斯特拉奇的同性戀傾向部分歸結于其家庭生活中父親的缺席和母親的主導地位,而將斯特拉奇性格中的陰郁成分歸因于其居所——蘭開斯特門的昏暗、閉塞、壓抑和維多利亞的時代氣息。劍橋大學作為斯特拉奇逃離家庭后最重要的精神歸宿,是孕育其思想和創作活動中反叛因素的圣地:G.E.摩爾《倫理學原理》()為他的同性戀情感沖動提供了一個“科學框架”,斯特拉奇直呼這本書的出版是“理性時代的開始”;加入秘密社團“使徒會”(the Apostles)讓他從沉默壓抑的長期歲月中得到解脫,大膽說出他的所思所感。霍爾羅伊德還將斯特拉奇界定為劍橋大學的“無冕之王”,認為他的影響至少囊括劍橋大學的三屆學生,甚至波及整個英國社會的宗教態度、帝國主義論調和性觀念。第二部分講述了斯特拉奇離開劍橋大學后五年間的賣文生涯,除了給《旁觀者》雜志供稿,他還試圖跟梅納德·凱恩斯保持通信以獲取劍橋大學的動態,并與鄧肯·格蘭特發展了他第一次明確的同性戀情感,當得知凱恩斯和鄧肯成了秘密情人時,他陷入了人生的黑暗時期。其中,霍爾羅伊德還提及斯特拉奇與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相遇以及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初步形成。第三部分主要圍繞斯特拉奇所在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在1910年至1918年間的活動展開,還涉及斯特拉奇對亨利·蘭姆、魯伯特·布魯克、拉爾夫·帕特里奇等人的迷戀,與弗吉尼亞·伍爾夫、奧特蘭·莫瑞爾女士(Lady Ottoline Morrell)的介于友情與愛情之間的情感,其中,莫瑞爾女士身上的男子氣和異裝癖激起了斯特拉奇關于雌雄同體的想象,為他書寫弗羅倫絲·南丁格爾、維多利亞女王和伊麗莎白女王提供了想象和范本。這個時期是斯特拉奇事業上和精神上的轉折點,他陸續創作了《法國文學的里程碑》()和《維多利亞名人傳》(),霍爾羅伊德注意到斯特拉奇表面上仍然羞怯,仍會夸大他在情感或寫作上遭遇的挫折,但他的自信正在逐步增長。第四部分重點寫斯特拉奇和多拉·卡琳頓、拉爾夫·帕特里奇之間的三角戀情,他們自1917年開始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2年斯特拉奇因胃癌去世,卡琳頓開槍自殺。
《斯特拉奇傳》的形式總體上因襲常規,按線性時間序列講述傳主的生平,里面充斥大量細節、軼事和人物對話,不禁讓人聯想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傳》,就如鮑斯威爾詳細記錄約翰遜博士的音容笑貌和只言片語,霍爾羅伊德以斯特拉奇的日記和大量書信為依托,且將其中的大部分以直接引語的形式呈現,讓讀者最直接地感受到斯特拉奇的獨特聲音,生動地塑造出一個理性又浪漫、自卑又傲慢、以愛為信仰卻無法獲得理想之愛的波西米亞式藝術家。但霍爾羅伊德最獨特的地方在于,他嘗試模仿斯特拉奇的聲音進行敘述,試圖使用斯特拉奇自己的“短語、句子節奏和其他文體特征”來說明傳主的生活和工作之間的聯系,以至于讓讀者最直觀地感受到傳主的心理和個性,甚至全然沉浸在斯氏的內心深處。傳記中有不少修辭采用了抒情的調子,比如在描寫斯特拉奇瀕死之際,作者描繪出生命消逝時的靜謐和斯特拉奇親友們無言的悲傷:
其他親戚朋友也趕來了,他們的車在碎石路上前后顛簸。自圣誕節以來的霜凍天氣仍在繼續。這樣的天氣里,萬籟俱寂——利頓一直很喜歡這種天氣。一層薄霧罩著草地,掛在榆樹上。陽光從樹枝丫間灑下,落在草坪上,似乎徘徊著、猶豫著,才觸到墻壁,透過窗戶傾瀉而下。護士們進進出出,忙里忙外。其他人則緊張、沉默,似乎陷入了夢幻般的靜止狀態。在等待的時候,他們不可能不將這種美與利頓的死相提并論,也不可能不去想利頓留下三人之間失衡的捆綁關系,會有什么樣的結果。
霍爾羅伊德著迷于斯特拉奇成長時期影響其性格形成的環境、事件和他曲折的情感經歷、心理變化,卻對他作為傳記家的成功經歷的美化和戲劇化提不起一點兒興趣——吸引霍爾羅伊德的往往是斯特拉奇創作時陷入的黑暗時期和成名后的矛盾心理。為了重建已然逝去的、在當下已過時的知識和藝術世界,霍爾羅伊德還圍繞著維多利亞時代傳記的終結者——斯特拉奇刻畫了布魯姆斯伯里團體肖像,為掀起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熱推波助瀾。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60年代是西方晚近文化歷史的分水嶺,《斯特拉奇傳》則是60年代文化歷史中生命書寫的一大里程碑,它對斯特拉奇同性戀情感的書寫“開辟了生命寫作中同性戀話題領域”,具有不容忽視的歷史意義。
不得不提的是,“每一個真理都必須有一個殉道者”。1967年至1968年,《斯特拉奇傳》一經出版,就在英國社會引發了軒然大波,首先遭到了與斯特拉奇有關的人物的“大規模鎮壓”,此傳面臨無法出版的危機,霍爾羅伊德也遭受著指控的威脅,因為這部傳記損壞了他們的名譽,破壞了他們的幸福,給他們帶來或大或小的不幸——此傳揭露了斯特拉奇以及他所在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同性戀傾向和行為。幸運的是,這些謾罵后來被溢美之詞蓋過,“后者不僅來自將斯特拉奇視為英雄的同性戀者,也來自樂于看到一堵文學柏林墻被逐漸拆除的傳記家同行們”。反觀之,種種抵制和鎮壓恰恰說明了這部傳記的真實性,可以說,此傳是對斯特拉奇人生最為真誠的書寫,也是斯特拉奇作品最為詳實的注腳。然而,“所有的傳記都在它自身內部笨拙地掩蓋著一部自傳”,傳記家看似“以觀察別人為己任,他其實是在尋找、記錄、懷疑和求證自我”。《斯特拉奇傳》亦如此。霍爾羅伊德在斯特拉奇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成長時期的灰暗色調、充滿愛與欲望的生命激情、修正傳統禁令的強烈愿望。此外,這部以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期作為單一時空的傳記里,還貫穿了霍爾羅伊德作為20世紀觀察者的審視和反思的目光,構建了一個跨越維多利亞時代和后現代的世界,在兩個時代互相對話的間隙,彰顯出霍爾羅伊德對人類存在本身的重構和傳記家、傳主兩個世界之間的同構性。
的確,“藝術家并非總是應時而生,很難簡單說一位作家歸屬于哪個時代”,但可以斷言的是,霍爾羅伊德“走在時代的前面,為模糊難辨的未來發出預言”。為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的延續和生活方式的穩定”,與60年代其他中產階級的孩子一樣,霍爾羅伊德一代接過從父輩手中遞來的經驗——不管是政治、文化、經濟方面,還是藝術標準、性別層面上的。最初,公開的“有傷風化”的性關系是明令禁止的,但沒有涉及刑事犯罪。然而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政府推出《拉布切爾刑法修正案》,首次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犯罪。后維多利亞時代的衛道者則狂熱到了極點,他們依據“官方”指示,制定了一系列防止出現同性戀行為的措施。在霍爾羅伊德中學時期所在的伊頓公學,與男校制度一起保留下來的是同性戀的審查制度和清洗行為。順從的父輩們道貌岸然,遵從著那一代的道德怯懦,對同性戀和性話題抱有很大的敵意,他們“從來就不從藝術本身來判斷藝術品的優勢,他覺得自己對藝術一竅不通,于是傾向于從道德上進行評判,尤其是從性方面來評判,即根據身體某些暴露程度來評判”,遂將道德標準植入藝術評價當中。然而,霍爾羅伊德一代對祖輩們和父輩們的遺產感到困惑,因為在他們看來,愛是無差別的,性是自然的,在男孩間這種浪漫友情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恰恰是傳統的社會規約造成人自然情感的復雜化。
此外,在霍爾羅伊德書寫和出版《斯特拉奇傳》之際,同性戀尚未被合法化,保守派還專門成立“凈化聯盟”,整飭文藝作品中的有害內容,重申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秩序——正確的性道德和性取向、倫理、貞操等,霍爾羅伊德不得不面對傳記無法出版、遭人控訴、名譽受損等現實問題。然而,正如他所言“很多都沒變:但一切即將改變”,延遲了十年之久,《沃爾分登報告》即同性戀合法化報告正式成為法案,《斯特拉奇傳》遂成為“后沃爾分登”時代的第一部傳記。在沉寂了整整一代人后,英國社會終于公開允許霍爾羅伊德實現其宣言:“在我的書中給予利頓的愛情生活以與其職業生涯一樣的突出地位,追蹤它對其工作的影響,并且公開地對待整個同性戀主題——就像我對待異性戀一樣。”從這個層面上看,可以說《斯特拉奇傳》得以出現的前提,是它借以探究斯特拉奇一代、霍爾羅伊德的父輩一代和霍爾羅伊德一代“變化途中”的基礎,一種共通于三個時代的時間,而《斯特拉奇傳》所揭示的,恰恰是一個“正在變化”的“途中”,在《斯特拉奇傳》發表之前,有關這個“變化的途中”的決定性事件——《沃爾分登報告》已然出現,但實際上霍爾羅伊德早就對這個“變化的途中”作了揭示和賦形——《斯特拉奇傳》文本內部的完成,或許可以說,這是傳記家對既往歷史的一次勝利。
正如詹明信所言:“論者在提出歷史分期的假設時,往往會為求同而存異,結果把活生生的歷史時刻簡化為龐大的論述同一體。”而實際上,歷史的意義總是開放的、流動的,既往的歷史并非是徹底的死寂。霍爾羅伊德看到了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中后期的相似性和歷史的延續性,并認為傳記恰恰“能給歷史帶來人性化效果”,所以在癡迷地描繪斯特拉奇時,還著重復現了這兩個時代的精神,重建了歷史與現實間的橋梁,在這種宏闊的歷史背景中,傳記家和傳主所處的時代無疑可以形成一種對照和同構。斯特拉奇所處的維多利亞時期,由G.E.摩爾《倫理學原理》的出版和劍橋大學同性戀風氣的盛行所共同開啟的“新文藝復興”,給當時虛偽的社會帶去的沖擊力絕不亞于霍爾羅伊德所處的20世紀60年代性解放運動,兩次解放運動相呼應,共同推動著人類關系的重新定義。而霍爾羅伊德在傳記中公開討論同性戀的愛情生活、性生活正是對斯特拉奇未竟事業的接續。詹姆斯·斯特拉奇相信,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會把傳記中暗示的事變成一場明晰的自傳運動,以實現同性戀和異性戀在法律下的同等待遇”。另外,福柯曾提出“另一類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維多利亞時期性禁錮下的一群異類,包括同性戀、娼妓、嫖客、歇斯底里者等,他們雖被排除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主流之外,但仍是社會無法回避的存在,甚至可以說,他們是聯結維多利亞時代和后現代的紐帶之一,因為他們身上表現出的特質,無不讓人聯系到后現代的文化特征:同性戀文化、性科學、高雅與通俗文化的融合,等等。而對于這兩個時代來說,最具創傷性的記憶分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二戰后成長起來的作家,霍爾羅伊德親歷了戰爭給家庭帶來的分裂,給人情感帶來的枯竭,所以在評論或闡釋斯特拉奇《維多利亞名人傳》的寫作、出版和反響時,他多次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他認為《維多利亞名人傳》出版之際,恰逢人們對大炮和大話相當厭倦而樂于看到斯特拉奇對鼓吹戰爭的自命不凡者的譏諷,這部傳記正是在這種契機下大獲成功;斯特拉奇寫作時,目睹了戰爭的偏執和歇斯底里,人輕易地放棄了自己的人性和個性,為此,除了在傳記中控訴福音傳教,提倡自由主義,他還試圖宣揚人道主義,以隱微筆法反思帝國主義,尤其是在傳記最后一章“戈登將軍的末日”中,批駁了英國帝國主義用非正義、偽善、屠殺來取代文明的發展。
簡言之,兩個時代的相似性和相關性——后現代文化往往可以在維多利亞時代找到它的根,給予了霍爾羅伊德關于歷史的鉤沉和傳記的資料。一方面,霍爾羅伊德自身的經歷既不完全包含在傳記中,也不排除在其外,正所謂“缺席的身體、在場的靈魂”。當斯特拉奇的生活細節、心理和話語出現缺損時,霍爾羅伊德轉而反觀自身,以一種平行世界的參照關系填補這種空缺。另一方面,當傳記材料和歷史的關系處于一種開放狀態,或者當傳記家和傳主的關系處于一種敞開狀態時,霍爾羅伊德將后現代社會作為參照系,以此重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特征。這也就是為什么他會首先注意到斯特拉奇居住長達25年之久的蘭開斯特門,并在傳記開篇就為其描述了一幅極具想象力和實質性的圖景——“如果說客廳是一座為維多利亞精神而建的廟宇,那么它的祭壇無疑是一個高聳而精致的壁爐臺……”的確,早在1764年,貝卡利亞就在形而上層面指出家庭可以代替教會和國家剝奪個人自由,會在有形或無形之中給個體帶去不幸。但霍爾羅伊德的這個描述不僅是超現實的,也具有社會象征性,它以隱喻的形式重構和具象化了維多利亞時代和身處那個時代中的個人家庭的整體環境,從而活現出斯特拉奇的困境,破除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神話”——“紳士的家”和“甜蜜的家”。霍爾羅伊德將蘭開斯特門看作充斥著維多利亞精神和氣息的整個時代的縮影,并將其視為斯特拉奇個人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象征:它的陰暗處讓人不由自主地迷戀,其宗教性陳設卻散發出陳舊的傳統主義氣息——約束和壓抑,使得斯特拉奇的“快樂逐漸消退,健康狀況也在下降”,對“傳統”的厭惡也由此根深蒂固。霍爾羅伊德似乎認為,斯特拉奇對這座宅子迷戀和厭惡態度的對比,與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矛盾態度相一致:他一面醉心于維多利亞時代之謎,一面又急切地想逃離這座“奇怪的陵墓”,甚至拋給這個“陵墓”所代表的維多利亞時代一聲反叛的驚雷并渴望“新時代”的到來以治愈他的一切痛苦。
而要進一步理解這種另類的家庭譬喻和想象,不得不聯系霍爾羅伊德在其自傳《巴茲爾街的布魯斯》()中提及的兩個失敗的家庭組合:他逃離父母不幸婚姻的陰影,前往祖父母的家諾赫斯塔,不料祖父母要么爭吵不休,要么無愛地沉默,整個家庭沒有真正的交流,沉悶閉塞如同“膠囊”。另外不能忽視的是,霍爾羅伊德想象斯特拉奇對其父最早的印象只有“堆滿文件的辦公桌”,也與霍爾羅伊德對父親無法讓家人擺脫孤獨的譴責、對父愛的渴望不謀而合。可以說,對家庭不幸的思考從小伴隨著霍爾羅伊德,就如同蘭開斯特門一直縈繞在斯特拉奇的夢境之中,他們共同期待的是一種更為寬闊的情感視野。但也正是這種復雜的自我意識和心理洞察使霍爾羅伊德獲得了內省的才華,通過反觀自身,他將籠罩斯特拉奇一生的時代的精神黑暗具象化為蘭開斯特門,讓這座“陵墓”成為其理智和情感上的奠基,成為使斯特拉奇成其為斯特拉奇的決定性條件。總而言之,這兩個關于家庭的譬喻相呼應,共同完成了有關個人存在本質的主題,雖然所謂的“陵墓”和“膠囊”最終消失在身后的虛無之中,霍爾羅伊德和斯特拉奇卻攜著一代人的記憶活了下來。
與此同時,霍爾羅伊德的同構并非是單向度的——傳記家作用于傳主,它還表現為“傳主—傳記家”來回往返的思辨過程。霍爾羅伊德曾多次強調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在孩童時期,他“有雙重體驗:父母的婚姻不幸破裂,祖父母婚姻的不幸沒有終結”,以致在家庭大戰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相形見絀。另外,他還自述道:“我幾乎是由我的祖父母撫養長大,我按照他們的節奏和狀態生活——也就是說,我七八歲的時候處在七八十歲的人的管理體制之下。”為此,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感到生活在人群中的沉重,直到找到傳記作為他逃離家庭的方式。在傳記中,他試圖沉浸在他人的世界來忘卻自我、求證自我。于他而言,“寫作是消失的一種形式”,是跟隨傳主進行一次形而上學的獨自的旅行,為了開始自我探尋之旅,他“不僅必須讓他人遠離自己的生活,還必須遠離自己的存在”。但與卡夫卡在《在流放地》中要求作者進行自我消滅所呈現出的文本的內部暴力不同,霍爾羅伊德的“自我消失”其實是一種“自我重構”——“我觀察故我在,我是我所觀察之物”——他在傳主身上發現、塑造自我。實際上,這也是整個后現代社會對“自我”的一種審視,一次由“主體異化”向“主體消亡”的嬗變。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充滿動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沖擊、性解放、“反文化”運動,導致文化、宗教和傳統價值觀的崩潰和逐漸遺失,個體較之以往雖有更多自由,但隨之而來的是空前的無序和困惑。正如A.S.拜厄特所言,很多后現代作家回到歷史小說創作,是出于對“自我”的懷疑:“我們或許不過是一系列分離的感官—印象,記憶中的事件,一些移動的知識,觀點、意識形態的片段和回復的儲備庫。……在不朽靈魂的消失之后,是發展完善而連貫的自我的消失。”換言之,即便是“上帝死了”,后現代社會也仍未越出蘇格拉底所說的“認識你自己”,相反,在后現代的存在困境中,他們書寫過去“是為了像本雅明說的那樣,‘炸開歷史的連續體’,在我們的現在時刻與可以贖救的過去某時之間鑄造銜接點,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解讀我們自己的時代”。與同時代的一些作家一樣,霍爾羅伊德的傳記書寫不僅重構了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中后期的文化層面和政治歷史,還試圖解答當代的一個共同問題:“我們是如何抵達這里的?”然而,這種重構與同構試圖締結的是什么?傳記家在傳主的世界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傳記之“記”,在同兩次世界大戰和多次社會變革的交互中,再次質問著它自身的可能性及意義。
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解放和性解放之前,整個英國社會充斥著苛刻的道德束縛和偽善的宗教規約,個人生活被撕裂為公共的和私人的,而“在最涉及私人的和最基本的領域,專制主義依然盛行”,私人生活尤其遭到社會的壓制和抹殺。事實證明,“假如人們屈服于權威的聲音,屈服于盲目沖動的宗教或者民族主義,或者性別優越性,那么導致的結果只能是仇恨,而不是愛。比如說,基督教徒之間的恨、民族國家之間的恨,盲目的仇恨煽動起了奧斯卡·王爾德事件,也使蘇格拉底無端喪命,這些形形色色的情緒全都源于非理性的盲目的仇恨”。王爾德曾用他的悲劇說明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偏見和虛偽——這個社會允許同性戀,只要它不張揚;這是個能夠嚴厲地懲罰同性戀以自我證明其本身道德的社會”,而該受到譴責的“正是對我們本有的東西進行譴責的行為;一切排斥,一切遭受到的影響應該受到禁止,因為它剝奪了我們的存在”。若說王爾德對個人存在的公設是“個性自由者”,那么霍爾羅伊德對人類存在的公設就是完滿地實現本性,他所關注的是傳記對人性永不休止的愛和對人性的完滿書寫。他早在斯特拉奇的《維多利亞名人傳》前言中讀到“人,多么重要,怎能僅僅被當作歷史的表征!人具有永恒的價值,不依存于任何忽然而逝的歷史進程”,為此,他試圖擺脫以往受政治和道德欺騙的、患“集體精神崩潰癥”的社會所塑造出的歪曲的邊緣人形象,擺脫他們根深蒂固、有時幾乎是妖術般的公式,揭露歷史及其殘留的假面。至于斯特拉奇本人,克萊夫·貝爾曾說:“對于任何了解他的人來說,愛、欲望以及這兩者的神秘混合物,是存在于他生命中的內在渴望,如果有傳記家忽略了這點,就會讓自己顯得可笑。”可見,不管從傳記家還是傳主的立場出發,揭示“性”都成為一種必要手段。
長期以來,“社會的紋理不但界定了人類之間真正的關系與組織形態,也決定了人類關系的一般規范,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峙的預期行為模式”。人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中都有脈絡可循。為了割斷社會強行編制的紋理,在《維多利亞名人傳》中,斯特拉奇用他尖銳的諷刺同他書寫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并且不時透露、挖掘這種距離,使傳主和讀者遠離那張由維多利亞社會的“良好意愿”編織成的神圣光輝的網,通過“俯視”傳主以還原其真實存在。而在《斯特拉奇傳》中,霍爾羅伊德則用“完全超然的完全同情”的筆法無限接近傳主——以至于他“感染”了斯特拉奇生命中黑暗時期的某些“精神疾病”,在這種近乎真實的感受和體驗中轉而引導讀者進入道德偽善和文化強權下的英國社會,揭示同性戀群體和“性”主題在傳記、甚至在整個英國歷史中的“無名狀態”。他在有意無意之中介入了社會內部,以反抗社會對人存在本身的剝奪,并在重構人類關系,尤其是性關系的訴求中形成了“一種召喚”,讓邊緣的聲音參與到宏大敘事中。霍爾羅伊德相信傳記的拯救力量,這自然不同于神的拯救,而是一種人在歷史序列中的自救。他認為好的傳記家不會給死者增加新的恐懼,而會在死者被遺忘之前,試圖從死亡本身中取回些東西,給死者一個貢獻生者世界的機會。的確,作為維多利亞時代價值觀和社會規范的產物,直到生命最后,斯特拉奇都沒有勇氣書寫他真實的世界,但幸運的是,霍爾羅伊德“向他的傳主伸出手,邀請他,邀請他,死后再合寫一部作品”,以這種重構和同構的溫和方式,傳記家與傳主一起參與到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其中最大意義在于有形無形之間,推翻了長久以來根深蒂固于社會和歷史當中,經由社會規范、傳統、禁令所傳達、認可、象征的人類倫理關系”。
由此,我們可以說霍爾羅伊德試圖讓重構發生在人類存在本身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中,從休·金斯米爾那里,他學會另一種看世界的目光:世界是由人內在的“意志和想象力”構成的,而非性別、階級、膚色等外在的區分組成。在以“消解中心”作為傳記觀的寫作中,他將游離在“行動和意圖,夢幻和現實”間的精神流浪者或邊緣人拉到幕前,多次將斯特拉奇與王爾德進行對比,重疊兩人的身影,為的不是讓斯特拉奇像E·M·福斯特筆下的莫瑞斯在接受審判時恐懼地申訴“我是奧斯卡·王爾德那種難以啟齒的人”,而是讓其扮演文化反叛者“執行奧斯卡挑戰傳統道德的事業”,并最終實現斯特拉奇的期待和預言——“我相信我們的時代將在百年之后到來,那時,準備行將充分,妥協或將達成,在我們的信件出版之際,每個人最終都會改變他們的信仰。”換個角度看,這意味著,霍爾羅伊德是在代替斯特拉奇等人進行講述,有時甚至把自己的聲音“借給”他們,重構了他們被歷史吞沒而未能出說的話語。當然,這并不是指“客觀傳記的神話”,相反,在傳記家的記憶和想象中,隱藏其中的傳記家呈現為在場的傳主的另一面,使得傳記的意義得以自足,這不僅克服了考證傳記與史實之間的匹配程度帶來的“閉絕性”,讓傳記本身進行浮動的歷史比較,更清晰地顯示出其溝通過去、現在、未來的張力,還由此消解了傳記的部分“彼時感”,而賦予文本一種“此時此地”的現時可感性,甚至是一種屬于全人類的普遍體驗或經驗,讓讀者“合上書后,也可能體驗到屬于他們的情感和思想”。與普魯塔克傳記的“時效性”相比,霍爾羅伊德的傳記顯得更遙遠,又更切近。
總的來說,作為一種“話語”,《斯特拉奇傳》中確實帶有霍爾羅伊德的“自我指涉”成分,但正因如此,讀者才能被“這個無法找到完整、共同的愛,最后卻被愛包圍的奇怪、溫柔、悲傷、文明的人所深深打動”,并思考斯特拉奇們在這個社會中能否幸福的問題。而在多個時代和兩個個體的重構與同構中,歷史的浮動和比較賦予此傳更大的張力,呈現為具有變化意味的“途中的鏡子”。還需看到,霍爾羅伊德為斯特拉奇作傳“不是為了履歷而是為了愛”,一種對人類的“愛”,他從來無意標榜此傳的“同性戀”“性”等主題以吸引讀者,更不贊同單一的閱讀視角。在他看來,“如果正常現象構成人類的前影,那么反常現象正是人類的背影”。借加繆的話說,“倘若反抗者應當同時拒絕對虛無的狂熱與對全體性的同意,藝術家則應該同時擺脫對形式的迷戀與現實的極權的美學”,同性戀者在此傳中只是作為受決定論的意識形態和道德倫理壓迫的少數人的象征,但倘若傳記家繼續對這類群體的完整人性和欲望緘默其口,無疑將會把傳記置于對人類經驗、甚至人類存在本身的不完整的書寫之中。
注釋:
[1]Ira Bruce Nadel,,Macmillan,1984,p.66.
[2][5][7]Nigel Hamil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59,p.252,p.254.
[3]Harold Fromm,,Vol.42,No.2 (Summer,1989),p.203.
[4][18][31][37]Michael Holroyd,.Chatto & Windus,1994,pp.681-682,pp.341-422,p.XII,p.102.
[6][美]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反對闡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7 頁。
[8]轉引自唐岫敏等著:《英國傳記發展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 頁。
[9][英]特里·伊格爾頓著,高曉玲譯:《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前言”第4 頁。
[10]1885年,由英國自由黨議員、同性戀反對者亨利·拉布切爾(Henry Labouchère)提出,在下議院的深夜辯論中通過,當時只有少數議員出席,該刑法首次提出同性戀應被定為刑事犯罪,其后的奧斯卡·王爾德和艾倫·圖靈等人由此被定罪。
[11]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3 頁。
[12]1957年,約翰·弗雷德里克·沃爾分登(John Frederick Wolfenden)組織的委員會發布《同性戀犯罪與賣淫問題調查委員會報告》(),提議保護同志的私人權利,同性戀私人行為應被視為無罪,直到1967年,該報告借由《性犯罪法》()獲得通過才正式成為法案。
[13][16]Michael Holroyd,,Chatto & Windus,1994,p.XXII,p.XXIII.
[14][19][38],p.XIX,p.10,p.92.
[15][美]詹明信著,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27 頁。
[17][法]米歇爾·福柯著,佘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 頁。
[20][法]茨維坦·托多羅夫著,馬利紅譯:《啟蒙的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1 頁。
[21][24][33][36]Michael Holroyd,,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9,p.118,p.264,p.298,p.96.
[22]Michael Holroyd,,Vol.22,No.1 (Winter 1999),p.33.
[23][法]茨維坦·托多羅夫著,孫偉紅譯:《脆弱的幸福:關于盧梭的隨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3 頁。
[25][英]A.S.拜厄特著,黃少婷譯:《論歷史與故事》,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3 頁。
[26][英]特里·伊格爾頓著,馬海良譯:《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27][英]約翰·福爾斯著,陳安全譯:《法國中尉的女人》,百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 頁。
[28][英]昆汀·貝爾著,季進譯:《隱秘的火焰: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 頁。
[29][法]茨維坦·托多羅夫著,朱靜譯:《走向絕對:王爾德、里爾克、茨維塔耶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2 頁。
[30][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方曉光譯:《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 頁。
[32][35][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13 頁,第412 頁。
[34]Michael Holroyd,,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02,p.19.
[39]Michael Holroyd,,Chatto & Windus,1996,p.29.
[40]HarperCollins,1993,p.341.
[41]借鑒自莫里斯·迪克斯坦的同名專著《途中的鏡子:文學與現實世界》(劉玉宇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迪克斯坦認為,文學并非機械地反映現實世界,而呈現為反映、折射和分解世界的不斷變化的三棱鏡,以“巧妙的方式解決了客觀真理和多重視角之間的哲學矛盾”。本文借用這一說法,試圖說明生命寫作與歷史之間、傳記家與傳主之間的復雜關系:歷史的分期和命名亦不代表多段歷史間的陌異性,生命寫作不意味著既往歷史或傳主生活的閉絕性,生命書寫往往能夠引起不同時空、不同主體間的共鳴。
[42][英]塔姆辛·斯巴格著,趙玉蘭譯:《福柯和酷兒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 頁。
[43][法]阿爾貝·加繆著,呂永真譯:《反抗者》,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