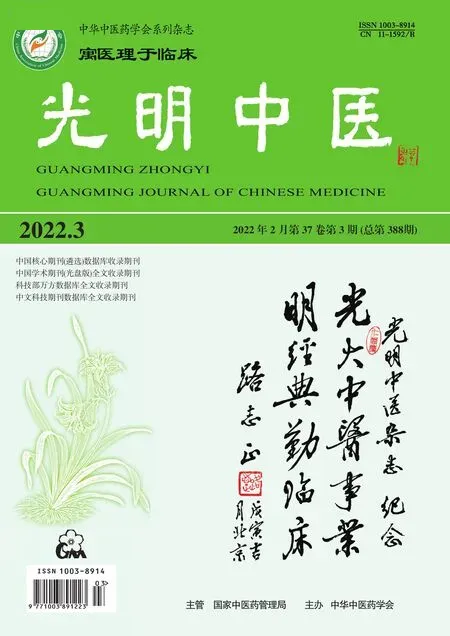柴胡理中湯結合針刺治療卒中后心脾兩虛失眠臨床研究*
范麗娜 張鵬鵬 王娟娟 王曉成 張永康
卒中為腦血管疾病的主要臨床類型,以突然發病、迅速出現局限性和彌漫性腦功能缺損為共同臨床特征,具有較高的發病率、致殘率、病死率。卒中后常并發失眠,易被忽視,但失眠會干擾患者的活動以及康復[1],使患者的神經和認知功能恢復進程受阻,引起焦慮、抑郁等情緒,是增加卒中再發的高風險因素之一。據統計,腦出血后失眠率為60.8%,腦梗死后失眠率為57.1%[2]。目前針對卒中后失眠的藥物以傳統的安眠藥為主,長期使用安眠藥存在藥物依賴、耐藥等缺點[3],成癮依賴性、戒斷性反應、呼吸抑制等不良反應也同樣被視為嚴重的醫療、社會問題,中醫治療失眠具有明顯的特色和優勢,受到普遍關注[4]。
卒中屬于中醫“中風”范疇,目前中醫對卒中后失眠的治療主要為中藥、針灸和推拿。大量數據表明,針刺在治療卒中后失眠療效確切,但是由于引起腦卒中后失眠病機、病程各有不同,單一療法見效慢,難以鞏固療效[5],故針刺聯合多種方法治療,常可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8年1月—2018年12月山西省人民醫院中醫科60例卒中后失眠的住院患者,辨證為心脾兩虛型,按數字表法隨機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0例。對照組1名患者因失訪而脫落,未納入統計。2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均衡可比(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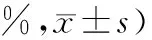
表1 2組失眠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例,
1.2 診斷標準
1.2.1 中醫診斷標準中風、不寐心脾兩虛證的診斷標準參考《中醫內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6,7]中相關內容。
1.2.2 西醫診斷標準卒中按照《腦梗死和腦出血中西醫結合診斷標準(試行)》[8]。失眠參照《中國成人失眠診斷與治療指南》[9]中失眠的診斷標準。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失眠出現在卒中發病后,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及中醫辨證標準;年齡45~70歲,發病時間多于2周小于1年;經頭顱CT或MR影像學證實為卒中;意識清楚,生命體征平穩,自愿加入本試驗,能配合完成各種量表的測評;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入組前停用其他治療失眠類藥物1周以上。排除標準:正在接受其他藥物試驗,或者可能影響本試驗效應的相關治療;合并嚴重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損害或其他各系統嚴重疾病者;既往有失眠、睡眠障礙、抑郁焦慮障礙等精神障礙病史。
1.4 病例脫落標準治療期間患者自覺療效差且要求退出;試驗過程中患者病情惡化或出現暈針、藥物過敏等其他身體狀況不適宜繼續試驗;擅自更改治療方案。
1.5 方法
1.5.1 治療方法2組患者均予卒中的二級預防,藥物治療包括調控血壓、血糖、血脂、穩斑在內的基礎病,營養腦神經,肢體功能康復訓練,防治并發癥及營養支持等對癥治療。治療組與對照組2組均進行針刺治療。針刺治療選穴依據《針灸學》[10],取印堂、四神聰、安眠、神門、照海、申脈、心俞、脾俞。神門、印堂、四神聰用平補平瀉法,照海用補法、申脈用瀉法。針具選用0.35 mm×40 mm漢醫牌一次性使用無菌針灸針(生產企業:長春愛康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生產許可證編號:吉食藥監械生產許20150075號)。常規消毒后用毫針進針,得氣后留針30 min,期間15 min行針一次。每天1次,每周針刺6 d,停刺1 d,1周為一個療程,共治療4個療程。治療組在針刺的基礎上加用柴胡理中湯口服治療。處方:柴胡6 g,黃芩6 g,姜半夏9 g,黨參9 g,炒白術12 g,茯苓15 g,片姜黃6 g,炙甘草6 g。水煎服,每2 d一劑,服用4周。由山西省人民醫院藥劑科中藥房制備。
1.5.2 觀察指標中醫證候積分量表: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1]用中醫證候評分標準評價治療前后的不易入睡、多夢易醒、睡眠時間、心悸、健忘、神疲體倦、頭暈目眩、腹脹食少、面色少華、總分和舌相、脈象情況,得分越多則失眠越嚴重。睡眠質量改變:按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從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日間功能障礙及總分進行評分,得分越高,說明睡眠質量越差。睡眠狀況自評量表評分(SRSS):該量表主要用于評定患者的睡眠情況,該表由10個項目組成,總分為10~50分,評分愈高,說明睡眠問題愈嚴重。
1.5.3 療效評價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1]中失眠的療效標準:臨床痊愈:恢復正常或夜晚睡眠6 h以上且睡眠深沉,醒后精力充沛;顯效:癥狀明顯好轉,時間大于3 h,睡眠深度加深;有效:癥狀減輕,睡眠時間較前增加但小于3 h;無效:無明顯改善,甚至失眠加重。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治療組總有效率為86.67%,對照組總有效率為62.07%,治療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2組失眠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中醫證候積分干預前2組患者在中醫證候積分總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患者在總分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治療組得分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說明柴胡理中湯結合針刺對中醫證候積分有顯著效果。見表3。

表3 2組失眠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例,
2.3 PSQI評分干預前2組患者在PSQI總分上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2組患者在總分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不管治療組還是對照組,柴胡理中湯結合針刺對改善睡眠有顯著作用。見表4。

表4 2組失眠患者治療前后PSQI評分比較 (例,
2.4 SRSS評分干預前2組患者在睡眠狀況自評量表評分上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治療組自評得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干預后睡眠自評得分改善明顯,均顯著低于干預前(P<0.05)。證明柴胡理中湯結合針刺對改善患者睡眠自評方面有效。見表5。

表5 2組失眠患者治療前后SRSS評分比較 (例,
3 討論
中醫認為中風的基本病機為陰陽失調、氣血逆亂,氣血衰少是致病之本,病理性質為本虛標實。人之寤寐由心神所控,氣血為滋養心神的物質基礎。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心主血脈,行血以輸送營養物質,心脾二臟的異常均可導致神失所養而不寐。由此可見,中風和不寐的病機共同涉及心脾,心脾兩虛則氣血不足,氣血虧虛影響疾病的轉歸。研究表明,卒中后3個月左右的患者普遍存在失眠,常持續1個月至3年不等[12]。失眠的治療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治療選穴及其應用已逐漸公認,但針刺具有疼痛感,患者較難持續長時間治療,中醫療法聯合應用可以互補短處、療效疊加,較單一針刺或單純藥物治療的近遠期療效更顯著[13]。歷代不同醫家對不寐有不同的辨證分型,但總體以虛證居多,尤以心脾兩虛型最為多見[14]。心脾兩虛的患者由于心血不足、脾氣虧虛導致失眠[15]。心主血,藏神,血充則氣足,血虛則氣弱;脾主運化,升清,統血,為氣血生化之源;由于脾氣虛弱,生血不足,造成心血虧虛;心血不足,無以化氣,導致脾氣虛弱,二者互為因果。心血不足,血不養神,神不守舍故失眠多夢易醒;心失所養,則心悸;血不能上榮頭目則頭暈目眩;脾氣不足,運化失職,故食少腹脹、神疲體倦、面色少華。
在治療失眠的古今方劑中,古代多以小柴胡湯與清熱藥配伍,現代則多以小柴胡湯與安神藥組方,其中較多使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而忽略小柴胡湯本方治療失眠的功效[16]。小柴胡湯是治療少陽病之主方,《黃帝內經》曰:“少陽為樞”,其中“樞”為運轉、開合、出入之義,“樞”在太陽與陽明之間,亦在三陰與三陽之間,故相對而言“樞”是處于“陽”與“陰”之間的,可司陰陽之運轉,表里之開合,氣機之出入。《類證治裁·不寐》云:“陽氣自動而靜,則寐;陰氣自靜而動,則寤;不寐者,病在陽不交陰也”。失眠患者,氣機升降失常,氣血運行紊亂,陽不交陰,邪于陰陽之間,樞失其職。
小柴胡湯通過后世的臨床驗證總結,和解少陽的功效也進一步具體化。柴胡理中湯是門九章教授經過多年臨床實踐的經驗總結,與小柴胡湯一脈相承的關系,由小柴胡湯化裁而來,立足于“顧護胃氣”的思想,胃氣是指“脾胃為后天之本”的正氣,包括脾胃的消化功能。故于小柴胡湯中加入白術、茯苓、片姜黃三味藥物,兼顧心脾二臟,增加健脾寧心安神之效,攻守兼備,既可提高患者代謝能力來祛邪,又可以提高患者吸收能力來補益。同時,通過扶助胃氣,調整患者自身功能,使機體恢復正常的功能狀態,達到治愈疾病的目的[17]。本研究結果顯示,門九章教授的柴胡理中湯與針刺結合能更好地改善卒中后失眠癥狀,療效優于單純針刺治療,治療組患者在改善中醫證候積分總分、PSQI及SRSS評分方面優于對照組,在健忘、頭暈目眩這2個中醫維度上2組間差異不大,還需進一步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