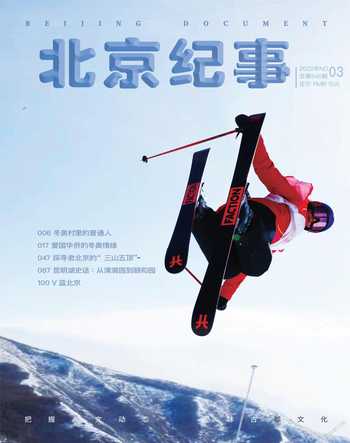文祖倉圣藏悠巷相伴小院尋高人

老北京人或許還有人知道,倉頡廟中住著一位“半仙兒”,之所以稱其“仙”,與迷信絲毫扯不上半點關系,或許是因為他的行動做派、或許是因為他的醫術了得,或許是因為他性格中的怪癖與不羈,又有著那么點子古道熱腸與閑云野鶴般的灑脫,正應了它的大號——閑齋。
無職業、無收入、無家庭,可小日子過得舒適安逸。三教九流之人皆樂與之交,但有人送錢給他,準碰一鼻子灰。貧者前來求醫問藥,往往舍藥免費,藥到病除療效驚人。所用之藥全由其本人配制,方子自然保密,詢問者必定也會迎來一鼻子灰。
民國初年,京兆尹張廣建的長子患病甚篤,慕名“王半仙”醫術高明,恭請其診治,隨后藥到病除。張廣建請朋友送上800元禮金,后被“王半仙”嚴詞拒絕。受托之友道:“這些錢不是給先生的謝禮,是想借先生之名做一些善事,施藥,解寒士之病困……”王厲聲曰:“搜刮之財來路不正!寒士骨耿!不用說施舍藥品,連我的方子也不用了。”說罷,指著屋門說:“請你由此出去復命,衙內的病是不該死,該死的病也治不活,以后再害病,就是該死,不要再來找我!”
民國元年(1912年)一個誓士的月薪四塊大洋,800元算得上是天價了,想想可以抵得上一處中檔四合院。袁世凱為了拉攏議員選他為正式大總統,開出的價碼也是800大洋(月薪),當時人謂議員為“800羅漢”,可想而知京兆尹張廣建的錢財來路。
“王半仙”看病不收錢,又無經濟來源,坊間好事者風傳他能“驅神役鬼”“點石成金”,所以根本用不著錢。又有人說他是江湖奇人、飛行大俠,劫富濟貧。傳說必定是傳說,這些特異功能定不屬實,但這“半仙”之名卻不脛而走,其實這位“半仙”的來歷甚明,是一個以鏢師身份進入北京的“奇人”,功夫確實了得。
辛亥革命爆發后,新疆巡撫袁大化鑒于自己無力掌控西陲政局,遂讓位于按察使楊增新,取道星星峽東歸。行至甘肅境內,遇歹徒攔截,危難之際,突然從莊稼地里躥出一個壯漢,揮舞著鋤頭將歹徒打散。袁大化懇謝搭救之恩,壯士答之曰:“不足道也。”并對袁說:“你在新疆執大吏數年,官聲尚佳,今見你的行囊,所聞不虛,現在兵荒馬亂,我保你平安進京。不過一路之上,曉行夜宿,你得聽我的安排,我也不和你同行,今晚你趕到某地住宿,我在那兒等你。”言罷,飄然逸去。
袁大化趕到指定地點,“不足道也”正在等候,連忙問道:“承蒙壯士厚愛,與我一同進京,總得留個姓名以便稱呼才好。”“不足道也”笑而答道:“王閑齋。”并對袁大化說:“明日啟程,途經某地,到某地住宿。”說罷,又飄然逸去。

路途之上,袁大化發現王閑齋不但武功超群,而且滿腹經綸、飽讀詩書。對沿途山川、河流、關塞、風土、民情了如指掌。對歷史、人文、典籍更是知之甚明,遂以先生稱之。袁大化一路之上按照王閑齋的安排,果然平安到達北京。
袁大化到京后任將軍府將軍,托舊友把王閑齋安排在陸軍部任主事,以施文武全才。王堅決不就職,便是自己不當官,找個謀生的小差事尚可。于是在陸軍部軍需司所屬的清河織呢廠當了一名辦事員,但不久便去職,在倉頡廟里過起了“半仙”的生活。醫道、書法、刻印俱佳,在京城之中頗有名氣,交往甚廣。清末翰林周介仁是位學貫中西的大儒,雖不懸壺但醫道精微,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施金墨便出其門下。周與王閑齋甚是投緣,常在一起研討《黃帝內經》。
吳佩孚在20世紀30年代初寓居北京,和王閑齋多有交往,吳標榜平生奉行三不主義,即不簽賣國條約、不借外債、不進租界。和友人唱和中有“百戰愧無國際功”之句,后被日本特務醫生毒死。吳一日驅車倉頡廟,接王閑齋一同游覽頤和園,汽車到達西直門后,王對吳說:“我有些事情要在西直門辦一下,你先走,過會兒樂壽堂前見。”說罷下車而去。吳到達頤和園后,見王閑齋早已立于樂壽堂前,吳與隨行人員均大吃一驚。當初袁大化進京乘坐的是騾車,王閑齋是飛毛腿先行到達,吳佩孚坐的是汽車,王仍舊能先行到達,當然是“巧”安排。此舉傳遍北平,好事者皆曰:王半仙是神行太保,發功后離地而行。更有甚者謂之“地仙”,系得道之人。
七七事變爆發后,7月27日凌晨,二十九軍部留守人員奉命由中南海居仁堂向西苑轉移。參議方仲純和秘書處周處長所乘之車未到西直門,即得報告:“西直門已換崗,由警察把守,不放軍部留守人員出城。”副參謀長張克俠命全體人員立即解散,各自尋找暫安之處,待機出城向保定方向集合。
方仲純未敢回家,乘著夜色來到西四附近的好友陳貫生家中。陳宅系三進四合院,尚有一個“小天地”。方和家人聯系后,得知寓所正被日軍查抄,私產被封,自己也成了“通緝犯”,覺得留在城中絕非長計,想取道天津租界,乘外輪南下。陳認為不可:“北平警察已被日軍接收,你的老岳任警察總監多年,警界的人大多認識你。警察在前門火車站設卡,你若乘火車去天津,是自投羅網。閑著沒事,不妨去和王閑齋聊聊,聽聽‘半仙’的高見。”
方仲純對王閑齋早有耳聞,于是和陳貫生步行穿過小巷,來到倉頡廟。時值秋日,王閑齋所住的小院大麗花盛開,居室之中古樸典雅,多寶閣上無金玉之器,均系古陶瓷、青銅、海貝、珊瑚之屬。窗明幾凈,壁上字畫多是石濤、朱耷、板橋手筆。“王半仙”打扮可稱是土氣中的土氣,布鞋、布襪,大五幅的白布褂子,深藍色的緬襠褲,和胡同口賣柿子的小販相仿。但黑鞋、白襪、藍褲、白褂均一塵不染,俗中不俗,浸透了清氣雅氣,使人覺得他決不是賣柿子的。
書案之上墨跡未干,所書系柳詩、柳體、鐵畫銀鉤,詩如其字,字如其人,深得真蘊、真意。互相見禮后,王即轉身離去,陳貫生對方仲純說:“等會兒你就知道,半仙上茶不會錯人。給你上的一定是綠茶……”正說著,王閑齋托著一個硬木方盤走了進來,上有兩蓋碗茶和幾盤佐茶之物。方離座欠身接茶,打開蓋碗后青綠沁人,系安徽名茶六安瓜片。
互相寒暄幾句之后,“王半仙”首先發問:“方先生是軍界中的人,國難當頭,有何打算?”方仲純答曰:“軍人有守土抗戰之責,欲赴南京看黨國有何全局安排……”王臉色一變,曰:“何為黨國,貪污集團耳,我路過南京時,見黑氣沉沉,劫數大了……”言談之中對蔣介石甚為不恥,認為江浙乃偏安之地,抗戰大業當靠河朔子弟、關隴健兒。力勸方仲純勿南下,認為留在北方才會有用武之地。
20世紀50年代初,王閑齋在院子里挑水澆花時突然身亡。各方面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幾封與國內外政要的信。信已封,內容不可知,有云由管片民警收去。
王閑齋藏書頗豐,好友們議定將其居室改為“閑齋圖書館”,造物弄人,這個圖書館終未能問世……
作為方家后人,筆者對這位半仙甚是好奇,曾在西四地區尋找過倉頡廟,但不得。數月前,于友人處得知,寶產胡同3號院系“蒼圣祠”,門側有“不可移動文物”標志。特意找到相關部門尋證,院內曾有慈濟醫院懸壺濟世等字樣,民國步軍統領江朝宗有題詞。正殿前原有鐵鼎,上鑄有“始制文字”“萬代文宗”。殿中原有倉頡像,今皆不存。老住戶向來訪者說:“鐵鼎、倉頡像,還有兩石碑在‘文革’中均埋于院中,現已在上面蓋上了房子。”
老北京人口碑相傳的“倉頡廟““王半仙”就是“蒼圣祠”,也是王閑齋的懸壺之所,這位“半仙”仙逝之后,成為了大雜院。曾幾何時,王閑齋的故事也隨著倉頡廟一同浸沒在這時光的長河之中,想來,他的“仙”完全源自他的“怪”,懷才在身,又不愿與當時的官場同流,藏身鬧事,卻也離不開浮生跌宕,因此只能以怪為名,特立獨行守護本心。
拙文皆系親聞,或許能為這處不可移動文物增添些有趣且生動的記憶。
作為《北京紀事》的編輯以及北京文化創作殿堂的一位小卒,游走胡同尋味光陰記憶成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悠巷深處,偶見一院門旁標注“蒼圣祠”提示,好刨根問底兒、追根溯源的我發了條微信,幸得老作家方彪先生注意,更勾起了先生對祖輩的往事追憶。院子雖小,故事很多,其中溯源更成為了北京人文研究領域的首發,也是刊物與作者在文章以外的交往友誼見證。感恩,為這座城市記憶添磚加瓦的人們。
3697500218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