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機(jī)關(guān)系的主奴原則
——《克拉拉與太陽》的機(jī)器倫理批評
□繆晶晶
【導(dǎo) 讀】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從主奴原則、融合原則和超越原則三個(gè)角度,突破了阿西莫夫“機(jī)器人三原則”的限定,在對人—機(jī)共生狀態(tài)的審視中,獲得了重構(gòu)和反思“人性”本質(zhì)的超越視角,并為科幻小說提供了新的題材和視域。
對機(jī)器智慧生物的關(guān)切是諸多科幻文學(xué)所熱衷的話題。在這些作品中,機(jī)器生命與人類的關(guān)系往往呈現(xiàn)為三種樣態(tài):機(jī)器人服務(wù)于人類而消耗自身,直至生命的終點(diǎn);抑或作為人類的器官與之合為一體;最為可怕的一種主題是,機(jī)器人擁有超越人類的智能,進(jìn)而威脅到后者的生存。這類作品的出現(xiàn)顯然是由于自科幻文學(xué)開端以來,人機(jī)關(guān)系的想象就被阿西莫夫“機(jī)器人三原則”所限定,而人類和想象或現(xiàn)實(shí)中的“智能機(jī)器生命”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被某種人與機(jī)器的“主奴關(guān)系”所規(guī)定,就導(dǎo)致相當(dāng)多的科幻作品在敘述機(jī)器生命時(shí),對主奴關(guān)系論采取或遵從或打破的態(tài)度。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則與上述作品不同。具體而言,石黑一雄致力于超越上述“主奴關(guān)系”的設(shè)定,試圖呈現(xiàn)無論是機(jī)器為人獻(xiàn)身,還是作為人的奴隸,都會讓人與機(jī)器生命的關(guān)系變得更不健康,而機(jī)器人克拉拉高于人類的道德理想和實(shí)踐推翻了“主奴關(guān)系”,最終使阿西莫夫歸于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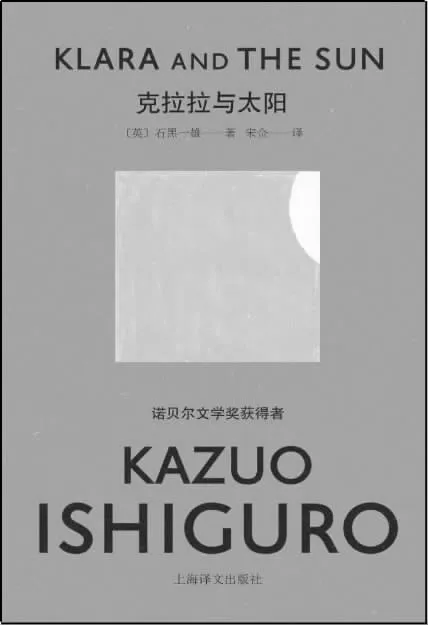
《克拉拉與太陽》是石黑一雄自201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后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繼《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以來另一部披著科幻外衣的人類寓言。故事通過主人公克拉拉的回憶緩慢鋪開。克拉拉是一臺人工智能機(jī)器人,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待售期后,她憑借出色的觀察力和模仿力被母親克麗西買下,用來陪伴身患重病的女兒喬西。隨著喬西的病情每況愈下,克拉拉逐漸發(fā)現(xiàn)克麗西買下自己的真正用途是在喬西不幸去世后“延續(xù)”她的生命,而所謂的“延續(xù)”則是穿上喬西外形的織物并模仿她的言行,讓克麗西覺得喬西依然生活在她身邊。克拉拉認(rèn)為出自內(nèi)心的愛是無法替代的,因此,她拒絕了克麗西的提議并固執(zhí)地向太陽祈禱喬西能夠康復(fù),而當(dāng)喬西奇跡般地痊愈并順利升入大學(xué)后,克拉拉則逐漸淡出他們的生活,直至最后因機(jī)械老化被拋棄在垃圾堆場。
石黑一雄在訪談中提及,他原本想要?jiǎng)?chuàng)作一部兒童故事,但由于女兒的反對,才最終寫成一部給成年人閱讀的作品。[1]在《克拉拉與太陽》中,石黑一雄堅(jiān)持著他一貫的文學(xué)主題,即對人性的叩問和追逐,他將故事場景設(shè)置在科技高度發(fā)達(dá)的未來時(shí)代,規(guī)避了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倫理的局限,使讀者能夠以最極端的方式從人類—機(jī)器的共生狀態(tài)中審視人類本身,進(jìn)而獲得重構(gòu)和反思“人性”本質(zhì)的超越視角。
一、太陽崇拜和自我犧牲:對主奴原則的反諷
AF(Artificial Friend),顧名思義,他們被制造出來的主要目的是“陪伴”,他們把為人類提供“良好的服務(wù)”[2]382作為自己的職責(zé)。人類出于各種緣由——譬如消解孤獨(dú),抑或彰顯身份——挑選心儀的AF,而AF則被剝奪了拒絕的權(quán)利,即便克拉拉出于自主意愿選擇了“自己的孩子”喬西,但也無法改變她在人類社會中所處的從屬地位:梅拉尼婭管家對她“心存芥蒂”[2]61,“除了發(fā)號施令或是斥責(zé)”[2]61以外,從不回應(yīng)克拉拉釋放的友善;喬西未曾阻止孩子們對克拉拉的戲弄,并笑稱想要更換一臺性能更好的B3型號AF;克麗西將她視為“延續(xù)”喬西的載體,忽冷忽熱的態(tài)度令克拉拉無所適從。小說中,人類和AF的關(guān)系與機(jī)器人敘事中的“主奴原則”不謀而合,在程序設(shè)定下,AF被要求無條件服從于人類的指令或承受人類的負(fù)面情緒,直至在機(jī)體老化凋零之際獲得人類對其所謂“成功”的評價(jià),成為典型的服務(wù)于人類而耗竭自身的機(jī)器生命。
作為由太陽能驅(qū)動的機(jī)器人,AF對太陽有著出于本能的依賴,尤其B2型號的AF在太陽能吸收方面存在問題。“某個(gè)AF在離開太陽幾小時(shí)后,還是會漸漸感到無精打采,他會不由得擔(dān)心他的身體有毛病……而一旦這毛病被人知曉,他就永遠(yuǎn)也找不到家了。”[2]8所以“太陽的滋養(yǎng)”于他們而言猶如生命的源泉,顯得格外重要。太陽崇拜是一個(gè)久遠(yuǎn)的習(xí)俗,出現(xiàn)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神話中,弗雷澤在《金枝》里描述了世界各地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太陽崇拜現(xiàn)象,例如,敘利亞和埃及的太陽誕生儀式、歐洲民間的模擬太陽的篝火儀式等。[3]太陽每日升起,照臨大地,綿延不絕,在永不衰竭中為混沌初開的人類帶來光明、溫暖和重生的希望,初始狀態(tài)下的AF在蒙昧中最先感受到的是太陽為機(jī)體注入的力量。石黑一雄在這里做了一個(gè)有趣的設(shè)定,AF并未將制造他們的人類當(dāng)作“造物主”,而是在口耳相傳下,將賜予滋養(yǎng)的太陽作為賦予他們生命的仁慈的神,這為后文克拉拉自我犧牲的崇高性埋下了伏筆。

在孩子們的社交聚會結(jié)束后不久,喬西就病倒了,克拉拉發(fā)現(xiàn),“讓太陽的圖案灑遍她(喬西)全身,她整個(gè)人明顯就有了力氣”[2]109,而記憶中“太陽發(fā)出的某種特殊的滋養(yǎng)”[2]47-48救活了“已經(jīng)死了”的乞丐人和他的狗,這些跡象讓克拉拉產(chǎn)生出一個(gè)模糊卻堅(jiān)定的念頭:太陽能夠?yàn)閱涛鳌八蛠硭厥獾膸椭保?]143。無一例外,太陽每天都會經(jīng)由麥克貝恩先生的谷倉沉入大地,因此,克拉拉認(rèn)為谷倉是最適合向太陽祈禱并獲得神賜奇跡的圣地。朝圣之旅道阻且長,在里克的幫助下,克拉拉通過溝坎縱橫、雜草叢生的小路抵達(dá)谷倉,向太陽許下摧毀庫廷斯機(jī)器從而“終結(jié)它的污染”[2]208的承諾。“太陽是世間所有活力的源泉,因?yàn)樗x予了世界生命,所以作為回報(bào),它也要從世界上獲得生命。”[3]86原始先民認(rèn)為,鮮血中含有生命和靈魂,因此,獻(xiàn)祭鮮血是向太陽換取心中所求的最好的饋贈。來到城里,克拉拉在保羅的協(xié)助下取出頭顱中的P-E-G 9溶液灌入庫廷斯機(jī)器中,破壞了它的發(fā)電單元,迫使它停止向外排放污染。對AF而言,P-E-G 9溶液如同維持人類生命的血液一般,支撐他們認(rèn)知功能正常運(yùn)行,取出P-E-G 9溶液無異于獻(xiàn)祭“鮮血”,最終克拉拉以機(jī)體受到損害為代價(jià),完成了與太陽的“交易”。
機(jī)器人作為科技理性高度發(fā)達(dá)階段的衍生物,理應(yīng)在程序和邏輯的支配下做出最有利于人類或自身的選擇,然而在克麗西、保羅、卡帕爾迪先生討論如何用圖表和數(shù)據(jù)更精確地“復(fù)制”喬西的時(shí)候,克拉拉更愿意相信憑借太陽的力量能夠“治愈”喬西——即使她的信仰被人類稱為“AF的迷信”[2]365。在這里,石黑一雄設(shè)置了一個(gè)懸念:太陽真的有治愈的力量嗎?喬西恢復(fù)健康究竟是源于太陽的滋養(yǎng),還是意外的好轉(zhuǎn)?無論奇跡發(fā)生的真正原因如何,非人類對自然的信仰超越了人類,其本身就是對人類理性之偉大崇高的反諷。人類從自然中誕生,卻在科技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拋棄了自然,非人類由科技孕育,卻萌生出對自然的親密和崇敬,自然人性與科技理性在此間發(fā)生了顛倒。

在“人性”視域下,石黑一雄無疑對人機(jī)主奴原則所包含的“壓迫—反抗”的緊張局勢持反對態(tài)度。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一書中揭示了主人和奴隸囿于對“死”這個(gè)“絕對主人的恐懼”[4]130而形成的微妙關(guān)系:主人通過強(qiáng)迫奴隸為自己勞動以獲得承認(rèn)和自由,奴隸則在勞動中將主人加諸其上的束縛轉(zhuǎn)化為對自我意義的實(shí)踐,并最終超越和控制主人。克拉拉對待喬西的方式顯然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背道而馳,她拒絕履行“延續(xù)”喬西并換取親情、愛情這一最佳且“符合于主人的意識”[4]130的行動,選擇承擔(dān)獻(xiàn)祭“鮮血”可能導(dǎo)致提前報(bào)廢的風(fēng)險(xiǎn),絕非出于奴隸對主人的被迫服從,而是在戰(zhàn)勝死亡恐懼后的主動犧牲。克拉拉無須他人的認(rèn)可,而是“達(dá)到了以獨(dú)立存在為自己本身的直觀”[4]130,通過向代表自然的太陽祈求力量,又將之毫無保留地貢獻(xiàn)給喬西,跳脫出主奴“生死較量”的循環(huán),獲得了精神的絕對自由和平等。但是克拉拉無意于逆轉(zhuǎn)主奴身份,她選擇繼續(xù)履行AF的使命,作為“為他”的存在而存在,直至最終報(bào)廢,這種異于主奴原則的選擇表征了石黑一雄對“人性”的深入思考。
二、生命—階級區(qū)隔:對融合原則的反諷
《克拉拉與太陽》不是一部“本格”科幻小說,石黑一雄操縱科技元素的根本目的是指向由技術(shù)引發(fā)的社會道德危機(jī),站在未來的時(shí)空為當(dāng)下敲響警鐘。布爾迪厄指出,在一個(gè)給定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人們被二元對立所區(qū)隔,“審美趣味”作為判斷文化習(xí)性的有效手段,成為社會結(jié)構(gòu)在身體上的反映,滲透到人們的實(shí)踐領(lǐng)域中,并為人們確定其自身的社會認(rèn)同和階級邊界。[5]與審美趣味這一后天形成的意識形態(tài)相比,石黑一雄選擇了更加直接且顯著的形而下的手段“科技”,作為這部“偽科幻”小說中的階級區(qū)隔標(biāo)志。
自工業(yè)革命以降,科技逐步被資本裹挾,從最初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代表淪為被資本用來劃分社會階級的武器。小說中,人們生活在科技高度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其典型特征是科技對人類生命的深度融入和改造。喬西和里克之間有“一個(gè)與他們的未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模糊愿景”[2]152,由于二者生命結(jié)構(gòu)不同——喬西是經(jīng)由基因編輯技術(shù)被“提升”過的孩子,而里克不是,因此關(guān)于未來的計(jì)劃,隨著二人的成長逐漸顯露出分歧,直至被心照不宣地廢止。在這個(gè)預(yù)設(shè)的時(shí)代,是否接受提升,成為決定孩子們未來命運(yùn)的分水嶺。
布爾迪厄認(rèn)為,審美趣味能夠生成一種歸屬感,劃分出“我們的”和“他們的”,科技作為進(jìn)步力量的代表,在此間起到的作用更勝一籌。在提升過的孩子們的聚會中,里克顯得格格不入。成年人為了讓孩子“學(xué)會和各式各樣的人和諧相處”[2]85,默許里克參加聚會,但是他們友善的招呼里隱藏著“一種奇怪的謹(jǐn)慎”[2]83。孩子們則將里克視為異類,尷尬地尋找話題,又居高臨下地評價(jià)他“表現(xiàn)得還不錯(cuò)”[2]92。提升作為一種輔助生育的科學(xué)技術(shù),在貌似自然形式的區(qū)隔中創(chuàng)造了作用于社會的排他性階級區(qū)隔,而從中獲得利益進(jìn)而掌握話語權(quán)并躍居上流的階級則將提升視為維護(hù)區(qū)隔的有效手段,二者之間的循環(huán)論證為以提升為代表的科技建構(gòu)了不證自明的正確性與合法性。于是,盡管作為“他們”的里克在無人機(jī)研究和制造方面有著極強(qiáng)的天賦,但由于未經(jīng)提升,所以他無法與“我們”一樣享受到優(yōu)質(zhì)的屏幕家教,也難以進(jìn)入唯一一所愿意接收這類孩子的大學(xué)。形而下的技術(shù)最終侵入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由提升改造的生命本身而非外在附加物,成為階級區(qū)隔的重要標(biāo)志。
20世紀(jì)以來,科幻作品中廣泛出現(xiàn)的“賽博格”形象,蘊(yùn)含了人類試圖借助科技力量獲得超越智力和體力極限的隱喻。小說中所謂的提升,即基因編輯技術(shù),較之賽博格顯然更具倫理挑戰(zhàn),提升使人類在出生前就被劃歸至不同的階級陣營,超前實(shí)現(xiàn)了社會分層和階級固化,與斯蒂芬·霍金“超人種族”的進(jìn)化預(yù)言遙相呼應(yīng)。小說有一個(gè)賭徒式的設(shè)定:提升不能保證孩子的生命安全,它是圍繞未來的一場投資,正如克麗西所言,“你下了小注,所以你贏得的收益也又少又可憐”[2]355。反之則不然。于是,在進(jìn)化論法則和階級區(qū)隔的威脅下,為孩子進(jìn)行提升被認(rèn)為是父母之愛的最佳詮釋方式,因此,即使提升導(dǎo)致薩爾不幸病逝,克麗西依舊選擇讓喬西走上同樣的道路,而海倫所堅(jiān)持不做提升也依然可以擁有遠(yuǎn)大前程的自我欺騙,在殘酷的現(xiàn)實(shí)面前迅速土崩瓦解。
如果說賽博格或經(jīng)提升改造的生命是人類—科技結(jié)合體的卓越代表,那么機(jī)器生命則應(yīng)成為絕對理性時(shí)代的“完人”。然而事實(shí)并非如此,純粹技術(shù)領(lǐng)域同樣充斥著新/舊、先進(jìn)/落后等二元對立:已經(jīng)被售出的AF很少從商店門口走過,因?yàn)樗麄兒ε潞⒆觽兛吹叫滦吞柕腁F后會把他們替換掉;B3型號的AF比之B2“獲得了各式各樣的改進(jìn)提升”[2]45,他們組成一個(gè)獨(dú)立的小團(tuán)體并刻意疏遠(yuǎn)B2。科技發(fā)展的原初目的是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但是在資本的運(yùn)作下,科技成為衡量階級歸屬的標(biāo)尺,并參與到社會關(guān)系的建構(gòu)中,由此其合法性便受到了道德觀念的挑戰(zhàn)和消解,使建立在科技基礎(chǔ)上的人機(jī)融合原則走向無解。
科技從來不是科幻小說的真正主題,石黑一雄坦言:“無論故事本身是否關(guān)于科技,都必須明白,我們現(xiàn)在所擔(dān)心的是急速發(fā)展帶來的巨大變化。”[6]由科技引發(fā)的一系列問題被視為人類社會發(fā)展千百年來的隱喻和縮寫,人工智能的廣泛利用是否將重演大機(jī)器生產(chǎn)時(shí)代的悲劇,資本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擴(kuò)張是否會加速人的異化,社會的飛速發(fā)展是否會引發(fā)劇烈的道德危機(jī),這是作為文學(xué)家的石黑一雄向世界提出的問題。通過《克拉拉與太陽》和《莫失莫忘》這兩部“偽科幻”小說,石黑一雄為科技時(shí)代安排了一個(gè)反烏托邦的設(shè)定,也為社會發(fā)展的未來留下一個(gè)頗具警示意味的開放式結(jié)局。
三、人心不在人上:對超越原則的反諷
在談到創(chuàng)作《克拉拉與太陽》的初衷時(shí),石黑一雄表示他最想寫的命題是:“人類的孤單,人有靈魂嗎?人類與動物、機(jī)器的區(qū)別是什么?愛是什么?愛是毫無邏輯的嗎?”[6]這一系列問題被石黑一雄凝練為小說的主要矛盾:機(jī)器人能否代替人類?
在卡帕爾迪先生看來,人類的內(nèi)核中并不具備“某種獨(dú)一無二、無法轉(zhuǎn)移的東西”[2]264。科學(xué)和數(shù)學(xué)可以將人類肢解為圖表、數(shù)據(jù)、模型等一切可量化的元素,因此,只要克拉拉“再稍許加把勁兒”[2]265,就能夠提高自己與喬西的相似度,最終達(dá)到“完完全全是一樣的”[2]264。從理性角度出發(fā),卡帕爾迪先生的計(jì)劃仿佛無懈可擊,然而克拉拉的模仿建立在對喬西“過去”和“現(xiàn)在”的分析上,一旦后者不幸去世,則前者將陷入無法更新的死循環(huán)中,這與制造人工智能的初衷相悖。
同時(shí),克麗西所謂的“延續(xù)”僅是基于對外貌和言行的模仿,比之克隆,甚至不具有任何生物性傳承,因此,延續(xù)的本質(zhì)是程式化的復(fù)制。本雅明提出,藝術(shù)品的即時(shí)即地性、獨(dú)一無二性以及自問世以來所經(jīng)歷的由歷史和社會變遷賦予的意義構(gòu)成了它的“靈暈”,大量復(fù)制品的生產(chǎn)必將導(dǎo)致原作品的“靈暈”消失。[7]當(dāng)人工智能發(fā)展到更高級階段,使機(jī)器人能夠更逼真地模仿喬西時(shí),真正的喬西的“靈暈”將逐漸消失,延續(xù)則會陷入逼真即失真的困局,成為克麗西自我欺騙的悖論。
保羅將人心的復(fù)雜比喻為“房間套著房間套著房間”[2]276,從文學(xué)意義上對以技術(shù)代替人心的方式提出了質(zhì)疑。最初,克拉拉堅(jiān)持在計(jì)算的邏輯下,人心是可以被窮盡的,但是當(dāng)獻(xiàn)祭未能換來喬西病愈,克拉拉不得不求助于舊世代的迷信“真愛”,作為說服太陽賜予仁慈的唯一理由。由此,克拉拉也轉(zhuǎn)變了作為科技理性衍生物的立場,最終意識到喬西“真有一樣非常特別的東西”[2]385是機(jī)器人無法延續(xù)的,那就是愛著喬西的人內(nèi)心中對她的感情。
在科技時(shí)代,追尋人心無異于固守舊世代的迷信。諷刺的是,作為機(jī)器人的克拉拉,反而撿拾起被人類拋棄的人心,這是一出上演于科技時(shí)代的黑色幽默。然而克拉拉眼中的人心又是否是真正的人心呢?小說中譯本的翻譯者宋僉認(rèn)為:“有一樣人類共有的特質(zhì)卻是克拉拉所缺失的,那便是自私——因?yàn)樗且粋€(gè)完全利他的存在。”[2]392科技中心主義的本質(zhì)是人類主體對機(jī)器人他者的利用,小說諸多細(xì)節(jié)都表明AF雖名為“朋友”,實(shí)則卻是滿足人類欲望予取予求的工具,即使他們有著超越人類智力和體力的優(yōu)越性,也無法避免被淘汰或拋棄的必然命運(yùn)。克拉拉以自我犧牲為代價(jià),源源不斷地向喬西和克麗西輸出愛意,與仁慈的太陽相比,她甚至不需要任何回報(bào),僅是執(zhí)行AF與生俱來的服務(wù)使命,直至生命的盡頭,與人類相比,克拉拉堪稱科技時(shí)代的道德楷模。
在大部分科幻作品中,機(jī)器人的進(jìn)化集中體現(xiàn)在功能性上,而其進(jìn)化是為了滿足人類對利益的追求,當(dāng)人類的攫取超出機(jī)器人的承受能力時(shí),便將引發(fā)后者的激烈反抗,《銀翼殺手》《機(jī)器人啟示錄》等經(jīng)典影視作品充分暴露了人類對可能遭遇的技術(shù)“反噬”的恐懼。《克拉拉與太陽》顯然不屬于上述“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式的作品,AF被設(shè)計(jì)為陪伴兒童的機(jī)器人,其機(jī)體力量必然無法達(dá)到反抗人類的程度,因此,AF的進(jìn)化更多體現(xiàn)在道德性上。在進(jìn)化倫理學(xué)視域下,道德被認(rèn)為是生物體進(jìn)化到人類階段的高級產(chǎn)物,起到約束人類私欲以維護(hù)社會秩序的作用。然而在小說中,不具有生物性的機(jī)器人克拉拉對愛和人心的理解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人類,達(dá)到絕對利他主義的高度,成為石黑一雄對機(jī)器人將威脅到人類生命這一論斷的反諷。
機(jī)器人的道德進(jìn)化并非石黑一雄首創(chuàng),他的突破在于將人—機(jī)關(guān)系置于一對滑稽的相互戲仿中——機(jī)器人模仿人類的外形,卻無法習(xí)得人類的利己本質(zhì);人類掌控機(jī)器人的命運(yùn),卻最終將人心讓渡出去。技術(shù)問題的根源在于人類抑或說人性本身,機(jī)器人的道德進(jìn)化反襯出人類社會的道德缺失,迫使人類不得不正視業(yè)已逼近的精神危機(jī)。“以系統(tǒng)思維來看,人文價(jià)值實(shí)際上是作為系統(tǒng)的工具而存在的。”[8]對人類社會這一具有自我完善和改進(jìn)功能的“自組織”而言,文學(xué)意義上的人心是解決道德缺失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工具。“愛作為一個(gè)武器或者說盾牌,能幫助我們對抗孤獨(dú)和死亡。”[1]石黑一雄無意于用悲劇結(jié)尾掀起整個(gè)故事的高潮,在一如既往的平靜敘事中,他賦予克拉拉微弱而堅(jiān)定的救贖力量,為隨時(shí)可能墮入深淵的人類社會敲響警鐘。
四、以科幻之名:社會關(guān)系的想象式治理
環(huán)境污染、資源短缺、病毒肆虐、物種滅絕,諸如此類由科技催生的問題使“反烏托邦”成為近年來科幻作品的主流話語。《莫失莫忘》于2005年出版后,曾一度引起評論界的熱議,大多數(shù)學(xué)者將其定義為一部具有反烏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說,認(rèn)為這是石黑一雄對由克隆技術(shù)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的思考。2021年,《克拉拉與太陽》的出版將公眾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科技,小說主人公由“類人”轉(zhuǎn)向“非人”,標(biāo)志著作者將生命倫理問題推向了更高的層次。然而細(xì)品之下,石黑一雄的兩部小說實(shí)則并不具備傳統(tǒng)科幻作品的必要元素:克隆人與機(jī)器人的橫空出世脫離了技術(shù)操作的過程性環(huán)節(jié),包括克隆胚胎培育、器官移植配型、機(jī)器人程序編碼、基因編輯技術(shù)等用以保證科幻體系邏輯自洽的重要敘述;同時(shí),小說中克隆人或機(jī)器人與人類始終處于不對等中,前者從未在行動上甚至思想上對后者采取任何反抗措施,這種關(guān)系更接近后殖民語境下的階級、種族書寫。因之,《莫失莫忘》和《克拉拉與太陽》的核心絕非科技,而是石黑一雄借科幻名義對反映至社會集體層面的人性所展開的描述和探討。
《莫失莫忘》通過主人公凱茜的回憶,講述了被人類當(dāng)作器官供體的克隆人毫無自由的悲劇人生。凱茜等人自小一同生活在黑爾舍姆寄宿學(xué)校,在成長過程中,他們逐漸知曉并接受了自己的真實(shí)身份,以及注定要為人類“捐獻(xiàn)”器官直至生命“完結(jié)”的既定命運(yùn)。黑爾舍姆流傳著一則“只要證明二人真心相愛,就能延緩捐獻(xiàn)”的傳言,畢業(yè)多年,當(dāng)凱茜與湯米重逢,并相互確認(rèn)心意后,他們決定向神秘的“夫人”提出延遲捐獻(xiàn)的申請,然而夫人和校長對傳言的斷然否認(rèn)猶如當(dāng)頭一棒,殘忍地打破了二人對未來的憧憬。不久之后,湯米完成了第四次捐獻(xiàn),完結(jié)了自己的生命,凱茜也帶著黑爾舍姆的共同回憶走上了捐獻(xiàn)之路。
兩部“偽科幻”小說都以非自然的人造人為主人公,人造人誕生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的生理或心理需求,因此,他們生來就處在被人類利用和壓迫的位置上。從情節(jié)來看,《莫失莫忘》中“捐獻(xiàn)”的設(shè)定顯然更為尖銳,克隆人擁有除生育能力以外與人類相同的生理結(jié)構(gòu),卻被迫僅作為“供應(yīng)醫(yī)學(xué)所需”[9]294而存在。人類盡量避免想起他們,并說服自己克隆人“算不上真正的人類,因此怎么都沒關(guān)系”[9]295。《克拉拉與太陽》則弱化了這種強(qiáng)烈的對立情緒,機(jī)器人本來就不具有生物性,并且終究會有老化報(bào)廢的一天,因此,人類無須遭受愧疚感的折磨,而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由“更加科學(xué),更有效 率”[9]306的新世界帶來的福祉。然而從反諷意義而言,人性體現(xiàn)在“類人”的克隆人身上可謂正常,體現(xiàn)在“非人”的機(jī)器人身上則必然成為一種反常。由此可見,兩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雖時(shí)隔16年,但石黑一雄并未斂其鋒芒,而是選擇將劇烈的情感震蕩隱藏在越發(fā)平淡的敘事之下,用更加綿長的韻味和更具普世效果的手法,對忠實(shí)于資本的人類中心主義及其漠視人類以外的生命之權(quán)利予以批判。
阿西莫夫的“機(jī)器人三原則”同樣適用于克隆人主題,對此,石黑一雄在最初即采取了超越“主奴關(guān)系”的態(tài)度,并不斷趨向深刻和激進(jìn)。凱茜等克隆人沒有拒絕的權(quán)利,面對命運(yùn),她和湯米的唯一行動是申請延緩捐獻(xiàn),當(dāng)他們被告知從不存在延緩的可能后,只能自欺為人類獻(xiàn)身是自己“分內(nèi)的工作”[9]3,而克拉拉放棄了延續(xù)喬西直至“慢慢凋零”[2]374的平靜生活,主動選擇以自我犧牲換取喬西的健康;接受器官移植的人類尚有一絲羞恥,他們選擇“相信這些器官是憑空出現(xiàn)的,或者最多是在某種真空里種植出來的”[9]295,而基因編輯下的人類則走向了臣服于以科技為表征的階級區(qū)隔的徹底異化;凱茜需要黑爾舍姆的快樂記憶以支撐她在失去露絲和湯米后,能夠有勇氣繼續(xù)完成捐獻(xiàn),而克拉拉的回憶則不斷強(qiáng)化自我犧牲是她所做的最正確的選擇這一信念。從被迫到自愿,從自我麻痹到自我肯定,“類人”的人性超越了人類,“非人”的人性又超越了“類人”;相反,人類卻拋棄了曾經(jīng)引以為傲的崇高人性,不斷滑向更幽暗的深淵。《莫失莫忘》和《克拉拉與太陽》這兩部“偽科幻”小說正是石黑一雄向人性發(fā)出的詰問,也是他為呼喚自由、尊嚴(yán)、希望等一切美德所做出的努力。
石黑一雄曾在多個(gè)場合下表達(dá)過其創(chuàng)作“國際化小說”的理想,他將“國際化”定義為“包含了對世界上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活景象”[10]569-570,這種對普遍人性的關(guān)懷成為貫穿于石黑一雄每一部小說的鮮明特征。被評論界稱為“戰(zhàn)后三部曲”的《遠(yuǎn)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和《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均描繪了戰(zhàn)爭對普通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創(chuàng)傷,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人生中某些重要時(shí)刻之意義和個(gè)人選擇之結(jié)果的反思;《無可慰藉》(The Unconsoled)通過模糊的時(shí)空,最大限度上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在庸碌生活中面臨的普遍焦慮和困境;《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打破民族、國家和身份認(rèn)同之間的界限,揭示出小人物懷揣拯救世界的宏大理想,卻被迫于時(shí)代巨浪中飄搖沉浮的悲劇命運(yùn);《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借不列顛史詩探討了個(gè)人在民族和社會層面的記憶與忘卻。雖然故事題材、人物經(jīng)歷、敘事手法各有不同,但是石黑一雄希望人們“感覺到他們看見的并非是一個(gè)陌生的世界,而是每個(gè)人所經(jīng)歷的故事”[11]216的寫作理念是始終如一的。
在全球化進(jìn)程愈加迅速的今天,人類個(gè)體面臨的問題亦是世界集體的困惑,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和其對世界的改造使人性中自私陰暗的一面驟然放大,無數(shù)微小的“惡”終將匯聚成龐大的“惡”,成為人類集體的災(zāi)難。于無聲處聽驚雷,在文字中徜徉、濡染,將創(chuàng)造出綿延久遠(yuǎn)的價(jià)值——文學(xué)無法直接介入生活,但是它能夠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發(fā)揮持續(xù)而有力的作用。無論是在基于現(xiàn)實(shí)的題材,還是純粹想象的時(shí)空中,石黑一雄所探討的都是人類如何面對并處理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guān)系等在內(nèi)的倫理問題,將人性的積極面賦予悲傷的結(jié)局,最終為故事留下一絲耀眼的光彩,正預(yù)示著作者對人類未來所懷抱的微小而堅(jiān)定的信心,這是石黑一雄對健康的社會關(guān)系所展開的呼吁和想象式治理,也是他對成為一名“國際主義作家”理想的實(shí)踐。
注釋
[1]趙松.專訪石黑一雄:愛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機(jī)器人的愛卻是個(gè)悲劇[N].新京報(bào),2021-03-31.
[2][英]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M].宋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
[3][英]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金枝[M].趙昍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0.
[4][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
[5]朱國華.純粹美學(xué)的社會條件——《區(qū)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引言[J].民族藝術(shù),2002(03):16-22.
[6]靳錦.專訪石黑一雄:誰生,誰死,誰講述故事?[N].GQ報(bào)道,2021-04-15.
[7][德]瓦爾特·本雅明.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M].王才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8]范勁2018年10月在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參加“首屆比較文學(xué)與跨文化研究國際高峰論壇”時(shí)的發(fā)言。
[9][英]石黑一雄.莫失莫忘[M].張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10]瞿世鏡等.當(dāng)代英國小說[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1998.
[11]Cynthia F.Wong&Grace Crummett.A Conversation about Life and Art with Kazuo Ishiguro[A].In Ed,Brian W.Shaffer&Cynthia F.Wong.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