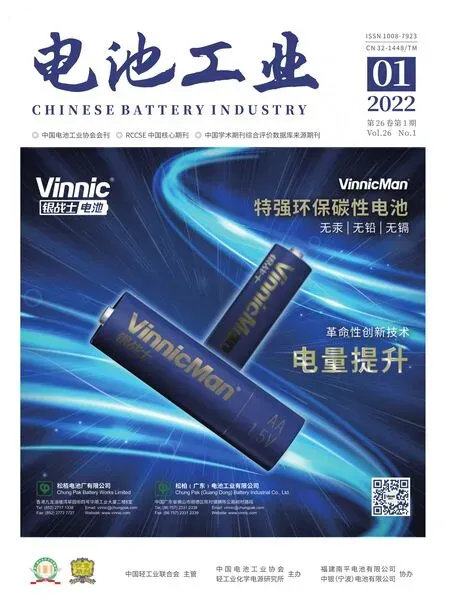電動汽車動力電池保溫性能設計與分析
姚麗君
(遠景睿泰動力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200120)
1 引言
電動汽車的動力電池一般是三元鋰離子電池。通常是由很多個三元鋰離子電芯(下文簡稱電芯)構成動力電池模組,再由多個動力電池模組通過不同的串并聯方式構成動力電池包。溫度是影響動力電池性能的關鍵因素之一,動力電池的最佳工作范圍,一般認為是15~40 ℃,當超出此溫度時,動力電池的性能會受到影響[1]。另外,動力電池包內各電芯的溫度一致性過低,也會影響動力電池的性能[2-4]。
例如,對于同一電芯,監測其在不同環溫度下容量從SOC 100%衰減至80%,當其處于環境溫度55 ℃時,衰減速率是環境溫度25 ℃的23倍;針對另一款電芯,當電芯剩余容量均為90%時,處于環境溫度35 ℃環境中輸出的可用容量僅為環境溫度為25 ℃時的一半[5-6]。
動力電池包根本上而言是由幾十個,甚至幾百個電芯通過不同的串并聯方式構成。每一個電芯的單體性能都影響著動力電池包的性能,且最差的電芯性能最終決定著動力電池包的性能,這就是著名的“木桶效應”[6]。因此,給動力電池配置額外的保溫隔熱系統,對其進行保溫或者隔熱,是提高續航里程、保護電池壽命的好方法,也為電動汽車在寒冷環境中的使用及普及,提供了解決措施。
首先利用計算流體力學原理[7],針對某液冷方式的動力電池包進行溫度場進行仿真分析;其次設計鋰電池組的保溫系統[8-10],并對其進行仿真分析,仿真結果顯示:增加保溫系統后,低溫環境下,電池溫升快,降溫慢;高溫環境下,電池溫升慢,降溫快;且能夠平衡電池包溫度場均勻性,提高電芯溫升一致性,為動力電池熱管理的設計提供依據,降低動力電池開發成本。
2 動力電池單體熱分析2.1 模型基本假設
電芯是由內部電解質、正負極片、隔膜等多種部件構成,各部件又是由不同的材料構成,這就形成了電芯材料多樣化,且不同的工況條件下電芯及其所處的周邊環境換熱條件也是多樣復雜的,所以為了方便對動力電池包進行熱仿真模擬,對其內部的電芯仿真模型做出一些假設和簡化[11],具體如下:
(1)假設電芯為規則長方體幾何模型;
(2)假設電芯為均勻實體,忽略內部物質之間的換熱;
(3)假設電芯的產熱為均勻分布的穩定值;
(4)假設電芯內部所有材料的熱物性參數相應溫度下的恒定值;
(5)假設電芯正常工作溫度范圍內,不考慮電芯的熱輻射。
2.2 鋰電池產熱模型
采用Bernardi生熱速率公式來推算電池的發熱功率,Bernardi生熱速率的理論公式[12],如公式(1)所示:
Φ=-ItdE/dT+I(E-V)
(1)
動力電池的生熱量可以分為化學反應產生的熱量和歐姆內阻產熱或者不可逆反應產生的熱量兩部分,-ItdE/dT是動力電池的可逆反應產熱,I(E-V)表示的是不可逆反應熱,I是動力電池充放電電流,E是鋰動力電池的開路電壓,T是鋰動力電池內部溫度,V是工作電壓。
2.3 鋰電池產熱模型
選取某品牌88 AH電芯為研究對象,電芯原材料是NMC,容量88 AH,導熱系數為27.6 W·m-1·K-1。比熱為1 191.4 J·kg-1·K-1,密度為2 605 kg·m-3。
根據公式(1)推算25 ℃溫度下電芯1 C放電發熱功率為13.13 W。
3 仿真結果與試驗驗證
3.1 仿真結果
由上述88 Ah電芯組成的某電動汽車電池組額定電壓350 V,采用液冷方式冷卻,動力電池包結構示意如圖1所示。

圖1 電池包結構的側視圖Fig.1 Cross section view of battery pack.
仿真模型如圖2所示,主要包括動力電池包上蓋、動力電池模組、導熱材料、動力電池包下箱體(含液冷板)。

圖2 電池包仿真模型Fig.2 Simulation model of battery pack.
冷卻介質為50%乙二醇,設置電芯溫度為25 ℃,冷卻液溫度為25 ℃,冷卻液流量為10 L·min-1,電芯發熱功率為13.13 W,導熱材料導熱系數為1.8 W·m-1·K-1。
仿真時間設定為3 600 s,計算穩定后的溫度云圖如圖3所示。其中,電芯最大溫度為45.3 ℃,最大溫差2.5 ℃。

圖3 1 C放電3 600 S后電芯溫度分布云Fig.3 Diagram of cell temperature after 1 C discharge 3 600 s.
3.2 試驗驗證
室溫25 ℃下,電芯首先進行標準循環充放,靜置后充電到SOC為100%。試驗開始以1 C放電到截止電壓。溫度采樣點為各電芯上部中間,通過預埋熱電偶進行溫度采集。
試驗結果如圖4所示,電芯溫差2 ℃,1 C放電3 600 s后,電芯最大溫度47.5 ℃,電芯最大溫差3.5 ℃。

圖4 電芯溫度Fig.4 Cell temperature.
如圖5所示,試驗溫度值和仿真溫度值趨勢基本一致。表3說明了仿真和試驗結果對比,電芯最大溫度和最大溫差均在5 ℃以內,證明仿真模型可用。

圖5 電芯溫度仿真和試驗對比Fig.5 Simulation result in comparison of test.

表3 仿真和試驗結果對比Table 3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with test result.
4 動力電保溫系統設計
根據上述圖1所示動力電池包結構,由于其箱體橫梁、縱梁和動力電池包下箱體直接連接,為鋁型材結構件,外界環境會通過這些鋁型材結構件構成的傳熱路徑,與動力電池模組進行熱交換,如果沒有熱隔離設計,電池包容易受到外界環境影響,造成電池包低溫漏熱大、高溫溫升快、溫差大。具體見圖6、7所示。

圖6 低溫傳熱路徑示意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low temperature heat transfer path.

圖7 高溫傳熱路徑示意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high temperature heat transfer path.
4.1 保溫隔熱系統
根據上述動力電池包結構及傳熱路徑,開發設計此電池包的保溫隔熱系統。
此保溫隔熱系統主要由導熱系數低于0.04 W·m-1·K-1的材料構成,厚度5 mm,包覆在動力電池包結構外側,如圖8所示。實際應用過程中,動力電池包上蓋是和電動汽車的下車身貼合在一起,所以動力電池上方不需要設計保溫隔熱系統。

圖8 保溫隔熱系統示意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al insulation.
4.2 仿真結果分析
4.2.1 低溫環境預熱
動力電池包在-20 ℃環境下進行加熱性能仿真,電芯初始溫度為-20 ℃,冷卻液溫度設定為30 ℃,冷卻液流量設為15 L·min-1,仿真時間6 h。
由圖9和圖10可知,2 h以內,加裝保溫隔熱系統,可使電芯最小溫度相對提高10 ℃左右。電芯的溫差最大可減小6 ℃。

圖9 電芯最小溫度升溫對比Fig.9 Comparison of minimum temperature rise of cell.

圖10 電芯溫差對比Fig.10 Comparison of cel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4.2.2 極寒環境靜置
將整個動力電池包設置于-30 ℃環境中,電芯溫度開始于25 ℃,對動力電池包進行熱仿真,仿真時間12 h。電池單體最低溫度的變化可以反映電池保溫隔熱系統的性能。由圖11可知,加保溫隔熱系統的電池系統電芯降溫時間會延長,整體較不加保溫系統的電芯降溫時間延長50%左右。

圖11 極寒環境電芯降溫結果Fig.11 Cooling results of cells in cold environment.
4.2.3 高溫環境靜置
仿真采用某高溫地區12 h的環境溫度作為邊界,在此環境溫度下進行高溫靜置仿真。處于高溫環境中的電芯初始溫度28 ℃,仿真時間12 h,模擬電池系統高溫暴曬工況。圖12顯示,電芯最大溫度低于環境溫度,且帶保溫電池系統溫度低于不帶保溫電池系統溫度。

圖12 高溫靜置12 h電芯溫度變化曲線Fig.12 Change curve of cell temperature in 12 h of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4.3 仿真與試驗對比
本文僅對極寒環境靜置進行試驗驗證。首先將帶有保溫隔熱系統的動力電池組置于25 ℃環境中,靜置至所有電芯溫度為25 ℃,且電芯最大溫差不超過2 ℃。然后將整個電池系統置于-30 ℃溫箱中,進行靜置降溫測試。溫度采樣點為各電芯上部中間,通過預埋熱電偶進行溫度采集。

圖13 極寒工況靜置仿真與試驗對比Fig.13 Comparison of static simulation and test results in cold environment.
由于動力電池包置于溫箱中進行靜置,而溫箱是通過風機來進行降溫,會在整個溫箱中產生一定的風速,加速動力電池包的散熱速度。所以仿真結果整體較試驗結果偏高,尤其最初的1 h,試驗中電芯降溫速度較仿真快,靜置初期電芯初始溫度較環境溫度溫差大,溫箱內的風速會加速電芯的降溫速度。
同時可以觀察到靜置前6 h,試驗溫差結果大于仿真結果。這是由于試驗過程中,受限于風機位置,導致電芯溫差偏大。隨著靜置時間的增加,電芯溫度和環境溫度的溫差逐漸減小,動力電池組溫度逐漸接近環境溫度,且溫差逐漸減小,并趨于穩定。在后續的工作中可以結合風機速度,強制對整個仿真模型進行對流換熱系數的修正,提高仿真精度。
5 結論
電池發熱計算值及仿真精度符合工程計算要求。仿真結果證明動力電池組保溫系統能夠有效增加低溫預熱速度,保溫隔熱系統保溫效果較明顯,2 h內可使得電芯溫度相對增加10 ℃,電芯溫差最大減小6 ℃;極寒環境下,保溫隔熱系統能夠延長保溫時長約50%;高溫輻射環境下,保溫隔熱系統能夠有效阻絕高溫環境的地面輻射對電芯的溫度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