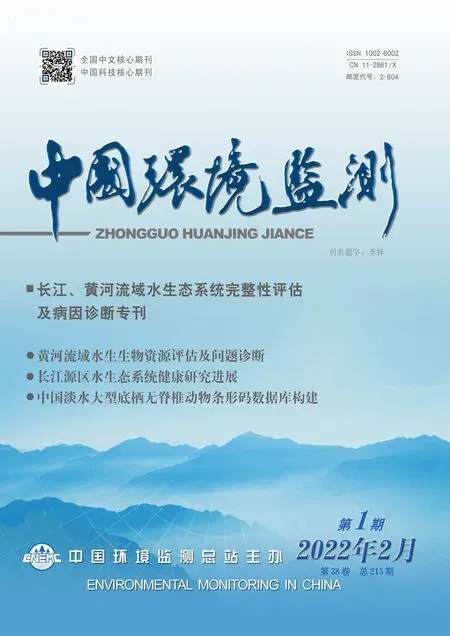長江上游洛磧河段采砂后魚類生境現狀研究
徐觀兵,楊勝發,王 麗,楊 威,胡 江,李文杰
1.重慶交通大學河海學院,重慶 400074
2.國家內河航道整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慶 400074
長江流域年均輸運到河口的泥沙量約為4.3億t,接近全球每年陸源泥沙通量的4.5%。 長江流域的泥沙輸運不僅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塑造了廣闊肥沃的沖積平原和河口三角洲,而且所輸運的部分泥沙作為建筑材料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 長江上游輸沙量占長江流域總輸沙量的80%以上,該區域分布有眾多輸沙模數大于2 000 t/km2的重點產沙區[2-3]。 近幾年來,隨著長江上游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地方建筑行業不斷發展,江砂開采規模日漸增大。 據統計,2007—2016 年,長江上游河道由采砂造成的地形變化量約為0.93 億m3;單坑采砂量達到500 萬m3的采砂坑有4 個,超過100 萬m3的有24 個,約占該河段采砂坑總數量的40%[4]。 長江上游大量集中采砂造成河床地貌大幅度改變,在河床上留下大量采砂坑深潭。 泥沙開挖后,河床高程降低,水深增加,河道流速減小,改變了該河段原有的水流特性[5-6]。 同時,長江上游魚類資源豐富,分布有特有魚類119 種,已建立的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共29 個[7-8]。 目前,河道采砂后的魚類生境現狀尚不明確。 了解長江上游采砂后的魚類棲息地分布現狀及特征,探明采砂后的河道變化對魚類生境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生態修復措施,已成為加強長江上游魚類資源保護的迫切需求。
國內外關于河道采砂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的相關研究,主要針對河道采砂對河流物理生境、河床穩定性以及底棲動物的影響[9-10]。 研究表明,采砂對河流生態環境尤其是魚類生境具有較大影響[11-12]。 比如,河道斷面變寬使得枯水期水位變低或者河床裸露,過水斷面減少不利于水生生物的棲息和遷徙。 河道采砂還會影響到河床和堤岸的穩定,導致河道下切、河床水位降低、洪水漫灘頻率和強度下降、地下水位降低,進而影響到河岸帶植被的生長,對河岸帶動植物生境產生負面影響[13-14];會對底棲動物產生影響[15-18],破壞河床底質穩定性,導致大型底棲動物棲息地減少、豐度和多樣性下降、遷移率上升[19]。 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長江上游采砂前后的河道地形及水流特性變化,探明魚群生境現狀,基于魚類適宜生境條件解析水流特性變化對魚類生境的影響,并結合生境現狀提出生態修復建議,從而為長江上游采砂河段的生境保護與恢復提供科學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洛磧河段位于重慶市渝北區,處于長江上游三峽庫區變動回水區中段,屬大型山區河流。 其河床底部高低起伏較大,深槽與淺灘交替出現[20],如圖1 所示。 受水庫調度影響,該河段水流條件年內分布變化較大:在蓄水期,其水深較大、水流平緩、水位較穩定;而在消落期及汛期,因壩前水位降低,該河段受水庫壅水影響減弱,水位及水流特性與天然狀態基本相似。 洛磧河段屬于長江重慶段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21],該保護區的主要保護對象為四大家魚。 同時,該河段在2008—2017 年存在持續的采砂過程,采砂量超過100 萬m3,最大挖深大于20 m[4]。 受航道修造以及河道采砂等人為因素的過度干擾,該河段水文環境條件發生了較大變化,流速、水深、水體營養元素的組成和濃度等均發生了改變[22]。

圖1 研究區域示意圖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tudy area
1.2 水聲學調查
2019 年1 月及2020 年6 月、12 月,在洛磧河段分別進行了3 次水聲學調查。 將魚探儀(美國BiSonics,DT-X)安裝在水面以下0.5 m 處,聲吶探頭采用200 kHz(角度6.8°)圓形分束換能器,并采用-130 dB 對閾值的部分雜波信號進行濾波,脈沖持續時間和頻率分別設置為0.4 ms 和5 ping/s。 調查前,根據DUCAN 等[23]描述的操作程序,使用21 mm 標準鎢球對回聲探測系統進行聲學校正。 調查船以約2 m/s 的速度航行,按200~400 m 間距平行式走航探測(重點區域間距為200 m,非重點區域為400 m),走航路線見圖2。 為避免夜間航行危險,所有調查都在白天進行。

圖2 走航路線Fig.2 Cruise route
利用Visual Analyzer 4.1 軟件對魚探儀采集到的原始數據進行分析和后處理;利用單回波檢測(SED)對數據進行處理,估計目標強度(TS)。SED 分析的參數設置如下:回波閾值為-65 dB,最小歸一化脈沖長度為0.75,最大歸一化脈沖長度為3。 將10 個以上的魚類個體信號計為魚群,以魚群中心點為魚群位置點。 魚類TS 值和魚類體長(TL)的換算公式[24]如下:

式中:TL 為目標魚類的體長,cm;TS 為魚類的目標強度,dB,閾值取-65 dB。
1.3 魚類棲息地模型
采用二維水動力模型模擬朝天門至涪陵區域的水力條件。 該模型基于求解Saint-Venant 方程,包括連續性方程和動量方程[25]。 在本研究中,計算區域在正交曲線坐標系下共包含3 255×60 個網格點,平均網格間距約為40 m,大小為15~93 m。 根據觀測值與模擬值的相關系數(R2)評價模型性能。R2介于0~1,越接近1 表示模型性能越好[26]。
棲息地適宜性指數(Habitat Suitablity Index,HSI)直接由棲息地模型輸出,表征研究區域對目標物種棲息生境要求的滿足程度。 HSI 取值范圍為0~1,1 表示該區域完全滿足目標魚類對棲息地生境的需求,0 表示不滿足生境需求。 HSI 計算公式如下[27-28]:

式中:HSI 為計算單元的棲息地適宜性指數;Hi為水深適合度指數,m;Vi為流速適合度指數,m/s。
本研究根據魚類在洪水期和蓄水期的不同生境需求,選取水深及流速兩個因子分別計算研究區域HSI 的空間分布。 三峽庫區變動回水區魚群空間分布及影響因素相關研究顯示,該區域魚群在洪水期的主要棲息指標為水深大于20 m 以及流速小于1.2 m/s[26],在蓄水期的主要棲息指標為水深大于20 m 以及流速小于0.6 m/s[29]。 魚類棲息對生境因子的響應曲線如圖3 所示。

圖3 魚類棲息對生境因子的響應曲線Fig.3 Response curves between suitability index and river ecological factors
2 結果分析
2.1 洛磧河段采砂坑形成后的魚類生境分布
2019 年1 月以及2020 年6 月、12 月,分別在洛磧河段進行了3 次水聲學調查,3 次調查能覆蓋年內洪水期(2020 年6 月)及蓄水期(2019 年1月及2020 年12 月)的水流特性變化。 圖4 為3次調查的魚群位置平面分布圖。 水聲學調查的范圍為航道里程597~607 km 處,共10 km 河段,采砂坑位于航道里程601 km 處,且整個采砂坑均在航道左側。 3 次水聲學調查結果顯示,魚群均位于采砂坑范圍內,且集中在采砂壩前段,即最大深潭處。 魚群棲息位置年內變化不明顯,采砂形成的深潭已逐漸成為魚類新的棲息生境,且位置相對固定。

圖4 洛磧河段魚群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sh swarms in Luoqi reach
3 次調查在研究河段均監測到魚群,且均分布在采砂坑處,但魚群規模不同。 2019 年1 月調查到的魚群密度為81.8 ind. /1 000 m3,2020 年6月、12 月分別為170.0、111.1 ind. /1 000 m3,2019年1 月最小,2020 年6 月最大。 魚群密度分布規律整體上呈現為洪水期>蓄水期。 將魚探儀測得的魚類目標強度值代入公式(1)便可得到魚類的體長。 調查結果顯示,2020 年6 月的魚類平均體長最大,達到了17.2 cm;其次為2020 年12 月,體長為15.1 cm;最小體長出現在2019 年1 月,為14.8 cm。 魚群體長分布規律整體上同樣呈現為洪水期>蓄水期。
2.2 采砂前后河床地形變化
對比2008 年、2013 年與2019 年實測地形變化,其中,2008 年為采砂前期,2013 年為采砂中期,2019 年為采砂結束后。 從圖5 可看出,采砂活動對地形的改變明顯。 采砂前,河床高程為150~155 m,縱向斷面高程變化不明顯。 采砂中期,河床最小高程為143 m,已初步形成采砂坑,采砂坑最大深度為7 m。 采砂結束后,河床最低高程小于131 m,形成了一個深度約為20 m 的深潭,采砂區域內水深較采砂前明顯增加。

圖5 2008—2019 年采砂區斷面高程對比Fig.5 Comparison of section elevation in the sand mining area from 2008 to 2019
2.3 采砂前后水流特性變化
寸灘水文站位于洛磧河段上游約50 km 處,其觀測資料全面且精度較高,可靠性、一致性、代表性均較好,能較好地反映該河段的水文特性,因此,采用寸灘站作為該河段水文分析代表站。 通過對比寸灘水文站的計算水位和實測水位,對二維水動力模型進行了率定和驗證。 5 月水位為率定,6 月水位為驗證,結果如圖6 所示。 通過模擬結果可以看出,模擬水位與實測數據的吻合程度較高,模型參數設置合理。

圖6 模型率定與驗證Fig.6 Model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2008 年、2013 年與2019 年采砂區最深處的全年水深變化如圖7 所示。 從圖7 可知,2008年、2013 年與2019 年全年水深變化規律相似,其中,5—10 月水深變化幅度大,10 月后(蓄水期)的水深變化幅度較小。 2008 年為采砂前期,采砂區原有的地形高程較大,整個區域的水深整體較小。 以20 m 水深作為分界線可得,2008 年采砂區最深處的全年水深均小于20 m。 2013 年為采砂中期,已初步形成采砂坑地形,因此,采砂區最深處的水深整體較2008 年要大,主汛期部分時段的水深大于20 m。 2019 年為采砂結束后,采砂坑處形成了一個深度約為20 m 的深潭,采砂區最深處的全年水深均大于20 m。 綜上可知,采砂后的采砂區水深較采砂前明顯增加,采砂活動對水深有明顯影響。

圖7 采砂區最深處水深變化Fig.7 Changes of water depth at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sand mining area
2008 年、2013 年與2019 年采砂區最深處的全年流速變化如圖8 所示。 圖8 顯示,采砂前后,在不同地形高程的作用下,采砂區最深處的平均流速發生了較大改變,且采砂前后的采砂區最深處全年流速變化規律存在顯著差異。 采砂前期及中期的流速分布呈現“n”形,主汛期的流速峰值顯著大于其他時期,其中,采砂前期流速峰值約為2.8 m/s,采砂中期有所降低,為2.2 m/s。 采砂結束后,由于在采砂處形成了深潭,流速分布與采砂前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主汛期的流速峰值大幅度減小,最大值為1.1 m/s,全年流速波動相對平緩。 以1.2 m/s 作為流速分界線可得,在2008年及2013 年,采砂區最深處5—9 月的流速均大于1.2 m/s,其他時段的流速則小于1.2 m/s;在2019 年,采砂區最深處全年流速均小于1.2 m/s。對比采砂區最深處在采砂前、中、后3 個不同時期的流速分布可知,采砂區流速總體隨采砂坑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圖8 采砂區最深處流速變化Fig.8 Changes of water velocity at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sand mining area
2.4 采砂后魚類棲息地適宜度空間分布
采砂前后的洪水期及蓄水期魚類棲息地適宜度空間分布如圖9 所示。 定義HSI 介于0.8~1.0(含上限不含下限,下同)為非常適宜,HSI 介于0.6~0.8 為適宜,HSI 介于0.4~0.6 為較適宜,HSI 介于0.2~0.4 為不適宜,HSI 介于0.0~0.2為非常不適宜。 從HSI 分布可以看出,洪水期主航道區域HSI 普遍偏小,蓄水期主航道區域HSI普遍較大,洪水期HSI 整體遠小于蓄水期。 當流量(Q)為35 000 m3/s 時,研究河段主流帶大部分區域的HSI 均小于0.2,非常不適宜魚類棲息。當Q為6 000 m3/s 時,研究河段主要區域的HSI均大于0.8,較洪水期有大幅度提升,非常適宜魚類棲息。 由此可知,在洪水期,采砂前的全河段HSI 均小于0.8,采砂后在深潭處出現了較高的HSI;在蓄水期,采砂前后全河段均存在大面積適宜棲息區域。

圖9 采砂前后的魚類棲息地適宜度空間分布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3 討論
3.1 洛磧河段采砂后魚類生境特征分析
從HSI 以及魚群的空間分布可以看出,整個調查區域的魚群均位于采砂坑深潭河段。 在洪水期以及蓄水期,均在采砂坑深潭監測到魚群,說明采砂坑深潭已逐漸形成可供魚類棲息的新生境。在洪水期,魚群喜愛棲息于深潭,主要原因是洪水期的整體流速較大,主流帶不適宜魚類棲息,采砂坑深潭能提供大水深、低流速的棲息生境,此時深潭中的緩流區成為了魚類的避難所[30-31]。 在蓄水期,由于整體流速較洪水期小,主流帶也可以滿足魚群棲息生境的水力要求,因此,蓄水期的深潭魚群密度小于洪水期。 但在兩個時期均監測到魚群,說明深潭處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棲息生境。 這可能是由于水流作用使得該區域相對于主航道更利于大量浮游動植物沉積,能為深潭魚群提供充足的食物[32]。
3.2 洛磧河段采砂后水流特性對魚類棲息的影響
影響魚群棲息的水流特性因子主要包括水深、流速等[33-34]。 已有研究人員對三峽庫區變動回水區的魚群空間分布及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發現該區域魚群在洪水期的主要棲息指標為水深大于20 m 以及流速小于1.2 m/s[26],在蓄水期的主要棲息指標為水深大于20 m 以及流速小于0.6 m/s[29]。 洛磧河道由于采砂形成了一個深度約為20 m 的采砂坑。 采砂坑形成后,采砂區域水深增加,深潭水深全年均大于20 m。 同時,由于采砂區域附近河道過水面積沒有明顯變化,水深的增加導致采砂區域流速減小。 相關研究已表明,三峽水庫變動回水區魚群的棲息流速小于1.2 m/s,因為過大的流速會使魚類為克服水流阻力而消耗大量能量。 采砂會引發河床的物理變化,從而導致物種豐富度、多樣性和魚類豐度下降[35-36]。 通過改變基質組成,采砂可能會破壞某些魚類的索餌、棲息和產卵場地[37-38]。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河道地形地貌及水文情勢會達到新的平衡,底棲生物逐漸恢復,會形成一個新的生境[39]。 本研究中,采砂后形成的采砂坑深潭生境的流速均小于1.2 m/s 的臨界值。 3 次調查均在采砂坑深潭監測到魚群,表明采砂坑深潭可能正逐漸成為新的魚類棲息生境。
3.3 采砂河段魚類生境修復
在生態修復方面,越來越多的河道管理人員開始意識到淺灘-深潭結構在建立河流生境多樣性方面的重要作用[40]。 然而,關于如何有效進行魚群生境修復,仍缺少理論基礎[41]。 現有研究顯示,在工程區域采用具有透水結構的人工魚礁有利于魚類、底棲動物和浮游動物的棲息和繁殖,可為魚類等水生生物提供索餌、繁殖、越冬和庇護場所[42-43]。 由于采砂坑難以實現自然修復,以往的思路是將航道整治所產生的棄碴回填至深潭處。但采砂深潭可能已形成新的魚類生境,因此,可以進行原地保護或改造,從而實現生境修復。 首先,對于已形成新生境的采砂深潭,保持現有地形地貌及水文情勢,不再回填清礁棄碴。 其次,可在采砂區域拋放人工魚礁,有利于魚類及其他水生生物的棲息。
4 結論
為了掌握長江上游洛磧河段采砂坑對魚類生境的影響及采砂后的魚類棲息地現狀,通過分析采砂前后地形、流速、水深等參數的變化,得到采砂前后水流特性對魚類生境的影響。 同時,采用水聲學探測儀揭示了洛磧河段的魚群時空分布規律及魚類棲息生境特征,旨在為長江上游洛磧河段魚類保護和棲息地修復提供科學依據。研究結果表明,采砂坑深潭能提供大水深、低流速的棲息生境。 3 次水聲學調查均在采砂坑深潭監測到魚群,采砂坑深潭已形成一個新的緩流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