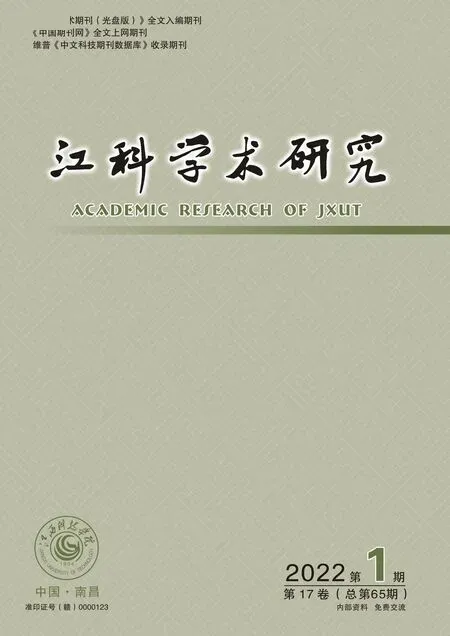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研究
王 慧 楊萬清 高日升 夏天添
一、研究背景
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是新時(shí)代賦予高校的重大使命、立身之本與前進(jìn)動(dòng)力,其不僅為我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同時(shí),也通過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需求和創(chuàng)業(yè)契機(jī),實(shí)現(xiàn)了我國(guó)社會(huì)建設(shè)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快速增長(zhǎng)。長(zhǎng)三角地區(qū)作為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活躍度最高、市場(chǎng)開放程度最高、創(chuàng)新水平最高的重要經(jīng)濟(jì)區(qū),在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與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戰(zhàn)略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目前,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正處于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與技術(shù)變革的攻堅(jiān)時(shí)期,需緊密契合國(guó)家戰(zhàn)略,立足高端、自主與深化協(xié)同的產(chǎn)學(xué)研融合機(jī)制,加速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創(chuàng)新發(fā)展。故此,如何精準(zhǔn)、客觀的評(píng)價(jià)長(zhǎng)三角地區(qū)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對(duì)推動(dòng)長(zhǎng)三角地區(qū)高校科研成果轉(zhuǎn)化效率提升,促進(jìn)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具有關(guān)鍵意義。高校作為我國(guó)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中的核心要件,其既是科技創(chuàng)新與技術(shù)研發(fā)的源頭,也是我國(guó)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主要培養(yǎng)機(jī)構(gòu)[7]。因此,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與質(zhì)量,將直接決定其對(duì)地方社會(huì)服務(wù)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做出的貢獻(xiàn)。
根據(jù)“投入-產(chǎn)出”理論,在“資源投入-成果產(chǎn)出”階段,科技成果僅實(shí)現(xiàn)了基礎(chǔ)性的“從無到有”的基礎(chǔ)轉(zhuǎn)化,如研究人員通過研究發(fā)表的論文、專著等學(xué)術(shù)型成果,該階段的成果轉(zhuǎn)化僅停留在“象牙塔”,而未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生產(chǎn)力轉(zhuǎn)化,即為資源投入方帶來實(shí)際的效益增長(zhǎng)。在對(duì)現(xiàn)有研究展開分析后發(fā)現(xiàn),前人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的評(píng)價(jià)研究上,普遍將學(xué)術(shù)型成果列為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主要考核目標(biāo),而鮮有學(xué)者對(duì)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實(shí)際收益展開細(xì)致的探討。“產(chǎn)出”象征著資源投入后的科技成果,而“轉(zhuǎn)化”則意味著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的具體過程;因此,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的評(píng)價(jià)研究,不僅是為了觀測(cè)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區(qū)域(對(duì)象)的科技成果產(chǎn)出,更是為了揭示其科技成果的轉(zhuǎn)化效率與投資質(zhì)量。
基于此,本研究認(rèn)為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需要在重視學(xué)術(shù)型成果產(chǎn)出的基礎(chǔ)上,強(qiáng)化關(guān)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對(duì)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效益的貢獻(xiàn)。為此,本研究將“投入-產(chǎn)出-轉(zhuǎn)化”,歸納為資源投入、成果產(chǎn)出和轉(zhuǎn)化效率三個(gè)指標(biāo)類型,并以此進(jìn)行DEA分析(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
二、模型與數(shù)據(jù)
(一)研究模型與數(shù)據(jù)來源
在樣本選擇上,本研究以我國(guó)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新工科高校為研究對(duì)象,其原因?yàn)樾鹿た剖俏覈?guó)迎接新一輪科技產(chǎn)業(yè)革命,推動(dòng)我國(guó)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型經(jīng)濟(jì)改革的重要人才供給來源,也是我國(guó)工科教育領(lǐng)域的排頭兵,對(duì)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為此,本研究將利用DEAP 2.1 軟件進(jìn)行DEA分析(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以觀測(cè)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在模型設(shè)定上,主要采用BCC模型,即規(guī)模可變型DEA模型,并將技術(shù)效率拆分為單一技術(shù)效率與規(guī)模效率兩個(gè)維度。同時(shí),本研究參考前人的做法,構(gòu)建了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模型與觀測(cè)指標(biāo)(如表1所示);其中,投入類指標(biāo)包含當(dāng)年科研(創(chuàng)新)支出費(fèi)用和當(dāng)年R&D 全時(shí)當(dāng)量人數(shù);產(chǎn)出類指標(biāo)包括學(xué)術(shù)專著數(shù)量與學(xué)術(shù)論文數(shù)量;轉(zhuǎn)化類指標(biāo)包括合同(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數(shù)量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收入。此外,本研究所用之?dāng)?shù)據(jù)均取自于2011-2017年度的《高等學(xué)校科技統(tǒng)計(jì)資料匯編》。

表1 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模型
(二)樣本處理
本研究以江蘇、上海、安徽與浙江地區(qū)的181 所高等院校為樣本,按照“投入-產(chǎn)出”數(shù)據(jù)不為0 原則進(jìn)行樣本篩選,首先,將2011-2017年間未在科技創(chuàng)新、技術(shù)研發(fā)等方面投入資源的9 所樣本院校剔除;其次,剔除資源投入3年后無科技成果產(chǎn)出的103所樣本院校并,在余下樣本中,再行剔除未開展“新工科”建設(shè)的47 所樣本院校。最終,共得到22 所高校的有效樣本。在對(duì)有效樣本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描述性分析后發(fā)現(xiàn)(如表2所示):在研究樣本中,平均年度科研支出費(fèi)用為80610.83 萬元、全職研究人員約1300 余人,說明在已開展或準(zhǔn)備開戰(zhàn)新工科建設(shè)的長(zhǎng)三角地區(qū)高校,普遍重視科技創(chuàng)新,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與財(cái)力(人均研究經(jīng)費(fèi)約60萬元),為科技創(chuàng)新與成果轉(zhuǎn)化奠定了夯實(shí)的基礎(chǔ);從科技成果產(chǎn)出角度來看,年均產(chǎn)出學(xué)術(shù)論文4000余篇、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授權(quán)500余項(xiàng),證明樣本院校亦具備一定的科技創(chuàng)新水平;然而,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指標(biāo)而言,無論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合同的簽訂還是轉(zhuǎn)化收入方面,樣本院校亦存在科技成果“無效(低效)產(chǎn)出”的隱患。

表2 描述性分析結(jié)果
三、實(shí)證分析
在對(duì)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22所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進(jìn)行DEA分析后發(fā)現(xiàn),僅有9所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達(dá)到區(qū)域均值以上水平,其他13所樣本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水平較低,然反觀其科技成果產(chǎn)出,則呈現(xiàn)出“高產(chǎn)出,低轉(zhuǎn)化”的窘境(如表3所示)。

表3 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的DEA分析結(jié)果
(一)科技成果“投入-產(chǎn)出”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分析
根據(jù)表4和表5的結(jié)果可知:2011-2017年度,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平均綜合“投入-產(chǎn)出”績(jī)效為0.630,其中,純技術(shù)效率為0.849,規(guī)模效率為0.739;雖然,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投入-產(chǎn)出”效率在純效率變化指標(biāo)上表現(xiàn)欠佳,但在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規(guī)模效率變化、技術(shù)效率變化方面均表現(xiàn)較好,從資源投入視角而言,資源要素的投入實(shí)質(zhì)上得到了規(guī)模性的科技成果產(chǎn)出,說明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產(chǎn)出效率,仍處于上升的發(fā)展趨勢(shì)。

表4 “投入-產(chǎn)出”績(jī)效DEA-Malmquist分析結(jié)果

表5 2011-2017年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投入-產(chǎn)出”績(jī)效變化
(二)科技成果“產(chǎn)出-轉(zhuǎn)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分析
根據(jù)表6和表7的結(jié)果可知:2011-2017年度,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平均綜合“產(chǎn)出-轉(zhuǎn)化”績(jī)效為0.355,其中,純技術(shù)效率為0.569,規(guī)模效率為0.654;同時(shí),技術(shù)效率變化、純效率變化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均大于1,若僅從科技成果的“產(chǎn)出-轉(zhuǎn)化”結(jié)果來看,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產(chǎn)出的科技成果,亦得到了較好的轉(zhuǎn)化。但從資源回報(bào)角度而言,2011-2017年,全要素效率升降波動(dòng)不穩(wěn)定,樣本院校通過資源投入所產(chǎn)出的科技成果,若無法實(shí)現(xiàn)持續(xù)性的穩(wěn)定轉(zhuǎn)化,其投入亦存在一定的投資風(fēng)險(xiǎn)。

表6 “產(chǎn)出-轉(zhuǎn)化”績(jī)效DEA-Malmquist分析結(jié)果

表7 2011-2017年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產(chǎn)出-轉(zhuǎn)化”績(jī)效變化
(三)科技成果“投入-轉(zhuǎn)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分析
根據(jù)表8和表9的結(jié)果可知:2011-2017年度,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平均綜合“投入-產(chǎn)出-轉(zhuǎn)化”績(jī)效為0.343,其中,純技術(shù)效率為0.416,規(guī)模效率為0.820,相對(duì)降幅較小,且規(guī)模效率有較大增幅;同時(shí),規(guī)模效率變化、純效率變化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均大于1,同比上升趨勢(shì)明顯,亦證實(shí)了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產(chǎn)出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較好,但依舊存在轉(zhuǎn)化效率不穩(wěn)定等問題。

表8 “投入-轉(zhuǎn)化”績(jī)效DEA-Malmquist分析結(jié)果

表9 2011-2017年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投入-轉(zhuǎn)化”績(jī)效變化
四、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機(jī)制與問題分析
新工科高校作為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產(chǎn)業(yè)升級(jí)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重要?jiǎng)恿Γ邪l(fā)技術(shù)與自主創(chuàng)新實(shí)力的持續(xù)提升,亦使其逐步成為我國(guó)科技創(chuàng)新戰(zhàn)略中的關(guān)鍵部分。為加快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長(zhǎng)三角地區(qū)高質(zhì)量發(fā)展,近年來,新工科高校亦在科技創(chuàng)新與技術(shù)研發(f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形成了相應(yīng)的技術(shù)轉(zhuǎn)移體系或機(jī)制,其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宏觀環(huán)境相比建設(shè)初期有了較好的改善,但依舊存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不足的問題。
(一)管理層面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問題分析
首先,新工科高校內(nèi)部的相關(guān)管理機(jī)制與過程設(shè)計(jì)存在不足。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體系是一項(xiàng)繁瑣、耗時(shí),且復(fù)雜的系統(tǒng)性工程,相關(guān)高校的對(duì)應(yīng)管理體制與流程機(jī)制亦存在明顯的不足或主軸缺失,導(dǎo)致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者)頻繁奔波于研發(fā)與行政之間,以使得科技成果難以實(shí)現(xiàn)高效率的轉(zhuǎn)化。同時(shí),以披露機(jī)制來看,目前在我國(guó)各大高校僅少數(shù)院校建立了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公開性制度,多數(shù)院校基于自我利益考量,仍對(duì)此持觀望態(tài)度。其次,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服務(wù)機(jī)制不足。在我國(guó)高校體系中,大學(xué)科技園、規(guī)劃處、科技處等組織之間的作用機(jī)制尚未厘清,更難以形成良性的交互體系,以高效對(duì)接產(chǎn)業(yè)發(fā)展、自主創(chuàng)新、資本投入、政策環(huán)境等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體系中的主要環(huán)節(jié),提升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目前,在長(zhǎng)三角地區(qū)中,各家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機(jī)制亦有所長(zhǎng)短,多數(shù)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亦停留在象征性的事務(wù)流程階段,且多重視資源投入到成果產(chǎn)出之間的管控,而極少涉入科技成果轉(zhuǎn)移、轉(zhuǎn)化階段。其緣由莫過于受限于高校編制約束,且科技成果產(chǎn)出在現(xiàn)行高校評(píng)價(jià)體系中的比重,顯高于成果轉(zhuǎn)化,故而出現(xià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者在職務(wù)晉升、待遇等方面激勵(lì)不足,致使其難以全身心的投入成果轉(zhuǎn)化工作當(dāng)中,阻礙了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增長(zhǎng)。其三,現(xiàn)行高校評(píng)價(jià)體系對(duì)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約束。我國(guó)近代高校評(píng)價(jià)體系(機(jī)制)的重心,多偏向于科技產(chǎn)出成果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與獲獎(jiǎng)級(jí)別,以至于忽視了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所帶來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國(guó)內(nèi)各大級(jí)別的基金項(xiàng)目,在項(xiàng)目結(jié)題(驗(yàn)收)環(huán)節(jié)上,已不同程度的出現(xiàn)“僅認(rèn)數(shù)量,不重質(zhì)量”的扭曲現(xiàn)象,從而導(dǎo)致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實(shí)際績(jī)效偏低。在如此機(jī)制之下,高校在科研工作者的職稱評(píng)定、職務(wù)晉升等方面亦東施效顰,而科研工作者亦將此奉為成功之道,久而久之,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教學(xué)科研工作者必定難以承擔(dān)優(yōu)秀人才培養(yǎng)與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任。
(二)環(huán)境層面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問題分析
十二五以來,我國(guó)針對(duì)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機(jī)制改革,已投入了龐大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并借由高校自主創(chuàng)新成果轉(zhuǎn)化,服務(wù)地方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加快地方產(chǎn)業(yè)升級(jí)。然而事實(shí)上,我國(guó)雖已頒布一系列支持政策,但政策紅利仍有待時(shí)間轉(zhuǎn)化,同時(shí),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作為高復(fù)雜度的系統(tǒng)性工程,人才引進(jìn)、產(chǎn)業(yè)升級(jí)、服務(wù)體系等配套政策,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各省市亦參差不齊,部分地方性政策多以試行方式頒布,其時(shí)效性短,極易出現(xiàn)騙補(bǔ)等消極現(xiàn)象。故如何實(shí)現(xiàn)長(zhǎng)三角地區(qū)創(chuàng)新資源的科學(xué)配置,強(qiáng)化四省市之間的校企資源互補(bǔ)、協(xié)同創(chuàng)新,為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大的價(jià)值,仍有待從政策層面進(jìn)一步研究落實(shí)。此外,出于市場(chǎng)信任機(jī)制考量,企業(yè)普遍認(rèn)為與高校的科技合作亦存在泄密風(fēng)險(xiǎn),同時(shí),少數(shù)企業(yè)出于短期利益考量,極少與高校進(jìn)行新技術(shù)或重大項(xiàng)目的科研合作或協(xié)同創(chuàng)新。
(三)過程層面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問題分析
無論從技術(shù)研發(fā),還是到產(chǎn)出成果的市場(chǎng)性轉(zhuǎn)化,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資源配置平均效率偏下。其中,純技術(shù)效率與規(guī)模效率不穩(wěn)定是造成其科技成果產(chǎn)出與轉(zhuǎn)化績(jī)效反復(fù)的主因,從DEA 分析的結(jié)果可知,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投入產(chǎn)出的平均純技術(shù)效率低于規(guī)模效率,印證了其資源要素配置不均衡,即資源投入可能存在一定的資源未充分利用,甚至浪費(fèi);而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上,平均純技術(shù)效率雖高于規(guī)模效率,代表其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要素配置相對(duì)高于其投入產(chǎn)出階段的資源配置,但其歷年數(shù)據(jù)互有反復(fù),亦凸顯其成果轉(zhuǎn)化要素配置仍存在較大隱患。同時(shí),從各高校科技成果投入轉(zhuǎn)化的規(guī)模效率來看,僅少數(shù)院校呈現(xiàn)出規(guī)模收益遞增狀態(tài),多數(shù)則呈現(xiàn)遞減或不變,由此證實(shí),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新工科高校在科技成果的轉(zhuǎn)化工作上,尚未達(dá)到最高績(jī)效,其資源投入仍存在大幅冗余,且大量資源投入并未帶來規(guī)模性效率提升,這也從側(cè)面印證出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新工科高校過于重視科技成果產(chǎn)出,而漠視其成果轉(zhuǎn)化。
(四)對(duì)象層面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問題分析
根據(jù)DEA 分析的結(jié)果可知,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產(chǎn)出與轉(zhuǎn)化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脫節(jié),其科技成果投入與產(chǎn)出績(jī)效較好,但產(chǎn)出成果轉(zhuǎn)化為實(shí)際商品或市場(chǎng)收益的渠道仍未大通。從表3-9 的結(jié)果不難發(fā)現(xiàn),在參與測(cè)算的新工科高校中,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均遜于其成果產(chǎn)出,由此可知,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雜科技資源投入、成果產(chǎn)出與成果轉(zhuǎn)化的兩個(gè)階段中,并未實(shí)現(xiàn)均衡化的發(fā)展;其中,22 所樣本院校的科技成果產(chǎn)出與轉(zhuǎn)化斷層頻現(xiàn),證實(shí)其科技成果產(chǎn)出與轉(zhuǎn)化之間的不必然性,即樣本院校雖具備較好的自主創(chuàng)新實(shí)力,并能夠形成頗具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或高獲獎(jiǎng)幾率的科技成果,但成果亦有可能停留在理論試驗(yàn)或?qū)嶒?yàn)階段,以使其并不絕對(duì)能夠轉(zhuǎn)化為實(shí)際的商品或市場(chǎng)效益。
五、長(zhǎng)三角地區(qū)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的提升策略
(一)重視成果轉(zhuǎn)化 構(gòu)建成果轉(zhuǎn)化體系
新工科高校因突破原有思維慣性,在科技管理體制建設(shè)方面,建立高效合理的制度體系,以進(jìn)一步推動(dòng)科技管理改革、優(yōu)化成果轉(zhuǎn)化機(jī)制、構(gòu)建專業(yè)化的成果轉(zhuǎn)化人才隊(duì)伍、完善成果轉(zhuǎn)化服務(wù)機(jī)制,通過充分發(fā)揮制度性手段機(jī)制,擴(kuò)大自主創(chuàng)新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最大動(dòng)能。為此,新工科高校首先必須重視科技創(chuàng)新規(guī)則,適時(shí)完善其內(nèi)部相應(yīng)管理政策、機(jī)制及組織,打破在資金、項(xiàng)目與鑒定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認(rèn)為約束,解放研究人員的思想枷鎖;同時(shí),嘗試采用項(xiàng)目資金管理“承包制”、項(xiàng)目“云管理”等方式,提升項(xiàng)目研發(fā)與管理效率,以為科技創(chuàng)新提供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其次,優(yōu)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機(jī)制,探索以自主創(chuàng)新與成果轉(zhuǎn)化為導(dǎo)向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機(jī)制,對(duì)不同方向、不同研究類型、不同工種的項(xiàng)目及人員設(shè)置對(duì)應(yīng)的績(jī)效考評(píng)機(jī)制,充分發(fā)揮項(xiàng)目和人員異質(zhì)性的優(yōu)勢(shì),提升科技創(chuàng)新與成果轉(zhuǎn)化效率。其三,建設(sh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轉(zhuǎn)移)人才隊(duì)伍,在科技管理組織中,設(shè)置專業(yè)的成果轉(zhuǎn)化或技術(shù)轉(zhuǎn)移崗位,并通過獎(jiǎng)金、職務(wù)晉升等手段,吸引、保留與培養(yǎng)服務(wù)于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專業(yè)人員;同時(shí),對(duì)內(nèi)打破體制化限制,成立校領(lǐng)導(dǎo)為核心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機(jī)構(gòu),全程參與本校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shè)、轉(zhuǎn)化機(jī)制設(shè)計(jì)等環(huán)節(jié),實(shí)施一體化、透明化、網(wǎng)絡(luò)化的統(tǒng)籌管理,貫通高校科技成果到市場(chǎng)(產(chǎn)業(yè))的快車道,引導(dǎo)外部?jī)?yōu)勢(shì)企業(yè)(組織)展開協(xié)同創(chuàng)新合作,強(qiáng)化高校自主創(chuàng)新與成果轉(zhuǎn)化。其四,在優(yōu)勢(shì)學(xué)科建設(shè)上,新工科高校應(yīng)積極推動(dòng)以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為導(dǎo)向的優(yōu)勢(shì)學(xué)科建設(shè),并透過優(yōu)勢(shì)學(xué)科建設(shè)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循環(huán)機(jī)制,逐步強(qiáng)化自身科創(chuàng)實(shí)力。為此,新工科高校需要著重推動(dòng)其本校優(yōu)勢(shì)學(xué)科領(lǐng)域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將轉(zhuǎn)化作為其優(yōu)勢(shì)學(xué)科建設(shè)的核心動(dòng)力,并逐步構(gòu)建創(chuàng)意檢驗(yàn)中心、技術(shù)轉(zhuǎn)化平臺(tái)等轉(zhuǎn)化層組織,加強(qiáng)加快新工科高校的優(yōu)勢(shì)學(xué)科建設(shè),從而在降低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風(fēng)險(xiǎn)的同時(shí),促進(jìn)高校自身的人才培養(yǎng)機(jī)制與科創(chuàng)實(shí)力。
(二)發(fā)揮政策優(yōu)勢(shì) 提升成果轉(zhuǎn)化效率
為規(guī)范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體系,地方政府的相關(guān)部門亦應(yīng)從法規(guī)政策層面,進(jìn)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政策導(dǎo)向與管理機(jī)制,強(qiáng)化對(duì)新工科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的指導(dǎo)與協(xié)調(diào),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績(jī)效納入其高校評(píng)價(jià)考核的核心指標(biāo),明確高校主體責(zé)任,優(yōu)化高校科創(chuàng)意識(shí);逐步為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者設(shè)立對(duì)應(yīng)的職務(wù)晉升制度,并探索以誠(chéng)信為基礎(chǔ)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介機(jī)制,深入開發(fā)高校自主創(chuàng)新的市場(chǎng)潛力。同時(shí),在政策資金投入方面,高校科技創(chuàng)新從“研究開發(fā)-成果產(chǎn)出-市場(chǎng)轉(zhuǎn)化”,各環(huán)節(jié)均需投入資金,且就目前高校自主創(chuàng)新而言,多仰賴政府相關(guān)政策資金的投入;故建議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的相關(guān)政府應(yīng)建立科學(xué)的科技財(cái)政投入機(jī)制,探索以財(cái)政補(bǔ)貼抵扣、稅務(wù)減免等為主的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資機(jī)制,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資本在高校科創(chuàng)領(lǐng)域的充分參與,加速新工科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
(三)促進(jìn)協(xié)同創(chuàng)新 謀求成果高效轉(zhuǎn)化
受誠(chéng)信風(fēng)險(xiǎn)等因素影響,我國(guó)高校尤其是以長(zhǎng)三角地區(qū)為代表的新工科高校,在自主創(chuàng)新及成果轉(zhuǎn)化上,多處于“自娛自樂”的扭曲境地,而企業(yè)的“后知后覺”現(xiàn)狀,亦變相印證了我國(guó)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無奈之處。企業(yè)作為實(shí)踐科技成果價(jià)值的最終環(huán)節(jié),其主體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發(fā)揮,亦代表著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實(shí)效。為此,企業(yè)應(yīng)充分發(fā)揮其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主體作用,以促進(jìn)自身科創(chuàng)實(shí)力為導(dǎo)向,積極探索與高校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機(jī)制;在明確自身需求與市場(chǎng)需求的前提下,為高校明確科創(chuàng)方向,并與高校緊密圍繞在以市場(chǎng)轉(zhuǎn)化為目標(biāo)的科創(chuàng)工作中,實(shí)現(xiàn)科技成果“產(chǎn)出-轉(zhuǎn)化”的無縫銜接,以將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最后一公里,塑造為“優(yōu)勢(shì)的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