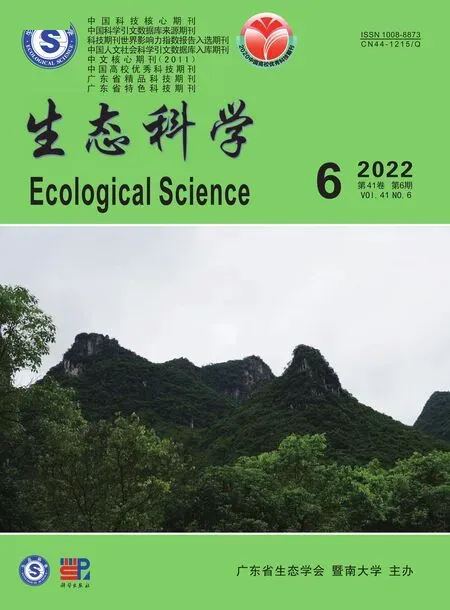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進展
李夢蝶, 王立龍, 晉秀龍
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進展
李夢蝶1, 王立龍2,*, 晉秀龍3,*
1. 安徽師范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 安徽蕪湖 241000 2. 安徽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安徽蕪湖 241000 3. 滁州學院, 安徽滁州 239000
隨著旅游業的發展, 保護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顯著。為了應對這些問題, 學者們開始逐漸將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協調旅游與生態因子之間的關系上, 就旅游對植物多樣性方面的影響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總結了國內外有關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的研究進展, 歸納了旅游過程中植物多樣性受到的影響因素, 并且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管理對策。最后提出, 生態旅游業作為一個新興的蓬勃發展行業, 已經引起政府和學術界高度關注, 但其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 仍然面臨著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 而有關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則可能成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重要突破口。
旅游干擾;植物多樣性;生態旅游
0 前言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 公眾對于旅游業的需求日趨旺盛, 旅游業的加速發展, 隨之給環境帶來了多方面的問題,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植物是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生態環境破壞的主要承擔者之一, 因此, 植物多樣性成為旅游干擾對生態環境影響程度的重點研究對象[1]。植物多樣性在旅游開發的影響下如何動態變化?是否由此影響了區域生態系統穩定?伴隨著一系列可能出現的連鎖問題, 植物多樣性研究逐步成為生態旅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旅游業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密不可分, 自然生態群落內不同植物相互競爭、相互依存, 組成了穩定的群落結構, 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決定著群落的結構特征和發展趨勢。但人類旅游活動所帶來的人為干擾可能破壞其中的生態平衡, 使得植物在物種、種群、群落甚至生態系統尺度出現結構的改變甚至是缺失, 以至于引起區域內生態環境的變化甚至惡化。目前, 大多數旅游區的生態環境均受到游客不同程度的干擾和破壞[2], 這些問題已引起了公眾們的普遍關注, 亟待相關學者積極參與解決。
1 旅游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背景
1.1 植物多樣性
地球上的植物與其他生物以及能量環境相互作用所組成的全部形式, 與不同層次組合的多樣化指的就是植物多樣性, 而植物多樣性還包括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多樣性三個方面[3]。20世紀中期之前, 人們對于環境的改變并未給予過多的關注, 隨著《寂靜的春天》的出版, 書中描述了人類對環境的過度干預, 引發的環境問題漸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不僅如此, 國內外學者還進一步構建和完善了植物多樣性分類的研究體系, 以便為后期植物多樣性實地調查提供更加準確的參考標準。
1.2 旅游干擾
多指在旅游活動中人為的對自然資源、環境及物種的一些負面影響, 主要表現在水體的污染、空氣的污染、植被的退化, 物種多樣性的減少及生態系統狀態的失衡等[4]。出現以上影響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游客的肆意踩踏、景區內設施建設對環境的破壞、園區活動開展、旅游活動下污染物排放的影響等[5]。在旅游干擾下, 植物是人為因素影響下的主要承受者, 影響范圍更深更廣。比如紅松作為我國東部地區的主要造林物種之一, 在本地區域環境內具有維持生態平衡穩定的作用。但是近幾年由于大力開發旅游資源, 讓紅松林受到大范圍的破壞, 使得紅松的數量逐年下降, 無法繼續維持群落內生態系統的穩定, 造成了當地水土流失、植物多樣性下降、植物群落結構改變等一系列問題。
2 旅游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意義
人們為了提高經濟效益, 在旅游區大范圍且無節制地開發建設, 極易適得其反, 引起不良后果[6]。比如過量引入游客, 易導致景區內的植物被踩踏, 影響其正常的授粉、擴散;景區內植物多樣性降低, 造成景觀效果單一, 無法滿足正常觀賞需求;更嚴重的是, 直接使得生態系統中某些因子的缺失, 破壞正常食物鏈內的物質和能量循環, 甚至使得食物鏈斷裂, 影響到整個區域內生態平衡, 從而引發更多的不良后果。
雖然學者們積極對植物與旅游干擾之間進行了諸多研究[7], 但由于旅游干擾自身多因素的復雜性, 以及植物多樣性的不同尺度范圍界定, 旅游干擾對植物影響仍然不夠明確[8]。但開展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調查研究對景區生態環境的監測與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將為協調景區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切實可行的指導性意見。
3 旅游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進展
3.1 國外研究進展
旅游活動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 游憩活動是自然環境與人為干擾之間一種最直接的表現方式[9], 也是如今人們對自然資源的另一種主流消費形式。但是隨著學者們發現旅游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逐漸增多, 環境作為旅游開發最直接的影響對象, 旅游區自然資源狀況的變化是人為干擾下最直接、明顯的自然指示器[10]。旅游、生態、資源各方面的專家開始對旅游環境受到的影響開始重點分析, 試圖尋找一個完美解決辦法, 實現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資源結合, 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11]。主要研究內容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旅游干擾對物種的影響研究。國外關于旅游活動對植物干擾這一方面的研究相比起國內, 起步比較早、范圍較廣, 研究最早始于20世紀20年代。國外學者關于旅游干擾對植物的影響進行過大范圍系統性的數據研究, 比如Habibullah等[12]通過對106個國家的抽樣調查, 發現受威脅的植物種類的數量與游客數量相關, 旅游業的發展更易增加受威脅植物的種類與數量;Morrison[13]在研究中提到, 太平洋地區內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物種的減少因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其中55%由于棲息地喪失, 32%由于過度開發, 22%由于物種入侵, 14%由于污染;Kelly等[14]認為旅游業會對澳大利亞的72個植物類群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當地被列為受威脅的346種植物類群種, 其中受旅游業威脅的比例就占20.8%。
二是不同旅游活動類型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國外學者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多數自然環境破壞案例的源頭都離不開人類活動, 所以對旅游時伴隨的人為活動進行了大量的實地案例調查, 并且得出了一些結論。比如T?ern等[15]發現在芬蘭北部森林保護區內, 徒步旅行對植被的直接影響大于滑雪活動, 但滑雪活動造成的影響范圍更廣。而騎馬活動容易引入外來雜草, 改變保護區內鄰近植物群落的結構;Kangas等[16]也在芬蘭北部的滑雪場進行過實地調查, 發現滑雪道上的植被覆蓋度高于森林, 但是其物種豐富度顯著低于森林, 且不同滑雪道上的平均物種豐富度也不完全相同;Pickering等[17]發現澳大利亞旅游保護區內為滿足游人和內部娛樂活動的需要, 清除大量植被作為基礎設施的場地, 后期基礎設施地的建造導致了水文和土壤等環境因素的改變, 在過程中引入了傳播性的病原體和雜草, 對園區內的植物造成大范圍的影響;北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內, 徒步旅行成為人們的主要旅游方式之一, Queiroz[18]調查后發現靠近小徑邊緣地塊的物種豐富度和多樣性最高, 隨著地區內海拔高度增加, 入侵物種和歸化物種的比例有所減少, 而本土物種的比例有所增加;在Aconcagua Provincial Park內調查發現, 由于人類的遠足活動易導致非本地物種引入, 但是它們的入侵也受到當地氣候的影響, 使得高海拔地區物種入侵率較低[19]。
三是游客踐踏等行為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其他類型的旅游用地內, 游人的干擾踩踏對本地植物生長具有長期和深入的影響。比如Seer等[20–21]在波羅的海沙灘上三個不同的區域進行“人類踩踏對海灘植被影響”的實驗, 得出一年生植物在第一次踩踏時, 生長就已經有初步下降的趨勢, 但后期實驗模擬踐踏壓力對于植物種子質量的影響, 卻得出沒有明顯的影響的結論;Fenu[22]在2007-2011年考察人類的踩踏對撒丁島海岸沙地的影響研究, 發現人類長期踩踏造成的后果和范圍比短期造成的影響更明顯。
國外研究主要關注點是對植物大范圍系統性的數據調查和不同類型人為旅游活動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 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樣且較為前沿, 多關注于宏觀層面的景觀生態學和3S的技術等, 調查周期普遍較長, 后期輔助人為模擬實驗進行比對, 但是對植物多樣性研究多停留在種群和群落等尺度, 應采用多層面的研究方法對不同類型的植物進行調查研究, 成為后期國外有關旅游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主要研究方向。
3.2 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有關旅游干擾對環境的影響研究于20世紀80年代才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起步較晚, 但發展迅速, 研究內容由定性分析具體到定量分析。早期時代, 秦好遠等人[23]也將國內旅游業的發展階段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階段為1980-1994年, 在這段時期內國內有關旅游對環境影響的成果較少, 且大體內容以定性描述為主, 關注的范圍是區域旅游業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第二階段為1995- 1999年, 這段時期內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趨于多樣性, 開始使用除定性研究以外的方法, 比如定點監測[24]、社會調查等[25]。后期得出一些有效結論, 比如旅游干擾對于草本層與灌木層的影響程度表現明顯, 對喬木的影響表現不明顯, 中等強度的旅游干擾利于植物種類多樣性的提高[24];第三階段為2000-至今, 這段時期國內學者對旅游業與社會環境問題的關注度有所提升, 定點定量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旅游業發展進程加快, 各方面環境問題加快出現, 專家們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在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保持平衡。主要的研究內容有兩個方面:
一是山岳型景區旅游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國內學者對山岳地形旅游勝地內人為活動對植物的影響進行過大量的調查研究[26–30], 比如倪珊珊等人[31]發現人為旅游干擾對峨眉山景區內的植被與土壤理化性質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其中草本層受影響程度最高;鞏劼等人[32]認為旅游干擾對黃山風景區內的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都具有一定的影響, 干擾的范圍區域可達游徑外10 m處;付裕等[33]認為旅游活動造成泰山景區群落物種的豐富度下降, 影響植物種類的更新與數量的增長。
二是森林公園和濕地保護區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國內對森林公園和濕地保護區等這類地區的旅游干擾也進行過大量案例的研究[34–37], 朱芳等[38]對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植被的調查中, 發現旅游干擾只造成草本層植物的物種豐富度、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和優勢度指數有顯著的降低, 對喬木層和灌木層未有顯著的影響差異;張昌貴等[39]運用典型樣地法對太白山森林公園神廟兩側的植被進行分析, 發現受旅游干擾之后, 灌木物種數量明顯降低, 草木物種數量大幅度增加, 群落中植物的物種組成及優勢度受到明顯影響。
國內有關旅游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研究主要依據多樣性指數作為游客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評判標準, 實地采樣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 宏觀層面的景觀生態學和3S技術應用較少, 且使用方法較為陳舊。對于微觀層面的重復研究較多, 多層面多尺度的綜合研究較少, 加強國內有關植物多樣性的宏觀層面數據分析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40]。
4 旅游過程中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原因
4.1 旅游景區發展中設施的修建
植物是自然景區內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生態系統中的生產者,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地位。如今, 自然保護區因為旅游需求量的增加, 為了提供便捷道路和吸引更多游客的需要, 進行了大規模的公路修建、開發[41]。保護區里的植物因施工材料的影響出現多樣性降低, 甚至導致一定數量的植物直接死亡。且開發的過程中植物種子和花容易遭到破壞, 后期無法進行授粉擴散, 使得區域內植物的擴散性受到影響。比如, 在安徽鷂落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游徑兩旁設立了觀察點, 發現旅游活動嚴重影響林下植物的物種組成結構。
4.2 旅游人群活動時的人為干擾
隨著旅游活動強度的增大, 某些脆弱的生態環境區更易受到外來行為的影響[42]。劉麗梅[43]發現旅游對草原植被的干擾使得群落結構發生嚴重的變化, 而且草原的觀賞功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旅游者的踐踏、穿越道路和旅游過程中的生產活動都對草原植被產生極大的影響[44]。比如, 南灣國家森林公園內旅游帶來的人為干擾造成園區內喬、灌、草三個層次的植物種類減少, 植物多樣性受到顯著影響, 森林群落的穩定性下降。
4.3 外來物種的入侵
王金亮等[45]認為某些外來物種的入侵也會影響植物生態結構變化, 前期有意或者無意的引入外來物種, 有些是為塑造出不適合本土條件的景觀效果, 有些是為配合景區旅游活動的開展, 但是它們的引入具有潛在的生態風險, 極易導致環境內物種失衡。外來物種若沒有天敵, 氣候環境適宜, 無法控制其生長速度, 也無法完全去除, 則會帶來一系列的生態問題。比如, 三裂葉牽牛作為外來物種, 容易攀附其他植物, 嚴重影響到被攀附植物的正常生長, 造成潛在的生態安全破壞[46]。
4.4 自然環境條件的改變
外界旅游人群帶來的干擾, 會引起旅游區域內植物所生存環境條件的變化。人為活動容易無意識地影響原生植物所需的光照、雨水、濕度的等自然環境因素, 從而導致環境內植物生長趨勢的改變, 物種組成發生變化, 有的甚至直接讓某些植物在原有生態環境內無法生存, 逐漸滅絕, 導致整個環境內物種多樣性明顯下降。比如, 在東大河林區調查發現, 由于后期自然環境條件的改變, 當地青海云杉的生長受到了影響, 種群的穩定性下降, 整個區域面臨種群老齡化的局面。
5 建議與對策
由于我國近幾年旅游業的快速發展, 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進程, 但同時也帶來了多方面的環境問題。為了讓環境保護與旅游業同步協調發展, 國家有關部門積極主張加強生態保護措施, 提高生態保護意識[47]。我們在利用環境資源的同時, 也要保證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48]。而植物在生態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所以需要創建一些相應的管理措施及對策。
5.1 制定適合的科學管理系統
根據不同區域的內部需求, 制定合理的科學管理體系, 以控制旅游高峰期和節假日旅游量猛增而造成人員的無法疏散, 使得景區內超負荷運轉的情況發生。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系統體系, 保護植物的授粉、傳播, 將人為活動對植物的影響力降到最低, 阻止人類對植物生態系統破壞的行為。注重環境容量的與旅游量的大小, 以保護景區植物生態環境為前提, 制定相匹配的監管方案[49]。比如根據《國家濕地公園總體規劃導則》可將濕地公園分為三個大類區域: 核心區、活動區和管理區, 核心區作為發掘、科考和保護的用途, 一般不對外開放;活動區是景點集中區域, 游客觀賞玩耍區域;管理區作為保護區域, 建設防護網, 游客較少涉及的區域[6]。
5.2 開展有關植物知識的科普及研學活動
將植物種類較多的園區場地劃分出來, 便于后期開展植物科普活動, 在特定的節日時對游人開展必要的植物科普教育, 提升國民尤其是學齡前兒童的素質教育, 讓他們從小樹立起保護環境的意識[50]。而且可在科普植物的活動之中, 展開一些親子合作的環節, 在游玩過程中收獲知識和提升親子親密度, 不僅讓孩子更是讓家長受益。
強化景區的自然教育功能, 將自然景區作為中小學接觸自然的重要學習場地之一, 依托景區特色的自然資源和當地高校自然教育的專業人才體系, 創造出一系列優秀的研學課程, 建造具備相關資質的研學體驗基地, 讓自然資源充分利用、使得中小學生得到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響應國家提倡的生態文明教育的號召。
5.3 加強景區內植物群落的多樣性建設
不同景區內部的植物物種多樣性的存在情況不同, 有的內部分布零散且整體群落中種類單一, 這樣的生態狀況不利于區域生態系統內動植物的良性發展, 不能長期保持生態穩定性。所以應當在不破壞當地景區的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前提之下, 加強群落內部植物的多樣性建設, 提高環境自身的自我恢復力, 而且要保證人工建筑物與景區植被能夠相互融合, 不會影響植物的自然生長。不應該為塑造某些造景的效果, 刻意移植許多不適宜本土環境的植物種類。適當發揮本土物種的生長優勢, 彌補景區內由于人為施工建設而造成的景觀破碎化的現象, 建設出一個擁有自我修復調節能力和具有較高穩定性的自然景區。
6 研究展望
國內外有關旅游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起步的時間不同, 發展速度不同, 國外缺少對植物多樣性的綜合多尺度的研究, 國內對于植物多樣性的研究方法較為陳舊, 主要研究在微觀層面上, 對于景觀生態學有關方面的研究較少。同時, 國內外學者應積極合作, 相互借鑒學習、交流前沿的研究成果, 從而得以推動旅游對于植物多樣性影響研究的長遠發展。生態旅游作為一個新興行業[51], 目前已經引起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雖然現階段發展處于初期階段, 但是它很“接地氣”, 深受中小學生和家長的歡迎, 但其仍然面臨著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 而有關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則可能成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重要突破口。
[1] 牛莉芹, 程占紅, 趙蒙. 旅游干擾下五臺山不同植被景觀區物種多樣性特征[J]. 應用與環境生物學報, 2012, 18(4): 559–564.
[2] 段桂蘭, 朱寅健. 旅游干擾對土壤生態系統的影響研究進展[J]. 生態學報, 2019, 39(22): 8338–8345.
[3] 劉思澤, 尹海鋒, 沈逸, 等. 間伐強度對馬尾松人工林間伐初期林下植被群落物種組成和多樣性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 2020, 31(9): 2866–2874.
[4] 李文杰, 潘婉雯, 宋河有. 旅游對環境影響研究的意義與展望[J]. 安全與環境工程, 2014, 21(2): 94–99.
[5] 李鵬, 濮勵杰, 章錦河. 旅游活動對土壤環境影響的國內研究進展[J]. 地理科學進展, 2012, 31(8): 1097–1105.
[6] 徐晶晶. 大溪國家濕地公園合理利用區生態旅游景觀規劃探究[D]. 北京: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 2017.
[7] 唐高溶, 鄭偉, 王祥, 等. 旅游對喀納斯景區植被和土壤碳、氮、磷化學計量特征的影響[J]. 草業科學, 2016, 33(8): 1476–1485.
[8] 張昌貴. 旅游開發對太白山森林公園植物多樣性與群落結構影響的研究[D]. 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2010.
[9] 李志強. 游憩活動對金鞭溪植物群落結構的影響[D]. 長沙: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2014.
[10] 李軍玲, 張金屯, 鄒春輝, 等. 旅游開發下普陀山植物群落類型及其排序[J]. 林業科學, 2012, 48(7): 174–181.
[11] HABIBULLAH M S, DIN B H, CHONG C W, et al. Tourism and Biodiversity Loss: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Sustainability[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6, 35: 166–172.
[12] HABIBULLAH M S, DIN B H, CHONG C W, et al.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reatened Plant Specie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224: 14–19.
[13] MORRISON C. Impacts of tourism on threatened species in the Pacific region: a review[J]. Pacific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2, 18: 227–238.
[14] KELLY C L, PICKERING C M, BUCKLEY R C. Impacts of tourism on threatened plant taxa and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J]. Ecological Management & Restoration, 2003, 4(1): 37–44.
[15] T?ERN A, TOLVANEN A, NOROKORPI Y, et al. Comparing the impacts of hiking, skiing and horse riding on trailand veget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fores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90(3): 1427–1434.
[16] KANGAS K, TOLVANEN A, KAELKAEJAE T, et al. Ecological Impacts of Revegeta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Ski Slopes in Northern Finland[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44(3): 408–419.
[17] PICKERING C M, HILL W. Impacts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on plant biodiversity and vegetation in protected areas in Austral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5(4): 791–800.
[18] QUEIROZ R E, VENTURA M A, SILVA L. Plant diversity in hiking trails crossing Natura 2000 areas in the Azore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and nature conservation[J].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014, 23(6): 1347–1365.
[19] BARROS A, PICKERING C M. Non-native Plant Invasion in Relation to Tourism Use of Aconcagua Park, Argentina, the Highest Protected Area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34(1): 13–26.
[20] SEER F K, IRMLER U, SCHRAUTZER J. Effects of trampling on beach plants at the Baltic Sea[J]. Folia Geobotanica, 2015, 50(4): 303–315.
[21] SEER F K, IRMLER U, SCHRAUTZER J. Beaches under pressure – effects of human access on vegetation at Baltic Sea beaches[J]. Applied Vegetation Science, 2016, 19(2): 225–234.
[22] FENU G, COGONI D, ULIAN T, et al. The impact of human trampling on a threatened coastal Mediterranean plant: The case of Anchusa littoreaMoris (Boraginaceae)[J]. Flora, 2013, 208(2): 104–110.
[23] 秦遠好, 謝德體, 魏朝富. 國內旅游業環境影響研究述評[J]. 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 32(5): 134–140.
[24] 管東生, 林衛強, 陳玉娟. 旅游干擾對白云山土壤和植被的影響[J]. 環境科學, 1999, 20(6): 6–9.
[25] 陸林. 旅游地居民態度調查研究——以皖南旅游區為例[J]. 自然資源學報, 1996, 11(4): 377–382.
[26] 段亞芳, 郭慧香, 張利敏, 等. 旅游干擾對河南嵩山風景區不同海拔梯度土壤性質的影響[J]. 河南農業大學學報, 2016, 50(1): 103–109.
[27] 趙建昌. 旅游干擾對賀蘭山典型草原生物多樣性及土壤性質的影響[J]. 水土保持通報, 2015, 35(3): 293–298.
[28] 王洪成, 王彤, 楊龍, 等. 旅游活動對嶗山風景區植物群落干擾的影響[J]. 山東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5, 46(2): 280–283.
[29] 馮飛, 畢潤成, 張欽弟. 旅游干擾對云丘山不同植被景觀區物種多樣性的影響[J]. 生態科學, 2014, 33(1): 134–140.
[30] 廖小娟, 卞莉莉, 何東進, 等. 旅游干擾對太姥山風景名勝區植物群落的影響[J]. 四川農業大學學報, 2012, 30(3): 287–292.
[31] 倪珊珊, 彭琳, 高越. 旅游干擾對峨眉山風景區土壤及植被的影響[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16, 37(3): 93–96.
[32] 鞏劼, 陸林, 晉秀龍, 等. 黃山風景區旅游干擾對植物群落及其土壤性質的影響[J]. 生態學報, 2009, 29(5): 2239– 2251.
[33] 付裕, 李傳榮, 申衛星, 等. 旅游活動對泰山登山中路植物群落種類組成及多樣性的影響[J]. 中國農學通報, 2009, 25(6): 215–219.
[34] 張茜, 楊東旭, 鐘永德, 等. 黃石寨景區旅游活動對典型植物群落的影響[J]. 浙江農業學報, 2017, 29(7): 1158– 1165.
[35] 鐘靜, 張捷. 基于景觀指數的九寨溝旅游區旅游干擾評價[J]. 生態學雜志, 2011, 30(6): 1210–1216.
[36] 魯慶彬, 游衛云, 趙昌杰, 等. 旅游干擾對青山湖風景區植物多樣性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 2011, 22(2): 295– 302.
[37] 李永亮, 岳明, 楊永林, 等. 旅游干擾對喀納斯自然保護區植物群落的影響[J]. 西北植物學報, 2010, 30(4): 786–794.
[38] 朱芳, 白卓靈. 旅游干擾對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植被及土壤特性的影響[J]. 水土保持研究, 2015, 22(3): 33–39.
[39] 張昌貴, 方大鳳, 劉瑩. 旅游干擾對寺廟附近植物多樣性的影響——以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神仙宮廟為例[J]. 陜西農業科學, 2012, 58(3): 39–43.
[40] 鞏劼, 陸林. 旅游環境影響研究進展與啟示[J]. 自然資源學報, 2007, 22 (4): 545–556.
[41] 于玲. 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可持續性評價指標體系研究[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06.
[42] 張桂萍, 張峰, 茹文明. 旅游干擾對歷山亞高山草甸植物多樣性的影響[J]. 生態學報, 2008, 28(1): 407–415.
[43] 劉麗梅, 呂君. 典型草原地區旅游發展對植被的環境影響[J]. 資源科學, 2009, 31(3): 442–449.
[44] 金亞征, 鄭志新, 常美花, 等. 旅游活動對草原植被、土壤環境的影響及控制對策[J]. 草業科學, 2017, 34(2): 310–320.
[45] 王金亮, 王平, 魯芬, 等. 碧塔海景區旅游活動對濕地生態環境影響研究[J]. 地理科學進展, 2004, 23(5): 101– 108.
[46] 汪朝輝. 山岳型森林公園生態安全評價研究[D]. 長沙: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2012.
[47] 劉炳亮. 自然保護區旅游開發對不同擴散模式植物多樣性的影響[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13.
[48] 董翠玲, 劉建, 王方忠, 等. 山東昆崳山國家森林公園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J]. 四川動物, 2007, 26(4): 878–880.
[49] 黃宏. 中國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管理對策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 2015, 43(34): 237–240.
[50] 單慧群. 武漢馬鞍山森林公園生態旅游開發與管理研究[D].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 2011.
[51] 叢林. 大青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旅游生態學研究[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13.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diversity
LI Mengdie1, WANG Lilong2,*, JIN Xiulong3,*
1.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0,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AnhuiNormalUniversity, WuhuAnhui241000, China 3.ChuzhouUniversity, ChuzhouAnhui239000,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ecological factors, and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plant diversity. It main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interference on plant diversity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nt d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ecotourism, as a new and vigorous industry,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still faces many unsolved problem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terference on plant diversity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is series of problems.
tourism disturbance; plant diversity; ecotourism
10.14108/j.cnki.1008-8873.2022.06.027
Q94
A
1008-8873(2022)06-230-07
2020-09-23;
2020-11-13
安徽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908085MD10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371162)
李夢蝶(1997—) , 女, 安徽馬鞍山人, 碩士研究生, 主要從事旅游生態學研究, E-mail: 1131681420@qq.com
通信作者:王立龍, 男, 博士, 研究員, 主要從事旅游生態學研究, E-mail: 24715892@qq.com; 晉秀龍,男,博士,教授,主要從事旅游生態學研究,E-mail: jxlcn@126.com
李夢蝶, 王立龍, 晉秀龍. 旅游干擾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進展[J]. 生態科學, 2022, 41(6): 230–236.
LI Mengdie, WANG Lilong, JIN Xiulong.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isturbance on plant diversity[J]. Ecological Science, 2022, 41(6): 23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