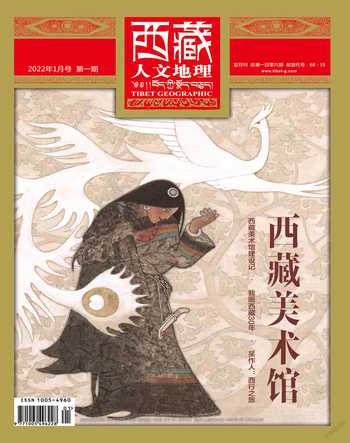資深“藏漂”畫家余友心
汪璐

20世紀80年代初期,西藏,作為一種特殊地理和文化的存在,開始成為內地知識分子的一種情結。當時四十歲出頭的余友心,相比之下在這個群落中算長輩。與西方思潮的追隨者相比,他和一幫年輕人的奮斗目標卻逆向而行。不管西方藝術界在干什么,他們選擇去了解藏民族在干什么,藏族民間藝術在干什么,宗教藝術在干什么。他們把創作扎根在藏文化的土壤上,再把學到的現代藝術創作能力與之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西藏藝術的表現形式——布面重彩。
創作于1984年的《高原天宇闊》正是余友心在那期間所畫的第一張布面重彩,作為西藏藝術家布面重彩中很有分量的早期代表作品,它進入了西藏美術館首期作品收藏名單。
位于西藏文聯大院內的一套老式二層小樓,是畫家余友心現在的畫室。這里也是他在藏工作過幾十年的地方,沒想到退休數年后,單位又給他分了一套老院子,對一個癡迷西藏的人來說,或許也算得上是落葉歸根。

屋前的老樹和房屋都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產物,它們在烈日炙烤中透著清涼古樸的氣息。進門處的寬敞院落,被主人打理得很有生活氣息。左側整齊地擺放著十個花盆,每個盆里都搭著架子種著西紅柿、辣椒一類的菜品;右側窗下則擱置著一張簡易茶幾和藏式卡墊鋪就的座椅,一旁的畫案上鋪陳著紙張、畫具,隨時靜候主人揮毫潑墨,墻上懸掛的幾幅宣紙寫意牦牛隨風輕輕揚起。
“今天采訪挺合適的,過段時間我就要去深入喜馬拉雅山溝了。”今年81歲的余友心說話時滿眼微笑,一副溫和、氣定神閑的模樣,仿佛一切盡在掌握。
1978年,余友心為所在單位立了件不小的功勞,作為獎勵,除了100元現金,單位表示還可以滿足他一個要求。于是在1980年,不惑之年的他獲得單位特許,第一次來到西藏。
在藏的半年時間里,他多次前往后藏日喀則,走遍了扎什倫布寺、白居寺、薩迦寺、夏魯寺等后藏著名的寺院,這些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壁畫,飽足了他的眼福。同時也讓他有機會結識很多當地的百姓,體驗了后藏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
“我來的第一個感受是那些地方人好,民風淳樸、文化氛圍濃厚,山河壯美。人和大自然相處融洽,能享有藝術創作最珍貴的精神境界。”
返回北京不久,余友心的單位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也加快了體制革新,領導希望調他到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畫店任職。
當時的北京改革發展充滿機遇,也是國內最早開放美術界的地方,北京畫店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幾家涉外畫店之一。就在各種羨慕的眼光紛紛投來之際,余友心卻選擇了辭別,因為他心里有了西藏。

《天鏡》

O5V6GYWfNCXOk9kH9EMObA==《閑云野鶴》
1982年7月,余友心和兩名學生帶著簡易的行李從成都走陸路奔赴拉薩。包里最重要的物品是速寫本和筆,買不起相機的年代,那就是最忠實的記錄工具了。
一路上師徒幾人走走停停,畫速寫、畫寫生、感受了解風土人情,飽覽河山壯美,也算詩意。不到20天的時間,他們就從四川盆地進入了世界屋脊,踏上了昌都的地界。
他并沒有繼續前往拉薩,而是決定先去藝術之鄉嘎瑪溝翁達崗村考察,雖然那里尚未通公路,很少有人能進去。
雇了向導,騎馬一天多,他們順利進入了大山深處的嘎瑪溝。
在那里,他有幸認識了年長自己8歲的嘎赤派唐卡畫師嘎瑪德勒。
當時嘎瑪德勒50歲,聲名還沒有今天這般響徹唐卡畫界,主要的原因是那時交通和媒介太過滯后。那也是余友心第一次零距離接觸唐卡畫家。他們之間雖然言語有障礙,但藝術思想卻是相通的;連比帶畫,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相互探討繪畫。
時光荏苒,2013年,在拉薩琉璃橋舉辦的一場唐卡邀請展上,余友心與82歲的嘎瑪德勒再次相遇,此刻他已經是譽滿藏區的嘎瑪嘎赤派唐卡最杰出的傳人、國內外公認的世界級畫家,老先生也立刻認出了余友心,兩人緊緊相擁,時光仿佛在那一刻穿越。
“與內地人以為的封閉落后相比,藏文化最核心的價值恰恰就是開放與綜合并行的藝術,最珍貴的一點就是對本民族傳承的不放棄!”這一點讓余友心心悅誠服。
在昌都的日子里,他還有幸得以鑒賞嘎瑪寺歷朝歷代珍藏下來的幾箱唐卡。
嘎瑪寺依山而建,可謂是一部多民族建筑融合的經典之作。嘎瑪寺1185年由噶舉派高僧堆松欽巴創建,已有八百多年歷史。
當近百幅傳世唐卡逐一展現在眼前,他們忘記了時間,恍惚進入了陶淵明的世外桃源。
作為回報,當寺里需要起重機進行維修時,余友心去縣里借來了滑輪,稍加改制,就達到了起重機的作用,令僧人們很是歡喜。
那樣一個偏遠的小山溝,卻把不同的文化因素綜合起來創造出一種非常獨特的、全新的藝術形式,這讓余友心受用不盡。
三個月后,歷盡波折的余友心總算平安抵達了拉薩。
80年代初期,西藏,作為一種特殊地理和文化的存在,開始成為內地知識分子的一種情結。一批以藏族青年為主體、包容了一群內地來藏美術青年的現代藝術朝圣群落,從零開始,踏上了漫長的文化苦旅,各自踐行著個性鮮明的試驗性創作研習,成為西藏現代美術群體崛起的萌芽。
那段時期,一部分畫家通過看大量的文藝書籍、畫冊,被西方藝術流派吸引,用20多年時間把西方所有的藝術風格都嘗試了一遍。
余友心卻是冷靜的,通過比較和認真思考,他選擇深入到最原生態的藏民族民間生活中去,到傳統美術的文化土壤里尋求精神食糧。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身在其中的歷史文化,用自己的情感作畫,力求開創一種不同的畫風。
與西方思潮的追隨者相比,他和一幫年輕人的奮斗目標卻逆向而行。不管西方藝術界在干什么,他們選擇去了解藏民族在干什么,藏族民間藝術在干什么,宗教藝術在干什么。他們把創作扎根在藏文化的土壤上,再把學到的現代藝術創作能力與之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西藏藝術的表現形式——布面重彩。
“西藏美術館這次收藏了我的作品《高原天宇闊》,創作于1984年,正是我所畫的第一張布面重彩。”余友心總是把布面重彩的誕生歸結為一群人的功勞。
但于他個人而言,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我來西藏沒兩年,帶的宣紙就用完了,看到藏族同胞都在布上作畫,就很想試一試,但并不是專門畫唐卡,而是吸取他們的一些傳統繪畫技法和我的所學結合到一起,包括材料使用等,我都做了融合,就這樣產生了我自己的另一種繪畫風格。”
余友心認為西藏美術館之所以選擇收藏這幅作品,是因為這幅作品的誕生,形成了一個新的藝術表現方式,也算是一個新時代的代表作。
1985年,從北京興起的美術新潮,很快風靡全國,這讓包括余友心在內的很多西藏畫家有機會參與世界各地的藝術交流活動。
“從1987年,我就開始全世界到處走,但我不是去開洋葷,而是把西藏的美好通過藝術的方式介紹給全世界。大家一看是西藏藝術家的畫,都激動得一塌糊涂。”除了繪畫,余友心還應朋友的邀請,幫忙在全國范圍內以及新加坡等國推銷西藏旅游博覽,他有些得意地挑眉:“當時效果特別好,走到哪里就轟動到哪里。”
“西藏出去的一批年輕畫家,十幾年之后又都做了海歸,大多數還客居北京,他們的身份是外國人,內心深處仍深藏著西藏情結,時刻懷念著西藏。由此可見西藏對人的心靈塑造多么深刻!”
余友心也曾多次與幾位藏族中青年畫家一道走出去辦展,當時西藏畫家的作品已經獨具風采,令外面的觀眾耳目一新。他們經過提煉,畫心中的佛、畫西藏的自然風光、畫藏民族的風俗民情……
“西方世界還給了大家一個令人欣慰的反應:他們從作品中感受到了西藏作者內心的寧靜。”余友心對此頗為自豪,“西方的文藝復興從神本走向人本,用了幾百年,我們的藝術走下神壇只用了30年!西藏歷史進程晚,但我們完成的速度快。”
“我們往傳統里走,然后創造了現代藝術。”這一段藝術探尋的經歷對余友心來講太深刻了。這些年他一邊創作、一邊進行理論思考,并時常參加國內外展覽。
他認為西藏美術已經成年了,需要總結、理清楚。
“西藏美術這30多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從深入研究西藏傳統藝術開始,然后潛心創作、創新,最后的成果是一批批土生土長的西藏中青年畫家走出去,展示西藏當代美術的成功,得到國內外的認可,這就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他說想把產生這一藝術成就的西藏文化沃土、文化生態放到一個世界平臺上去讓大家認識,因為那些東西是最根本、最寶貴的。
他把這一歷程歸結為:向世人推銷“眼福”。
眼下,整裝待發的余友心把目的地放在了喜馬拉雅山溝。
“至于去多久,我不用時間計算,只想去發現美好,再回來創作。喜馬拉雅山脈里地理很復雜,以前去過,但接觸的面很有限。”之所以選擇這些特別的線路,與余友心很推崇米拉熱巴有關,“他在一千年前就批評了佛教末法時期的弊端。他提倡眾生平等,反對階級壓迫。提出每個人要跳出苦海到達彼岸,必須靠自己。”他坦言自己把米拉熱巴當成了偶像,想接近米拉熱巴的精神境界,所以會去深入了解他走過的路和修行的環境。
與人聊天,余友心不時開懷大笑,借此表達著他對自我的認同與滿意。
其實剛來西藏時,他一樣苦悶、彷徨過。找不到自己可以涉足的范疇,感覺懸在空中,很多事情都不盡如人意,陷入精神上那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洞。
隨著對藏文化、西藏傳統藝術的了解越來越多,對西藏無限壯美神奇的大自然年復一年的親近和領悟,余友心終于找到了自己傾心皈依的崇高精神境界,他的心不亂了。
從林芝墨脫縣的原始部落到昌都貢覺縣的小村莊,幾乎走遍了西藏山山水水的余友心陶醉于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民間美術現象。他嘆服道:“這是一個以美為魂的民族,老百姓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藝術大師!
我來西藏就是從做學生開始,到現在還是一個勤奮的小學生。”
對于自己在西藏的定位,余友心用了一個詞匯——藏漂,接著補充道:“一個資深老藏漂!”言及此,他忍不住又小有得意地強調了一句:“像我這樣的狀態,不為世俗誘惑所動,心懷喜悅坦然面對人生,別人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是的,他這一漂就超過了40年,“藏漂”之言也成了他戲謔自我的幽默。在其他外鄉人忙于落葉歸根時,年屆81歲的余友心卻早已把這里當作了故鄉,他習慣這里的一切,這里也以家的方式接納了他。
3095500218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