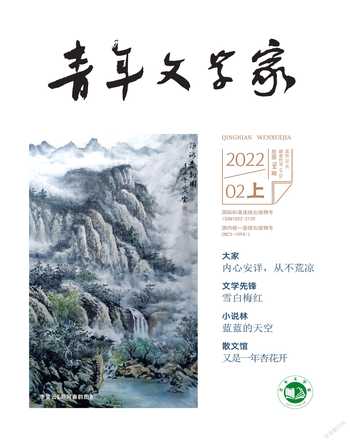走不出的原鄉
肖江
1
漢水湯湯,其輝煌煌。
漢水,生命中繞不過去的話題。興也因它,離也因它。
故鄉的家園就在漢水河畔。我在此出生、成長、歡樂、憂傷。但我從未想過,將來的某一天,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將會以某種悲壯的方式消失,迫使我遠離家鄉,遠離這一方歷史與文明之地。從此,肉身四處游蕩,靈魂無處安放。
中線南水北調,這項以漢江為源頭的宏大世紀工程,動遷不可避免。因此而進行的漢水大移民,我們被遷往七百里外的隨州。這是我現今的戶籍所在地,也就是所謂地理意義上的家鄉。但我除了那一紙戶籍之外,好像和它再沒有任何形式的交集。在心底,我從未把隨州鳳凰寨當作我的家鄉。我的心,我的根,依然停留在那個漢水之濱的小山村,那個叫肖家灣兒的地方。因為只有那里,才讓我覺得親切,哪怕遠遠地望一眼,也有滿滿的歸屬感。但是,我們終歸是遷走了的故鄉人。戶籍地的變遷,老屋的不復存在,以及那些河灘沙地盡數沒入江底,我們在此生活的痕跡被一點一點地抹去,直到與我們毫無關聯。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葉、一人、一物,無不鐫刻著我深深的思戀。
我恐懼,我憂傷,我在夢里夢外傷心得無可名狀。一次次找尋,一次次失望。那條歸鄉的路啊,看不到終點。
我不止一次地想,那時我為何要遠遷?如果后靠,我還會不會有如此濃烈的鄉愁?
世間沒有假如,如此便多了許多缺憾。我成了浮游的萍,如何再次停靠故岸,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夢里的故鄉歡聲笑語,夢里的鄉音情真意切。回首,卻是夢里水鄉……
2
這是一個被漢水環成半島的小小村莊。低矮的禿山,蜿蜒的漢水,滋養著這里的一草一木,繁衍著一代又一代的父老鄉親。
在我記事起,除了池洼和陰坡溝有一片樅樹林外,其他地方不是長滿龍須草和茅草,便是低矮的馬鞭梢。坡地貧瘠,真正的好土地太少。隨著人口瘋狂增長,這些土地根本養不活肖家灣兒的父老鄉親。于是,祖輩們開荒,樅樹、馬鞭梢、茅草窩被清理一空。本就光禿禿的山更顯荒涼。即便如此,這些土地也僅僅是讓鄉親們有口飯吃。
父親說:“這地方太窮。兒子,你要好好讀書,將來走出這地方。如果有可能,你永遠不要回來。”四五歲的時候,我理解不了這句話的含義。
在上學認識字后,我瘋狂地愛上了看書。文字,為我打開了另一片天地。在書的世界里,我知道了盤古開天地,知道了后羿射日,知道了三皇五帝。
父親是獸醫,弄來了許多書籍。我在偌大的書堆里翻找我想看的書,在文字里找尋著獨屬于我的快樂。于是三年級時,我已經把六年級以下的語文書以及歷史書全部看完。
我知道了堯舜禹湯,知道了秦皇漢武,知道了唐宗宋祖,更為朱元璋從一介布衣成為天子而擊節叫好。“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開啟了我的另一扇窗。
那時候,我有很大的理想。我想當一名農業科學家,像袁隆平一樣,為國、為民造福,讓故鄉的百姓都能吃口飽飯;我想當一名老師,授業解惑,讓閉塞的鄉民不再無知,在這巫文化的發源地,讓科學照亮未來。
少年愛玩的天性和夢想激烈碰撞。父親嚴厲地管束著我,我也不曾讓他失望,每次考試都在班級前三名。但在我上五年級那年,初冬的一個上午,父親去了遙遠的天國。我的少年時光陷入一片黑暗。
我努力讀書,努力學習,但終究敵不過苦難的現實。作為家中的長子和父母唯一的兒子,我做不到無動于衷。逃避,放棄,初三那一整年的大好學習時光,于我而言就是荒廢成一片的荒草漫長。即使如此,我還是在當年考上了鄖縣二中。錄取通知書收到以后,我僅僅看了一眼,便很干脆地把它丟在了陰暗的角落。
3
沒有盤纏,沒有行囊,孑然一身,遠離家鄉。
十六歲的我,徒步三十余里,從農村到城市,自此踏進了風云變幻的大社會。青蔥年少,以夢為馬,追逐韶華。
彼時的我,初生牛犢,不知鄉愁為何物,只想趕快離開故土。雖然不是以父親期望那般用讀書考取功名的方式,但我終究離開了生養我的故鄉。
漫漫打工路。廚房里的日子,根本沒有想象中的美好。無論白天多么讓人糟心,在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總能在文字中沉靜,讓文字洗去白日的戾氣。
于是,我成了廚房里的另類。多少個不眠之夜,當我的那些同事們在酒桌上、牌場上尋找他們的快樂時,我總是一個人孤獨地窩在昏暗的寢室,在書海里找尋我的精神食糧。寫工作筆記,記喜怒哀樂。厚厚的幾大本,記載了青春歲月中的點滴日常。
在這個城市里打工,靈魂卻一直在游蕩。沒有歸屬感的年月,我懷念故鄉的土房,思念媽媽做的飯菜的味道。
努力賺錢,壓抑思念,只為早日掙夠能在這個城市買房的錢。
城市的房子剛剛有些眉目,南水北調的動遷已箭在弦上。那座維系我和故鄉關系的老屋,在初秋時節轟然倒掉。望著瓦礫遍地的老屋場,內心止不住的悲涼。從此,我便不是真正意義的故鄉人了!
我未在隨州定居。潛意識里,我是排斥這個被稱之為“新的家鄉”的地方。三間房,七畝地,便讓人叛離故鄉?行動無果,內心更是抗拒。直到此刻,才發現我的鄉愁如此濃烈,濃烈到,成了我心中無法解開的結。
4
故鄉,并沒有因為出走時間的久遠和與它距離的遙遠而模糊。它反而在我的心中越發清晰,好像我從未遠離一樣。
在十堰工作、生活十余年,我總感覺沒有融入這座城,似乎一直游離在城市的邊緣,哪怕我一直居于這個城市的中心地帶。為了找到在這個城市的歸屬感,母親和我花光了所有積蓄,在這個城市買了一個屋,總算不再如浮萍般飄蕩。
母親和我同住,隨后,我娶妻生子。媽在哪兒,家在哪兒。固然,母親在身邊,便少了一份牽掛,多了一絲溫情。這個城市,將會成為女兒的故鄉,而我終究只是一個過客。我內心十分清楚:肉體的安頓,并不代表靈魂也一并安頓了下來,我始終游離在它的靈魂之外。
某日回歸故鄉。在老屋場四處張望,幾個年輕后生看見了我。
“你誰呀?在這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呢?”后生伢問我。
“我是誰?我是肖家灣兒的人呀!你們是誰家的孩子?”我反問。
“我們從未見過你,你怎么可能是我們這兒的,騙我們的吧?”幾個后生伢有些警惕。
我啞然失笑。在此生活了近二十年,我卻變成了不被后生們認識的“騙子”。悲不悲哀?可不可笑?但我卻笑不出來。
望著熟悉的故土,再看看那些陌生的青春臉龐,不得不承認,我早已是無根的孤獨游子了。
有風吹過。老屋場后的竹海“沙沙聲”一片,好像在為那些逝去的先人與歲月,抑或為我這個游子,奏響一曲招魂的挽歌。
5
父親,我雖然不是以你希望的方式走出故鄉的,可是你說的“如果有可能,你永遠不要回來”,一語成讖!如今,我想回到故鄉,卻是遍尋不見歸路。這一條歸鄉路啊,怎么隱匿起了身形?
我惆悵!我心傷!我成了一個流浪在外、無法歸家的孩子。
用文字消愁,成了我慣用的方式。在鄖陽籍老師們的字里行間,我好像看見了故鄉的阡陌小徑。梅潔老師的散文《我生命中的一條河》,文中的漢水那樣親切,挖浪柴的場景如此熟悉,一步步走向遠方的身影那樣模糊又清晰,我如此感同身受;蘭善清老師的《萬古一地》,講述了楚文化的源頭、遼瓦店子遺址、屈原與漢水的往事,以及因屈原而延伸出來的漢江邊上的諸多地名,黎家店也位列其中,這讓我知道了故土的來路,讓骨子里的求知一解其因。原來,我的故鄉人文如此豐富,漢水哺育的恩情代代傳承。我好像找到了靈魂的宿地!我想,這或許是我如此思戀故土的真正緣由吧。
有友人曾這樣和我說過一段話:“梅潔老師、楊菁老師、蘭善清老師,以及你,你們的行文都有漢水的身影,并且還有相同的漢水情結。我覺得,你們應同屬于‘漢水文化圈’,姑且叫‘漢水行吟’吧。”
雖然把我和幾位大咖排在一起,讓我這晚輩有幾許汗顏、幾許尷尬,但我還是十分認同“漢水文化圈”的“漢水行吟”這一說法。
借于此,多少次在不眠的午夜,我重新審視那遙遠的故鄉,還有那條赫赫有名的漢水。是的,正因為有了這育人的生命之水,才產生了源源不斷的漢水文化。水,生命之源泉;漢水文化,心靈之沃土。千秋萬代,傳承至今。代代受益,心存感恩。于是,在骨子里,對這方山水眷戀至深,千里萬里,都日夜思念著這片故土。
我好像釋懷了。
飄蕩就飄蕩吧!再也回不去的原鄉啊!雖然此生不能在故土安放肉身,現實中也找不到故鄉的歸途,可冥冥中,是文字,是漢水行吟,始終維系著我與故鄉的情緣,讓靈魂得以棲息于故鄉。
282650170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