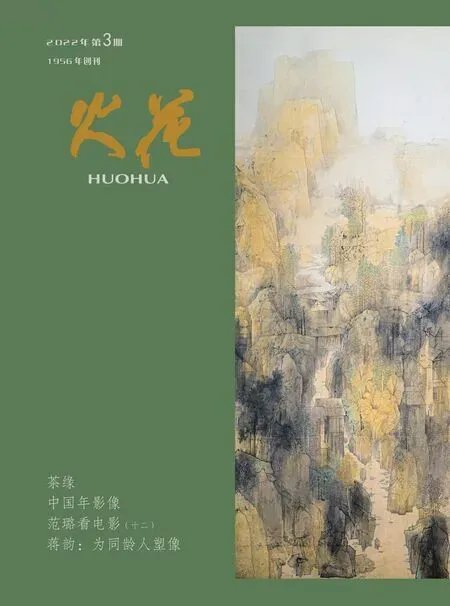何紹基: 漫道吟詩入黔來
田日曰
書法大家何紹基,有譽為“有清二百余年來第一人”。他諸體皆擅,熔鑄古今,修養精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書法風貌,得曾國藩“字必傳千古無疑”的評價。
其實,他不僅書法了得,還是清道咸年間宋詩派的倡導者和重要詩人。何紹基一生寫下大量詩文,僅《湖湘文庫》編輯、岳麓書社出版的《何紹基詩文集》,就收錄校點了其千余首(篇)。其中,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所寫并收入其詩文集的詩歌,數量就達150首之多,算得上他一生中詩作最多的一年。
而這一年的他,恰恰與貴州有關。
這年是清道光甲辰年。檢視《何紹基年表》,見有記載:“五月初一,奉命充貴州鄉試副考官。九月榜發,得四十賢,黔中人士盛稱得士之盛,前所未有。”意思是說,那年五月初一領得詔命,他作為副考官,與正考官萬青藜同赴貴州主持甲辰恩科,甄拔“滄海蛟騰四十賢”,為黔之前所未有。
如他《出都四首》寫到:“因循逾二旬,官牒促鞭弭。北堂一跪拜,簌簌淚不止。”“使車今再發,能不心悁悁?”“破涕從此行,家書幾時寄?”“乃悵半年別,念我萬里行……遇川必懷珠,逢山當采瓊。只虞力不足,還戒心自盲。誓擷邊山秀,歸使大國驚。”難舍堂上慈母,更難卻皇命及身;唯恐力弱難當,又分明是壯志滿懷。這真有點讓人糾結。
有意思的是,臨行前,除了辭別老母和家小,何紹基還去顧炎武先生祠堂拜別。“君親鑒吾身,學行須貫穿。愿從實踐人,敢恃虛談便。且當語黔士,庶弗規為瑱。再拜別先生,歸來已寒霰。”從其《別顧先生祠》中詩句看來,他這一近乎宗教性行為,顯示出顧炎武于他,已不限于學術上的宗主或者私淑的對象,可堪稱是具有人格的神性。
那一次去貴州,他們一行是經湘西取道黔東南,走的便是現今湘黔鐵路的路徑。從辰溪、芷江、晃州、玉屏到鎮遠,再到且蘭黃平……一路遍游山水名勝,相互唱和助興,處處留詩題詠,著有《使黔草》。他歌詠貴州山川勝景,流傳至今的詩文,便有《玉屏山》《青龍洞》《文德關》《飛云巖》《云溪洞》《牟珠洞》《響琴峽》《見示陽明先生遺像,敬賦書后》《九日登黔靈山》《漏勺泉》《葛鏡橋》《諸葛洞》等等,勒石諸多,給“黔文化”留下一筆筆寶貴財富。那次使黔,何紹基還巧遇既是湖南同鄉也是與父親何凌漢世交很深的貴州巡撫賀長齡。
研讀何紹基詩作可知,他們一行一入黔境玉屏,賀長齡指派的下屬早已恭候在那兒,然后一路陪同萬青藜等使黔考官去貴陽。這種禮遇,當然是鄉試對考官接待的慣例和標配,足見當時地方大員對教育的重視。但也不可否認,這其中更有賀長齡與何紹基間雖只年長他十四歲,卻可稱其為世侄的私情。
何紹基一首題為《入黔省境,中丞遣吏來迎,意當有家書先至黔,卻寄來此乃不可得,作詩寄子愚弟》的詩,透露很多信息:
“母言兒弟善承歡,兒念君恩強自寬。六十日同經歲別,七千里盼一書難。思親淚滴溪流熱,作客心吞月氣寒。山館燈花聊慰藉,連宵歸夢話團圓。”顯然,這應當是何紹基離京赴黔時,對在京的家人早有交待,說寫信直接寄給賀長齡轉交便是。這表明,賀何兩家關系相當密切。因為何紹基父親何凌漢當年在世時,與賀長齡是同鄉加同僚。至于,賀長齡侄孫女、賀仲瑗次女適何紹基侄兒、何紹祺之三子何慶熙,兩家結為姻親,則是賀長齡去世之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閏十月的事了。
果然,還沒等何紹基一路游歷到達貴州,他弟弟何紹京(子愚)寫的家書,卻已抵達賀長齡手中。但這信卻不能交給何紹基閱讀,這是何故?原來朝廷素有規定,考官受命主持鄉試期間,不得與家人通信,為的是防止打招呼舞弊。所以,何紹基知道家中有信來,卻不能親讀。
到達貴陽后,賀長齡拿出何紹基之弟紹京的家書,讓人展示給何紹基看。而這算不算徇私違規,我們今天不得而知。想必,賀長齡此舉是通融的做法,表明賀長齡既有人情也有原則。其實,這也是對何紹基的保護,免得授人以柄。
離家兩個多月,何紹基豈有不思念堂上老母之理?他所作題為《賀藕耕中丞丈得子愚弟六月廿八書,有家中平安語,遣人持示。典例不得通家書也。且慰且悵》的詩,情深且長:“萬水千山少雁聲,平安傳語未分明。高堂白發行人淚,一例關防四不情。”
另有《寄家書》,更引人淚目:“桂花香里平安字,計到家時菊酒濃。老母開顏應一笑,兒書兩月十三封。”奉命入黔,忠孝不能兩全,兩個月里寫給母親的信有十三封!
甲辰年,貴州全省考生三千六百人(一說有五千考生)云集貴陽,逐鹿科場。當年九月恩科揭榜,貴州學人共四十人中舉,被稱為清代貴州科舉的高峰盛年。
揭榜之日,作為監臨的賀長齡控制不住心情激動,居然失態地高呼:“主司得人也!”他心潮起伏地寫下這樣的詩句:“雪未飛檐席未單,萬千廣廈庇猶寒。喜聞正氣開云易,轉恐中秋見月難。婉孌半隨賓國去,衰頹只合仗鄉看。起衰幸有昌黎手,勸學頻年意未闌。”
賀長齡認為,這次恩科有此佳績,與兩位考官在學問追求上與賀長齡有著默契分不開。他在詩注中說:“兩主司皆欲以經策覘實學,與仆有同志。”
賀長齡對兩位考官懷抱感激自不用說,他《贈何子貞太史,即題其使黔草》詩中寫道:“九年徒苦口,起衰悵無由,裒然巨牘出,詫睹篇章稠”“從此士氣奮,不負皇華諏”“更抒夙昔學,以揚天子休”。
這次恩科佳績,既是賀長齡在黔九年苦心育人的欣慰回報,也是何紹基對其父八掌文衡名聲的發揚光大。何紹基先后三次為鄉試正副考官,甲辰恩科當然是他最得意的一次,故也留詩《闈墨制成,合四書文及經策得六十余篇,炳朗可觀。同人謂黔中從來所未有,喜成一律》以記,其中有句:“秋風鵠立三千士,滄海蛟騰四十賢。”
果然,甲辰鄉試之后第二年,賀長齡即由貴州巡撫升任云貴總督。
有話再往回說。何紹基一行忙完考務,便與舊友新交作別,動身回京交差。一路歡愉盡可略去,卻有兩件事情頗值一提。
一是再次路過飛云巖時,仍覺得不過癮,復吟一首《望飛云洞》,詩曰:“山山紅葉易斜暉,遙認孤亭山翠微。慚愧山僧迎馬首,客心今似白云飛。”寥寥四句,卻勾勒出一幅鮮活的山水畫:不僅有洞四周紅葉醉透的秋景之美,還有山僧招手相迎的靈動,甚至詩人因歸心似箭無法駐足賞景而對誠心相迎的山僧心生愧疚的內心世界,也表達得明明白白。這與詩人數月前路過此地時,心情判若兩樣。那時,他寫下一首七古長篇,共八十句五百六十字,以賦體手法,對飛云巖的動態和靜態都做了細膩的描繪,想象瑰奇,比擬貼切,世為推崇,令人嘆奇。
另有一事,則讓人很是揪心。是說何紹基返程時,原本想繞道長沙,順便祭拜一下歸葬在長沙西九子嶺的父親。加之“黔試甫竣,長沙友人唐印云書來謂我必歸,諄諄延佇;卒以迂道往返,須耽延月馀,請假不便,省墓莫由,凄懷惘惘”。但他歸期太緊,連祭拜父親的愿望也不能達成,還拂了舊友美意,只好寫下一首長長的《望九子嶺》五言詩表達心境。猶有句言:“船頭望湘山,云樹莽紛糾。天空祠墓寒,秋葉誰秉帚?”彼時,詩人是否淚眼婆娑,我們無法親見,但我讀這首詩時,著實是一眶淺淚的。
即便如此,當年,他們一行舟車勞頓回到北京,也是兩個多月后的十一月底。他一首《廿六日入城宿楊墨林寓園,廿七日復命后抵家作》寫到:“弟侄喧呼使者回,半年慈抱一時開……圍爐已是銷寒后,良友遲留雪夜杯。”
歲月飛逝,如白駒過隙。自那177年之后,我與一幫好友驅車從我跟何紹基共同的故鄉古道州地(今湖南道縣)出發,差不多踏著他當年足跡,有了一趟貴州之旅。幾乎是全程的高速公路,走走停停,自由自在,短短幾天假期,輕而易舉就走完他當年兩個月的行程。特別是在石崖上再次誦讀他的詩文,與他當年早已不是一樣的心境。
更有甚,但見說著不同方言甚至他國語言的游客,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乘坐一日三千里的飛機或高鐵,來游他當年游過的勝景地,全無當年的勞累,我不免有嘆,這真是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