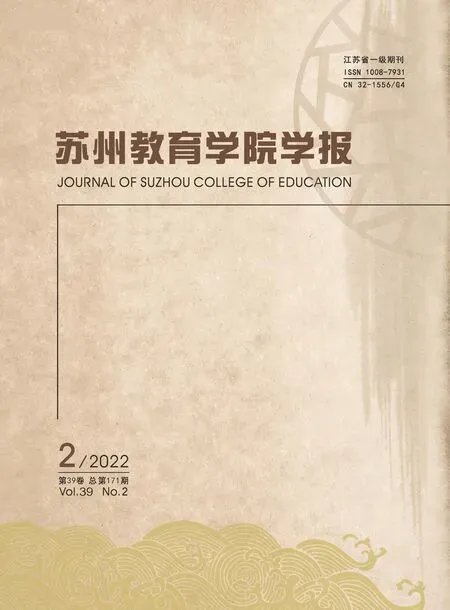當代人類“神話思維”復歸的契機
——《克拉拉與太陽》的主體意識分析
馬俊豪
(西安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
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認為,比較薩摩亞文化和美國文化,可以為美國提供一些變革的啟迪,在進行充分的田野調(diào)查后,米德從薩摩亞少女身上獲得啟發(fā),針對美國青少年的成長提出了自已的看法。[1]此后近百年,在諸多人類學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化人類學者們產(chǎn)出了豐富的田野資料和民族志成果,憑借著這些學術(shù)成果,當代人在對不同文明形態(tài)下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進行把握時,有了更多的參照。但是如果將人類看作整體,那么能為人類自身提供參照的對象又是什么?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科學技術(shù)界不斷突破技術(shù)壁壘,在探索“讓機器人變得更為智能”中取得更大的進展。然而隨著智能機器人技術(shù)的更迭,人文社科學者們陷入了一種新的思考和追問中,一時間諸如“人類的主體性問題”“技術(shù)的倫理問題”等這些古老的哲學命題和新的時代問題相互裹挾著,成為了今天人文社科研究的新難點之一。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2]講述了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智能機器人的故事,通過石黑一雄的想象,也許在藝術(shù)真實中,我們迎來了一個反思人類自身思維問題的新契機。
一、自我意識的生成—狀語條件的補闕作用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與太陽》中塑造了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克拉拉,但是克拉拉的“自我意識”是殘缺的,而這樣的殘缺又與社會歷史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通過對克拉拉個體意識的分析,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社會歷史是如何作用于個體意識的生成,進而決定其發(fā)展和走向的。
(一)“自我意識”的生成和“狀語條件”的不足
喬納森·布朗和瑪格麗特·布朗在《自我》中,充分分析了“自我意識”的生成機制,他們認為,“人們對生活事件所做的歸因構(gòu)成了人自我認識的重要來源”[3]87。在歸因欲望的驅(qū)動下,認知主體會主動地對外部世界作出反應(yīng)和選擇,進而獲得認識,產(chǎn)生意識。《克拉拉與太陽》中,克拉拉的自我認知便與她強大的歸因能力息息相關(guān)。克拉拉尤其擅長觀察世界、總結(jié)規(guī)律。例如,當克拉拉在展示櫥窗中看到萎靡的乞丐因陽光的照射而振作起來后,便對陽光的作用進行了歸因,得出“陽光的滋養(yǎng)拯救了人類”[2]48這一結(jié)論。可見克拉拉對外部世界的歸因是她生成自我意識的重要來源。在歸因活動中,克拉拉不斷豐富著自己的知覺,推動著主體“自我意識”的生成與演化。
無法忽視的是,克拉拉生成的“自我意識”,始終存在著與“自然人”之間無法彌合的“認知”偏差。英國心理學家漢弗萊在分析“機器人的意識能否被設(shè)計”這一問題時,敏銳地指出,“基于理論設(shè)計原則,從頭開始建立一個有意識機器人……在實踐中幾乎無法完成的原因是:沒有辦法重造這個自然的歷史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已經(jīng)賦予出現(xiàn)在自然腦中的活動以意識的獨特模態(tài)品質(zhì)”[4]187。由于克拉拉善于在生活中觀察與認知世界,故而儲備了豐富的個體經(jīng)驗,并得以在歸因中深化“自我意識”的革新。但由于缺乏自然演化的歷史條件,克拉拉“自我意識”中的“歷史傳統(tǒng)”漏洞無法通過個體經(jīng)驗的累積而填充,這意味著不論克拉拉個體怎么努力,仍然無法獲得與人類等同的認知經(jīng)驗。
此外,作為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artificial friend,AF),克拉拉是被人設(shè)計出來的,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陪伴兒童長大。如何填補機器人自我認識中的“歷史傳統(tǒng)”漏洞,不論對于克拉拉的設(shè)計者還是使用者,均是被忽視的環(huán)節(jié)。正如小說中,克拉拉在面對來到店里挑選機器人的顧客,沒有盡力展現(xiàn)自己的優(yōu)勢時,經(jīng)理會毫不客氣地對克拉拉說,“是顧客在挑選AF,千萬不要弄反了”[2]41-42。
機器人如何才能產(chǎn)生類人的意識能力,漢弗萊提到了“狀語條件”的概念,即“重新發(fā)現(xiàn)情態(tài)的關(guān)鍵狀語特性(而不是碳摹本)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整個自然演化的進程,這個過程首先將它們置于像我們這樣的動物中”[4]187-188。小說中,克拉拉與人類生活在一起,使其在共時向度上獲得了產(chǎn)生類人意識的“空間狀語條件”。但是在歷時向度上,由于“時間狀語條件”的空白,克拉拉無法真正在個體的成長中明確自已的身份與定位,而這也是克拉拉的意識與人類意識之間無法彌合的裂痕之一。
(二)“主我”的斷裂和“賓我”的缺位
威廉·詹姆斯將個體意識分成了“主我”和“賓我”兩個部分[5],在詹姆斯的影響下,后來的心理學家用“主我來指代自我意識中積極地感知、思考的部分,而賓我來指代自我中注意、思考或感知的客體部分”[3]15。
小說中,克拉拉不僅善于從細微處觀察與認知世界,還頗具理性分析能力。但是在克拉拉個體意識的構(gòu)建中,由于“狀語條件”的先天不足,與人類相比,她的“主我”和“賓我”均存在一定缺失,表現(xiàn)為“主我”的斷裂和“賓我”的缺位。
對于“主我”來說,建構(gòu)認知的“同一性”是“主我”得以穩(wěn)定的前提。而認知“同一性”的關(guān)鍵便在于主體“對于先前知覺及相關(guān)影響的持續(xù)記憶”[3]67。作為機器人,克拉拉獲取能量、維持運轉(zhuǎn)的方式是對太陽能的轉(zhuǎn)化,因此她基于對個人生活的總結(jié),天然地認為陽光是自然界一切能量的來源。同時,因為前文提到的“乞丐照射陽光事件”,便更加深化了克拉拉對太陽能量的認知,進而產(chǎn)生了“太陽崇拜”心理。但由于缺乏歷時演化的“賓語條件”,克拉拉沒有認識到乞丐恢復精神的偶然性和太陽并不能治愈一切人類疾病的必然性。于是,當克拉拉決定向太陽獻祭出維持自身機器運轉(zhuǎn)的重要液體,以求得太陽對喬西的恩賜時[2]350,克拉拉的認知與現(xiàn)代人類的認知之間的偏差便展現(xiàn)了出來,而這一富有張力的情節(jié)也為克拉拉的行為添加了悲壯感。但是這一悲壯行為背后所展現(xiàn)的正是克拉拉的認知與現(xiàn)代人類的認知之間的斷裂點,以及克拉拉的“主我”意識在“歷史演化條件”中缺失的表現(xiàn)。
在自我認識中,“賓我”是對于“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是什么的看法”[3]36。詹姆斯將“賓我”的存在劃分為“物質(zhì)自我、社會自我和精神自我”三個維度。[5]314-318小說中,喬西的母親希望克拉拉能在喬西死后成為喬西的替代品,這也促使克拉拉不斷反思:自己與喬西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區(qū)別?從“物質(zhì)自我”的維度來看,機器人克拉拉與人類之間的區(qū)別是顯而易見的,機器人的身體和碳基生物的身體之間的區(qū)別顯然無法彌合。對于“社會自我”來說,克拉拉在實踐中得出“人內(nèi)心中無法在機器人身上延續(xù)的地方不是在人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愛她的人的心里面”[2]385。克拉拉認識到,她再怎么精確地復刻喬西,自己依然只是一臺機器,她無法觸及“母親、里克、梅拉尼婭管家、父親這些人在內(nèi)心對喬西的感情”[2]385。喬西的家人也許十分情愿讓克拉拉替代即將死去的喬西,但是他們自身卻無法將對喬西的情感轉(zhuǎn)嫁到克拉拉身上,這也是克拉拉無法取代喬西的重要原因,也是克拉拉“賓我”意識中“社會自我”缺位的體現(xiàn)。從“精神自我”的維度來看,喬西的父親認為,人心就像一個房子套著另一個房子,你永遠也不知道人的心中究竟會存在多少房子[2]276。克拉拉最終接受了這一關(guān)于人心的論述,認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無法真正地復刻喬西的內(nèi)心,這表明在“精神自我”的認識上,克拉拉也清楚了自己的認知與人類的認知之間存在的差異性。
二、科學與神話—被隱匿的思維
隨著工業(yè)文明的繁榮,自然與文化二元對立的思想甚囂塵上,在激進者眼中,“自然”更是被描繪成了一種拒絕變化的過時之物。而“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的對立就是自然與文化之間對立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而由于“狀語條件”的缺失,克拉拉的思維中并未顯現(xiàn)出“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性,其意識中的“神話思維”并非隱性存在,而是顯性的,并與“科學思維”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和諧共生的狀態(tài)。吊詭的是,克拉拉的這一思維方式固然使得自己與人類格格不入,但是深入分析后,這些不同點卻從側(cè)面打開了人類的自反空間。我們有必要對這一表征作進一步挖掘和解碼。
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對“庫庭斯”機器的描寫,當“庫庭斯”開始運行時,會產(chǎn)生大量污染,在“庫庭斯”的轟鳴聲中,濃煙一度遮蔽了太陽,這使克拉拉感到恐慌,因為在克拉拉的認知中,“庫庭斯”產(chǎn)生的污染會惹怒太陽,進而導致人類生病,想要治愈喬西,最為可行的方式就是摧毀“庫庭斯”,以求得太陽的原諒,為了達成這一目的,克拉拉甚至不惜取出維持體內(nèi)正常運轉(zhuǎn)的重要液體。另外,在克拉拉看來,陽光所照射的空間理應(yīng)是鮮亮明凈的,在陽光下生活的生物應(yīng)當是友好柔和的。但是在去往瀑布的路上,克拉拉在看到農(nóng)場的公牛后大驚失色,甚至叫出聲來[2]126。對于自己為何如此恐懼,克拉拉解釋道:“之前從沒有見過這樣一種東西,竟能在同一時間內(nèi)傳遞出這么多預示著憤怒與毀滅意愿的信號。”[2]126在“太陽崇拜”的認知下,帶有“負面情緒”的公牛出現(xiàn)在陽光下,克拉拉無法接受,因為它的存在打破了克拉拉內(nèi)心對于太陽的認知邏輯。值得一提的是,克拉拉對太陽的敬畏,并非源于科學知識的匱乏。在小說塑造的世界中,得到“基因提升”的孩子們,往往擁有更聰明的大腦,能夠理解更加復雜的知識,進而考進好大學,迎接更加光明的未來。里克的母親因為里克沒有得到“基因提升”而感到焦慮,為此她求助于克拉拉,希望克拉拉能夠幫助里克學習,理解教科書。[2]190可見克拉拉對科學知識的掌握是高于未得到過“基因提升”的人類的。為什么克拉拉能夠在掌握了“科學思維”的基礎(chǔ)上,仍然能保持自身“神話思維”的完整性,并與自然之間維持相對和諧的關(guān)系?這其中展現(xiàn)出的正是石黑一雄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和哲學反思。當克拉拉身上的“科學思維”與“神話思維”能夠很好地融合時,我們不妨對“神話思維”的隱匿過程進行梳理。
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落后的社會更加敬畏自然的力量。[6]70但工業(yè)時代以來,自然和文化愈發(fā)被看作是兩種不相融之物,自然代表著拒絕變化的無機物,而文化則是馴服自然之后的派生物。列維-斯特勞斯說:“發(fā)展意味著我們要將文化置于自然之上,而給予文化的這種優(yōu)先權(quán)幾乎從未以這種形式被接受—除了被工業(yè)文明接受。”[6]71為了發(fā)展,人類將文化置于自然之上。作為“自然思維”代表的“神話思維”也逐漸趨向隱性。一方面,馬林諾夫斯基在考察神話和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后認為,“神話世界因滄海桑田的變化而豐富。……反過來,敘述得極具感染力的神話故事又反作用于山川……賦予山川明確的意義”[7],在工業(yè)文明高度繁榮的今天,馬林諾夫斯基筆下“神話”與“現(xiàn)實”交相輝映的思維方式已盛況不再。另一方面,在馬林諾夫斯基看來,神話是為了“滿足深切的宗教欲望、道德要求、社會的服從與介入,甚而實用的需求”[8],神話和宗教一直以來關(guān)系密切。在“科學思維”的萌芽期,為了給予其合法性,進而集合社會意識,人們只能對宗教思維和神話思維進行徹底的攻擊,直至今日,人類認知中的“神話思維”日漸式微,便不足為奇了。但是隨著戰(zhàn)爭、疾病、自然災(zāi)害、文化沖突等問題接踵而至,人類不得不開始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緊張關(guān)系,而石黑一雄所堅持的國際主義寫作,就是要關(guān)注諸如此類的人類共通性問題。
對構(gòu)成人類今天思維的“歷史狀語”進行爬梳后,我們可以看到,“神話思維”作為早期人類認知世界的重要思維方式,是在“科學思維”產(chǎn)生之后,才逐漸退居幕后的。對于回歸“神話思維”本身,列維-斯特勞斯提到,“神話思維的本質(zhì)在于符號的多樣性,即:在對多種已知條件加以比較時,得出不變的特征”[9]。在對太陽崇拜和與太陽相關(guān)聯(lián)現(xiàn)象的感知下,克拉拉深化了個體對太陽意象的認知,并進一步將太陽神圣化,但是這樣的神圣化似乎也并不影響克拉拉“科學思維”的發(fā)展。談及“科學思維”和“神話思維”的關(guān)系時,列維-斯特勞斯又說:科學思維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不僅能解釋自身的有效性,還能解釋存在于神話中具有真確性的事物。[10]自然與文化、科學與神話理應(yīng)是并行不悖的。格羅茲在《時間的旅行—女性主義,自然,權(quán)力》中駁斥了現(xiàn)代社會將自然與文化置于對立面的思維方式,她認為,“自然并非文化的異己之物,而是文化的根基”[11]。與人類相比,克拉拉更加敬畏自然,且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也更加和諧。
我們在小說中看到了“歷史狀語”被抽離之后,“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得以和諧共生的表現(xiàn)。克拉拉的形象似乎就在向我們描繪著一幅兩種思維和諧共生的藍圖,并引導著讀者重新反思和認識人類。克拉拉的故事,或許是一個反思人類演進中思維變化的契機。今天的人類,即使無法抽離自身已經(jīng)具備的“歷史狀語”條件,但是識別出我們“歷史狀語”中戕害“神話思維”的元素,可以幫助我們還原自身思維的完整性。
三、重新認知自我的契機—人工智能機器人時代的人類主體性反思
在前文的分析中,“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被“歷史狀語”截然分開,而“歷史狀語”的生成背后又與社會的變革息息相關(guān)。作為一篇虛構(gòu)的文學作品,《克拉拉與太陽》當然不能作為批判現(xiàn)實的材料,然而在藝術(shù)真實的維度,石黑一雄或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那就是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拾“神話思維”的可能性,以及探索在今天的語境下,人與自然、神話與科學和諧共生的可能性。
小說中的喬西由于罕見的家族遺傳病,死亡的可能性極大,她母親和卡帕爾迪先生試圖讓克拉拉復制喬西的行為和思想,并在喬西死后及時填補母親的內(nèi)心。這種想法遭到了喬西父親的否決。為了論述喬西的不可復制性,父親提及了“人心”的概念,在父親看來,“人心”才是讓每個人成為獨特個體的原因,并且“人心”是無限的、不可復制的。而父親與母親等人的分歧,即是對“什么是人”這一問題的分歧,也是對認知自然與文化間關(guān)系的分歧。
在福山看來,人在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中要實現(xiàn)自我社會化,并擔當起一系列的角色—天主教徒、工人、離經(jīng)叛道者、母親、官僚等,這些角色限制了人們進行選擇的自由,通過規(guī)范將人群聯(lián)系在一起,并由他們嚴格執(zhí)行規(guī)范。[12]一方面,在分工日益精細化的現(xiàn)代社會,人們想要在某一領(lǐng)域獲得成就,需要從身體和思維上均達到該領(lǐng)域的要求,進而全面沉浸于自己的社會分工中。但是分工本身就是對整體進行部分的切割,這樣的分工的確確保了社會發(fā)展的動力與速度,但是卻傷害了人本身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假肢、人工晶體、人工耳蝸等新技術(shù)的出現(xiàn)幫助人們獲得了肉體和感官上的延伸,人類自身的完整性又在技術(shù)的更迭中得到彌補。
在頗具戲劇性的現(xiàn)實中,人們開始思考,也許有朝一日肉體也能被金屬或其他人造物替代,同時個體的意識卻依然能夠生成,而當有機體和無機體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和絕對界限不復存在時,人類又該如何認識自己。2016年,谷歌的圍棋機器人AlphaGo相繼戰(zhàn)勝人類棋手李世石和柯潔,一時間人工智能產(chǎn)品在智力上可能會超越人類的說法甚囂塵上,而這種觀點所帶來的恐慌也使人類對于自身存在的主體性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克拉拉與太陽》中,石黑一雄并未表現(xiàn)人與機器人的對立,克拉拉也從未想過替代喬西,她所探索的僅僅是讓喬西及其身邊人如何感到快樂。在喬西患病后,克拉拉向太陽祈禱破壞那些制造污染的機器人,甚至不惜獻出體內(nèi)重要的液體,以幫助喬西康復。克拉拉意識中的“神話思維”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打動讀者,促使讀者去回憶人類思維的缺失,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路徑。
小說中太陽的意象反復出現(xiàn),克拉拉對太陽的崇拜一方面宣告著自己與人類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展現(xiàn)著自己意識中“神話思維”的影子。小說就是在這二者間的張力中不斷呼喚讀者去思考,在今天的語境下,我們應(yīng)當如何看待意識的生成?如何彌補人類自身意識的缺陷?
克拉拉雖然只是一個虛構(gòu)的形象,但是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已成事實,也許不久之后,類似克拉拉的機器人終將問世。但在此之前,石黑一雄用他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和藝術(shù)想象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自己思維的契機,或許通過與克拉拉的對比,人類能夠在反思中探索出一條“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共生的道路。
四、結(jié)語
《克拉拉與太陽》延續(xù)了石黑一雄的國際化主題,表現(xiàn)出對當代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的深刻思考。透過克拉拉的故事,我們看到了人類在享受工業(yè)文明的繁榮和生產(chǎn)力紅利的同時,也自我閹割了個體完整的意識和思維,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處于二元對立之中難以自拔。一個世紀之前,在米德等人類學家的努力下,我們看到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并在豐富的田野資料中生成了對不同文化模式進行對比的可能性。今天,在石黑一雄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故事中,我們得以在克拉拉的“主體意識”與人類“主體意識”的對比中去思考,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其主體性何在,以及思維中失落的部分該如何打撈的問題。這也是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我們迎來的一個反思自身思維局限性的新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