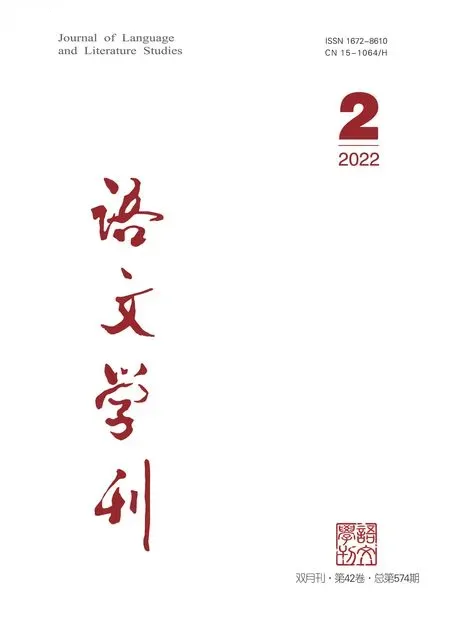近期長篇報告文學的武陵山區脫貧攻堅書寫
○ 王泉
(湖南城市學院 人文學院,湖南 益陽 413000)
武陵山區地處中國西南的湘、鄂、黔、渝的交界地帶,山高路險,四季分明,民風淳樸。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經濟發展不活躍,許多農民掙扎在貧困線上。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經濟開始復蘇,特別是伴隨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極大地改善了一些偏遠農村的落后面貌,帶給基層群眾家的溫馨感。許多中國作家有感于這片土地的變化,通過實地采訪,寫出了一批長篇報告文學作品,表現了武陵山區脫貧的歷程。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彭學明的《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羅長江的《石頭開花》、謝慧的《古丈守藝人》、歐甸丘的《決戰武陵山——新華社記者貴州掛職扶貧記》、何炬學的《太陽出來喜洋洋——重慶脫貧攻堅見聞錄》和盧志佳、楊俊江合著的《花茂沃土》等報告文學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書寫了脫貧攻堅中的動人事跡,見證了新時代武陵山區農村變革的風采和基層群眾擺脫貧困、安居樂業的新面貌。
一、聚焦鄉村人物的精神演變
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他不可能獨立于社會之外,成為一個“超人”,因此,從一個人的成長經歷可以看出社會變遷對他的影響。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表明,只有探秘采訪對象的心理,才能呈現出不同時期不同個體的真實心態,以折射社會的變遷。脫貧攻堅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的發展舉措,解決的不僅是貧困戶的溫飽問題,而且涉及廣大干部和群眾思想觀念的轉變,所以,脫貧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付出愛心與耐心,攻堅則顯現了一種迎難而上的決心、信心與毅力。
武陵源山清水秀,人文薈萃,但貧窮迫使一些年輕人離開了生養他們的故鄉,為了生計而奔走四方。故土難離,孤獨的老人和兒童又讓這些人牽腸掛肚,在外漂泊的境遇加速了他們回歸故里的渴望。隨著政府一系列惠農政策的推行,一部分農民工意識到家鄉建設的緊迫性,已經返鄉創業,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使原本落后的農村煥發了勃勃生機。羅長江深深地感受到脫貧攻堅的協奏曲在湘西大地的回響,他創作的報告文學《石頭開花》從武陵源旅游業的興起開始敘述,寫出了回鄉創業的一批武陵山區人的開拓精神。陳玉林夫婦為了家鄉的未來,帶領鄉親奔小康,開啟了武陵人的新生活。作品以張家界市“五號山谷”民宿從無到有的崛起,書寫了鄉村振興的意義:“留得住農民,才留得住文化,留得住鄉愁”[1]。李平回到自己的故鄉——桑植縣,發展鄉村民宿,把龍尾巴村打造成“國際慢村”,將生態宜居的理念融入鄉村民宿建設中,打開了村民致富的大門。作品還敘述了王作軍創辦“湘阿妹”公司的故事,道出了湘西傳統美食的新生之路。熊風創建雕塑園,則讓普通的石頭變成了藝術精品,為當地的旅游業錦上添花。作品對童軍依靠科技發展生態農業之舉的描寫,突出了湘西新一代農民突破傳統思維模式、挑戰自我的勇氣。童軍面對冷嘲熱諷,沒有灰心喪氣,而是死磕到底,終于建立了生態多樣性的水稻生產基地,實現了農業致富夢。通過這些創業故事,作品道出了石頭“開花”的時代意義:只有抓住機遇,才能迎難而上,擺脫貧困,實現鄉村的振興。同時,作品通過穿插微電影中的對話與生活片段,描寫李冰帶領楊家坪村人脫貧的故事,體現了黨員干部舍小家顧大家、以身作則的風采。
口述實錄報告文學以講述者的原話為中心,往往帶給讀者一種強烈的現場感,作者、讀者與講述人構成了一個同聲共享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講述人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作者和讀者都成為故事的“聆聽者”。當然,作者在敘述聽到的故事時,也自覺地參與了故事的建構。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以口述實錄的方式記錄了真實的場景:第一支精準扶貧工作隊進駐十八洞村后遇到了不被理解、甚至被“酒鬼”龍先生砸了場子的尷尬局面。這一頗具戲劇性的情節讓讀者如身臨其境,感受到了這個小村村民思想轉變的迫切性。作者在敘述時看似不動聲色,還原這樣的場景,實際上已把作者自己和讀者帶入到故事的情景之中。通過老村主任的口述,我們看到了一個貧困村村干部的苦衷:老婆不支持。但為了實現村民脫貧的渴望,他挺過來了,最后得到了家人的支持。透過這則故事,作品讓讀者看到了農村基層干部無怨無悔的執著。村民龍金彪成立合作社、發動大家種植無患子樹的經歷,則顯現了新一代農民沖破束縛、闖出致富路的智慧。年輕的村民楊超文到外地打工找不到門路,后來在村里辦起了農家樂,實現了自給自足。擺攤子的小石,雖然嫁給了一個歪脖子的男人,但靠賣一些土特產生活,依然感到了勞動的快樂,體現了她知足常樂的心態。一些村民發展黃桃種植業,增加了收入的同時,還推動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透過這些故事,作品形象地勾勒了十八洞村村民走出貧困、走向廣闊天地的軌跡,向讀者呈現了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與溫情暖意。
在中國的教育發展史上,鄉村教育的滯后至今依然是一個亟須解決的難題。地處偏僻的武陵山區的鄉村教育方興未艾,需要有志者能夠扎根這里的農村學校,讓貧困學生接受義務教育,顯得十分必要。《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中的浦老師是李迪細心刻畫的一個平凡人物。作為十八洞村小學的一名教師,浦老師除了教不同年級的學生的課,還要負責用摩托車把他們的午餐運回來。但他沒有任何怨言,而是在學校周圍都種了花,把學校當成了家。作品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浦老師的關于鄉村教育的匯報材料,表現了對熱情有為的年輕人的欣賞。這個故事寫的是教育扶貧,歌頌了青年一代扎根鄉村教育的奉獻精神。可見,作品通過一個個活生生的個案,把有志者追逐幸福生活的畫面鋪展開來,還原了生活的本相。著名作家鐵凝認為:“他的作品是質樸的,沒有華麗的修辭,他努力寫出人民心里的話,他的風格溫暖明亮,他的態度情深意長,這在根本上源于他對人民群眾深切的情感認同。”[2]也許正是由于李迪的平易近人、豁達、開朗,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平淡無奇的語言中透射出感人的色調,因而在眾多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中脫穎而出。
歐甸丘的《決戰武陵山——新華社記者貴州掛職扶貧記》以一個記者兼扶貧干部的眼光審視了發生在銅仁地區的山鄉巨變。作品從石阡縣山、路、水、房的變化寫起,展現了干部作風、生態環境的轉變以及群眾由信心不足到奮力追趕的剪影,突出了扶貧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硬骨頭”精神,并反思了脫貧攻堅中的干群關系。這部作品從農村生活的實際出發,集中塑造了羅忠樞、楊雁、張舉等一批基層干部形象,表現了他們與農民同甘共苦、默默奉獻的情懷。同時,作為扶貧干部的“我”與作為記者的“我”構建了一個多聲部的敘事,將親身體驗、耳聞目睹與深度訪談相結合,揭示了脫貧攻堅中的困惑,展望了這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未來。
何炬學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重慶作家,深受重慶地域文化的影響。他的《太陽出來喜洋洋——重慶脫貧攻堅見聞錄》一開始就從民歌《太陽出來喜洋洋》《嬌阿依》、黃庭堅的《竹枝詞二首》和文化典籍《尚書》里探尋重慶人自古以來代代相傳的喜洋洋精神,揭示了重慶人不怕吃苦、勤勞、樂觀向上的精神的源遠流長,這無疑升華了扶貧攻堅的意義。第三章《選擇:寧愿苦干,不愿苦熬》描寫了黔江縣村民養牛、發展生豬產業和養蜂產業脫貧的經歷,突出了武陵山區人民依靠自身的地理環境,自力更生謀發展的精神。第六章《聚焦:以河壩村為例》通過河壩村的過去與現在的對比,刻畫了公路修通之后的變化。以前村里人總擔心做夢時翻身會掉進懸崖,如今在幫扶隊的開導下,有的殘疾人改變了古怪的脾氣,脫了貧;有的因為幾個孩子讀大學,導致了暫時的困難,通過幫扶,擺脫了窘境。作品這樣寫道:
如今在河壩村,曬著太陽等脫貧的人沒有了。特殊困難家庭,都得到了兜底性保障。兩不愁三保障,落實到了每一個家庭。人的精神面貌,有了較為根本的改變[3]。
可見,腳踏實地的扶貧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河壩人找到了存在的價值和生活的樂趣,扶貧貴在扶志的社會意義凸顯出來。
窮則思變,在求變中謀發展,不僅是個人進步的源泉,而且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法寶。脫貧攻堅是一場硬戰,需要各方面的齊心合力。近期的長篇報告文學通過記錄這場戰斗中的人情冷暖,發現了不同的個體脫胎換骨般的變化。同時,通過描寫群體的協作,展示武陵山區旅游扶貧與自主創業的交相輝映,表現了各族干群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實干精神,凸顯民族的凝聚力,此類報告文學也因此以強烈的時代性見長。
二、追本溯源,書寫新的鄉村傳奇
費孝通認為:“人之所以要有記憶,也許并不是因為他的腦子是個自動的攝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實,人利用此能力,發展此能力,還是因為他‘當前’的生活必需有著‘過去’所傳下來的辦法。”[4]文化創新同樣離不開對人類記憶與歷史的傳承。武陵山區是漢族、土家族、苗族、瑤族、侗族等20多個民族的聚集地,經過長期的發展與民族的融合,已經形成特有的傳統。楚文化、巴文化相互滲透,使得武陵山區流傳著神秘的傳說,形成了民間信仰。如關于廩君的傳說,寄寓了土家族人的白虎信仰。湘西地區民間流傳的蠱術,則帶有明顯的巫術色彩,是苗族人以毒攻毒的智慧體現。近代以來,以賀龍為代表的革命先烈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發掘不同村落的歷史文化,重新認識鄉土景觀的人文價值,將歷史、記憶與火熱的現實聯系起來,書寫新的武陵傳奇,成為近年來長篇報告文學的一個亮點。
因長篇散文《娘》而名聲鵲起的彭學明,一直關注與思考著湘西的變與不變。他忘不了湘西古老的民間文化對他的滋養,惦記著父老鄉親的生活狀況。他創作的報告文學《人間正是艷陽天》全景展示了十八洞村五年來的巨變,將十八洞村五年前的景象和如今的變化進行了對比,凸顯舊貌換新顏的時代新貌。這部作品以大量的數據勾勒出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莊在扶貧工作組的帶領下走出閉塞和貧困、走向開放的圖景。由于十八洞村由飛蟲寨、竹子寨、梨子寨和當戎寨合并而成,通過把原來的土路進行硬化,改善了交通。與此同時,通過原汁原味地修繕原有的民居,既保存了苗族村寨的典雅、古樸,又改善了居住條件,實現了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彭學明作為一名湘西人,對故鄉的變化感到由衷的喜悅,在他的筆下,臘肉、苗秀都插上了翅膀,變成了父老鄉親眼里的金鳳凰。可見,從散文《娘》到報告文學《人間正是艷陽天》,他的筆下始終洋溢著濃郁的鄉情。《娘》道出的是一個兒子對母親的牽掛與愧疚,彌漫著與生俱來的孤獨感。《人間正是艷陽天》則以滿腔的熱情描寫十八洞村人的成就感,字里行間流淌著自豪之情,這無疑是彭學明又一次的精神返鄉。他從十八洞村人幸福的笑臉里看到了自己曾經的憧憬,看到了湘西鄉村振興的未來。
西蘭卡普是土家族傳統的藝術精品,其斑斕的色彩與圖案凝聚著土家族人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羅長江的《石頭開花》在《西蘭卡普道情》一章中敘述了古老的土家族織錦經過改造后煥發出來的異彩。在講述丁世舉創辦織錦公司的故事的同時,穿插了土家族《梯瑪神歌》中有關西蘭卡普的傳說,表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過程中土家人不忘祖訓、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在《高峽深峪筑路歌》中,作者回溯了白虎堂村人昔日對于生活的失望和修路的歷史,展現了當地群眾通過修路走出峽谷、走出貧困的堅韌毅力。同時,作者還借龍潭坪鎮的紅色文化資源,展望了從農業旅游到紅色旅游開發的廣闊前景,情理交融,道出了傳承湘西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性。可見,羅長江沒有羅列傳說和歷史,而是發掘其中的地域文化傳統,思考著文化扶貧的可行性。這樣就把敘事、抒情與議論融為一體,形成了立體化的書寫。
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在描寫脫貧攻堅的同時,通過九十多歲的龍文典老人之口,道出了昔日解放軍在村寨抓土匪、斗地主的故事,流露出老一代農民發自內心的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感恩之情。這樣的敘述,直接將采訪對象的話語作為報告文學的內容,避免了說教味,使得敘述變得更加親切而鮮活。
在中國的西南地區,土司作為當地少數民族民間的政權組織,在管理地方事務、維護民族團結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以傻子二少爺的視角演繹了一個藏族土司部落的興衰,表現了大膽的藝術探索精神,成為當代文學的經典。報告文學不同于小說,但同樣可以書寫歷史,以古鑒今,觀照現代社會的人性演變。何炬學的《太陽出來喜洋洋——重慶脫貧攻堅見聞錄》追溯了石柱土司的歷史,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土司夫人秦良玉平定叛亂、三次勤王和精通農業的偉績,凸顯土家族兒女勤勞、勇敢、踏實的優秀品質,繼而反思黔江農村扶貧的現狀,突出了先賢的精神在當代的發揚光大。可見,這部作品通過古今對照,寫出了黔江農村后繼有人的新風貌。
從農業互助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村土地流轉制,當代中國農村發生的這三次土地重大變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尤其是農村土地流轉制的推廣,加快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縮小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歐甸丘的《決戰武陵山——新華社記者貴州掛職扶貧記》敘述了大屯村大眾茶的崛起和竹產業的壯大,展現出依托傳統優勢、因地制宜的脫貧效果。盧志佳、楊俊江的《花茂沃土》描寫貴州遵義的花茂村由原來的“空殼村”到現代農業園的崛起的演變,生動地再現了第三次土地大變革帶來的巨變。作品用一定的篇幅描寫了近年來這個村莊傳統的陶器業的重新興起和古法造紙術的傳承與發揚光大,彰顯了老區人民因地制宜、立足優秀傳統文化謀發展的長遠之策。
在眾多的報告文學作品中,謝慧的《古丈守藝人》可謂一部描寫古丈縣茶人茶事的作品。古丈種茶、制茶的歷史悠久,古丈毛尖以其優良的品質聞名遐邇,歌曲《挑擔茶葉上北京》《古丈茶歌》更讓古丈茶葉家喻戶曉。好茶生長于優美的山地環境,更離不開制茶人的細心烘焙與技藝創新。這部作品追溯了古丈茶文化的歷史,并從清代以后沿襲至今的“斗茶”之風中探尋一代代古丈茶王的成長經歷,如數家珍般展現了他們傳承茶藝、不斷推陳出新的風采。經過茶王向春輝、張遠忠、二代茶人田麗、企業家吳曉瓊和來自“光大”集團的扶貧者李言志等的不斷探索,古丈茶葉完成了由自產自銷到產業化的華麗轉身,這既傳承了傳統的茶藝,又實現了茶農的增收。作品還從細節入手,描寫了古陽河茶莊的主人胡維霞的飲茶之道,寫出了茶人回歸自然的雅趣與佛家因果說的不謀而合。透過28位古丈人的故事,作品歌頌了茶藝傳承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大膽開拓的企業家精神。這樣的書寫不動聲色地將脫貧主題隱含在茶藝傳承和茶葉開發的故事之中,以小見大,呈現了時代巨變中古丈茶人默默堅守、推陳出新的精神,凸顯作家對故土的一片深情。
土地是農民得以立足的根本,而在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各種鄉土景觀,則是人類智慧的產物。武陵山區的鄉土景觀以自然山水為依托,分布在崇山峻嶺之中,蘊含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層層疊疊的梯田、古樸的吊腳樓,與起伏的山脊、幽深的峽谷、飛瀉的瀑布相映成趣,構成了人與自然共生的美麗景觀。“對鄉土景觀的認識可以加深人們對幸福感的理解,這種幸福來源于對其所處的自然和社會文化環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5]以紀實的方式再現武陵山區的鄉土景觀及其改觀的歷史,流露出作家的傳統文化情結與家園意識,有益于讀者認識武陵山區地域景觀的獨特性,尋找詩意棲居的家園。同時,“報告文學應當是站在社會生活的前沿,站在時代前沿的文學。作家并不是為了現實而現實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一種先進的,文明的,現代的思維、觀念和標準來認識和影響現實。是為了現實更加合乎人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而走向現實。”[6]可見,報告文學作家不能拘泥于現實,而要以現代意識審視現實。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奠定了鄉村文化的傳統,盡管鄉村沒有城市那樣發達的現代文明,它卻是許多人魂牽夢繞的精神家園。當然,鄉村不可能定格在某一個時代,在全球化時代,只有在傳統中推陳出新,才能創造出新的鄉村文明,留住綠水青山,重塑民族文化之魂。武陵山區脫貧攻堅的實踐證明:思想改造是脫貧的基礎。長期以來,農民固有的小生產者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早在20世紀40年代,趙樹理就看到了封建思想束縛下農民改造的艱巨性,到了21世紀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一些農民依然沒有完全走出舊思想的禁錮。因此,脫貧攻堅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改造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一些貧困戶的惰性思維。近期的報告文學描繪鄉村在脫貧前后的變化,集中呈現了武陵山區農民在政策的支持下窮則思變的奮斗軌跡,體現了一些干部深入農村、真抓實干的作風。有全景式的展示,如歐甸丘的《決戰武陵山——新華社記者貴州掛職扶貧記》,以作者自己的扶貧經歷為經,以當地干群的奮斗故事為緯,交織出一幅幅改天換地的時代圖景;有口述實錄式的情景再現,如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以十八個不同人物的口述實錄貫通起來,看以平淡,實則形成了歷史與記憶的疊加,自然而貼切;也有激情四射的詩意描繪,如羅長江的《石頭開花》,語言靈動而富于哲思,每一章講述一個人物自主創業的故事,中間穿插民謠、民間傳說、名人詩句,激活了敘事。在講完故事之后附加一則關于反貧困的隨想,層層深入,增添了作品的典型性與思辨色彩。這樣的書寫打破了傳統報告文學的結構模式,突出了審美性與思想性,顯得別具一格。因此,近期長篇報告文學的武陵山區脫貧攻堅書寫顯得多姿多彩,唱響了昂揚的新時代文學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