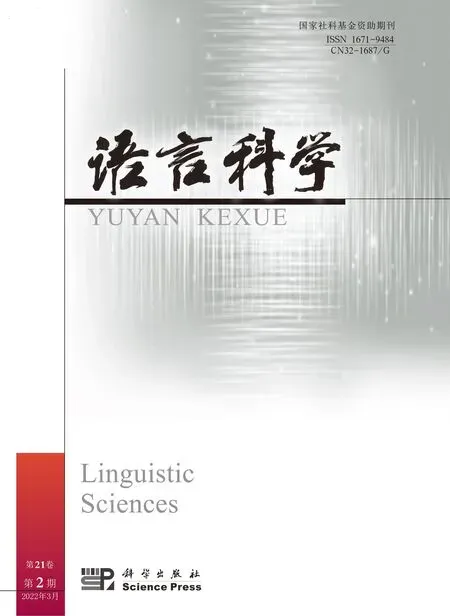異質語言特殊用法與語言接觸*
——以漢譯佛經中全稱量化詞“敢”之來源為例
龍國富 范曉露
1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北京 100872 2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湖南 長沙 410205
提要 中古漢譯佛經中“敢”有表全稱量化的特殊用法。關于其來源目前尚無定讞,有詞匯沾染說,亦有月氏語影響說。本文發現是譯師們將原典梵語中既表充分條件又表全稱的句式翻譯為“敢……皆”構式,產生全稱量化用法。“敢”吸收并承載了“敢……皆”構式的全稱量化義。其產生動因是因充分條件義和全稱量化義邏輯上相通,句式在梵文中有充分條件和全稱二義,則漢語為第二語言的外來譯者以為漢語“敢……皆”構式也可如此。語言特殊用法的產生在同質語言中往往受特殊語境及特殊句法結構影響,在異質語言中常常因語言接觸導致,“敢”表全稱量化用法很好地詮釋了后者。
1 研究現狀
以往研究發現中古漢譯佛經中“敢”表全稱量化用法。例如:(引自朱慶之1989;董志翹和蔡鏡浩1994:147-149;李維琦2004:434-435)
(1)佛告須菩提:“今日菩薩大會,因諸菩薩故,說般若波羅蜜,菩薩當是學成。”舍利弗心念言:“今使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自用力說耶?持佛威神說乎?”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便語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東漢支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
(2)于是秋露子念:“此賢者說明度道,自己力所?乘佛圣恩乎?”善業知其意而答曰:“敢佛弟子所說,皆乘如來大士之作。”(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一)
(3)須菩提知諸菩薩、大弟子、天人意之所念,語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說法、所出音聲、所可教授,皆是世尊大士之務。”(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二)
(4)如來道慧所入至處,莫不蒙安。敢佛弟子班宣經典,皆承如來威神圣旨,以入如來空法之身。(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五》)
(5)慧命須菩提知諸菩薩摩訶薩、大弟子、諸天心所念,語慧命舍利弗:“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教授,皆是佛力。”(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四十一)
上面這類用例中“敢”直接在名詞性成分前面,后面有“皆”與之配合使用。“敢佛弟子……皆……”成為構式,表全稱量化,相當于“所有佛弟子……都……”。例(1)大意為:所有佛弟子宣說法、成就法都是憑借佛的威力。例(2)為例(1)的同經異譯,其同經異譯還有:前秦竺佛念譯作“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姚秦鳩摩羅什譯作“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唐玄奘譯作“世尊弟子敢有宣說顯了開示,皆承如來威神之力”,宋施護譯作“世尊所有聲聞弟子,于諸法中若自宣說或為他說,一切皆是佛威神力”。此處“敢佛弟子……皆”“佛諸弟子敢有……皆”“世尊諸弟子敢有……皆”“所有聲聞弟子……皆”都是同義翻譯,對照可知,“敢”對其后名詞“弟子”進行全體稱量,具有全稱量化用法。
關于“敢”表全稱的來源,朱慶之(1989)認為是沾染“皆”詞義的結果,李維琦(2004:434-435)認為是受月氏語影響,研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小軍(2018)支持朱慶之“詞匯沾染”說。前人有關這一問題研究已取得很好的研究基礎,但還需做進一步探討。既然全稱用法“敢”源于其句法中“皆”詞匯沾染,那么其應屬于漢語內部演變,漢語中就應該有“敢”全稱用法,但是中土漢語中一直未曾有“敢”表全稱用例,只見于漢譯佛經中,或許還需觀察是否有佛經翻譯的影響。
本文試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利用梵漢對勘研究漢譯佛經中“敢”表全稱之來源,分析佛經翻譯是否對“敢”的語義產生影響。
2 漢譯佛經中“敢”的用法
根據功能、語義和語境,中古漢譯佛經中“敢”的用法可分兩類:一類表示膽敢義,用于下對上冒犯的語境中;另一類表示全稱,用于某行為符合社會道德良俗規范的語境中。
2.1 表示膽敢義
在以下例句中“敢”表膽敢義:
(6)有外善內穢,違佛清化,即權令布敕曰:“敢有奉佛道者,罪至棄市。”(三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四)
(7)王善鹿之言,喜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后恣鹿所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同上)
這一類“敢”做意愿動詞,后面有動詞“有”,“敢有……者”即“膽敢有……的人”。此類結構具有構式義,用于將來時表示充分條件假設,其構式義為:只要有這樣的人,就會被處以某種罰責。此時“敢”所稱量的人是以卑觸尊,不自明,即用于下對上冒犯的語境中。
2.2 表示全稱義
在以下例句中“敢”表示全稱義:
(8)辯積曰:“化其中人敢見我等皆得辯才,使諸伎樂轉共談語。”超度無虛跡曰:“令其中人吾等目見,皆使究竟至于無上正真之道。”(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離垢施女經》卷一)
(9)十一法寶者。十方諸佛三千日月。敢有來聽經者,悉得佛莂,即住虛空中亦如是。(東晉祇多蜜譯《寶如來三昧經》卷下)(1)“莂”指佛對弟子授未來成佛之記。
(10)大迦葉曰:“愿城中人施我食者,一切皆使得無盡福至無為度。”須菩提曰:“愿城中人敢覩光明,以是緣報,皆得生天及在人間,然后逮得無為之法。”(西晉竺法護譯《佛說離垢施女經》卷一)
(11)十一者他方剎土,敢有來聽經者,悉令得決。(西晉竺法護譯《無極寶三昧經》卷下)(2)據《開元釋教錄》記載,西晉懷帝永嘉元年三月三日由竺法護譯出本經。
(12)眾有所志,敢有所求,皆令得愿。(西晉竺法護譯《無言童子經》卷下)
例(8)中“化其中人敢見我等皆得辯才”指被勸化出家的人凡是見到佛都能得到辨析佛法奧義的才能;例(10)中“愿城中人敢覩光明,以是緣報,皆得生天及在人間”指愿所有能見到佛之光明的三千大千佛界中的人,因此緣報都能轉生天道和佛所住之地;例(11)中“敢有來聽經者,悉令得決”即凡有來聽經者都得決疑。這類“敢”均表示對后面中心名詞的全稱量化。
“敢”用于“所”字結構前,也表示對所屬名詞成分的全稱。(朱慶之 1989)例如:(引自李維琦 2004)
(13)其明智者,志愿堅強,未曾違失,往古所曉,為一切智,精進殷懃,終不處于興廢異乘,奉行精進,常無放逸,敢所遵修,心不怯弱。(西晉竺法護譯《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14)善權闿士,敢所生處,其所住處,不計吾我,未曾自輕。(西晉竺法護譯《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15)無能憎嫉而嬈害者,以何等故無能嬈者,其行治業莫能逮故;有所建立無能誹者,所以莫能譏謗者何?敢所興造無根原故。(西晉竺法護譯《阿差末菩薩經》卷上)
“敢有”即“所有、一切”,后面接名詞。例如:(引自朱慶之 1989;董志翹和蔡鏡浩1994)
(16)如我有時與諸天共于天上坐,持異特座,乃至自我座,敢有天人來至我所承事我,我未及至座所,我不坐上時,諸天人皆為我坐。(東漢支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二)
(17)眾生之類,敢有見知,咸發無上正真道意。(西晉竺法護譯《漸備一切智德經》卷五)
(18)眾人所志,敢有所求,皆令得愿,各各得所,不失其僥。(西晉竺法護譯《無言童子經》卷下)
(19)群生品類,敢有形者,隨其色貌,皆現其前,無不見像。(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如來興顯經》卷二)
譯經中“可”能用作“所”,有“敢可”的用例,相當于“凡所”。例如:(引自朱慶之 1989;董志翹和蔡鏡浩 1994)
(20)阿差末言:“菩薩念往古知不可盡,敢可憶念,思逮了本,群黎之類,皆悉荷蒙。”(西晉竺法護譯《阿差末菩薩經》卷五)
(21)如來一切,所可分別,悉至解脫,敢可說者,悉誠諦句。(西晉竺法護譯《持心梵天所問經》卷一)
(22)逮覩諸佛無所罣礙,敢可遵修,皆成如來清凈之行。(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七之《寶髻菩薩會》第四十七之一)
(23)如是,天子!敢可成就至于大化,皆由戒立。(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下)
以上例子中的“敢可”語義指“所有”,與“皆”“悉”相呼應,表示此范圍之內不論何人何事都為同一情況。此時“敢”所稱量的人是以卑敬尊,即用于主體非常自明之語境。中土文獻未見“敢”表全稱的用法,而在譯經中使用頻率較高,共調查到200余例。如東漢支讖3例,其中《道行般若經》中2例,《兜沙經》中1例。三國支謙《大明度經》1例,西晉竺法護11例,見于《離垢施女經》《無言童子經》《大哀經》《無極寶三昧經》《大寶積經·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五》《如來興顯經》《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魔逆經》等。從歷時角度看,西晉之前的譯經中全稱量化詞“敢”用得多,東晉之后“敢”的使用頻率降低。下文將討論全稱量化詞“敢”的來源問題。
3 “敢”表全稱用法之來源
如果“敢”表全稱用法來源于情態動詞“敢”,那么為什么全稱用法來源于情態義?從漢語自身的演變和佛經翻譯兩個方面考察可見一斑。
3.1 “敢”自身演變
首先,漢語中的“敢”自身的語義和句法演變可分兩個階段:
1)用于否定性單句“不敢+V”中,表示不敢做某事,“敢”作情態動詞。
春秋時期,“敢”本指勇于進取,有勇氣,有膽量。《說文》:“敢,進取也。”由此“敢”引申為情態動詞,作情態動詞時多用于否定句中。例如:
(24)何斯違斯?莫敢或遑。(《詩·召南·殷其雷》)
(25)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左傳·隱公五年》)
例(24),程俊英和蔣見元(1999:46)注曰:“為何此時違去此地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有閑暇也。”例(25)的意思是“叔父對我有怨恨,我不敢忘其忠誠”。
2)用于充分條件復句,多用于膽敢做某事者都會受到處罰的語境中,“敢”仍作情態動詞。
秦漢開始,“敢”發展為用于肯定式,并出現在復句“敢VP者,(皆)VP”中。前小句表全稱概念,指“膽敢有做某事的人”,“敢”仍為情態動詞。后小句表結果,指“都會受到某一處罰”,多有“皆”與前小句相配合。復句意義表示膽敢有做違背道義禮制之事的人,必將受到譴責或處罰。例如:
(26)敢為詐偽者,貲二甲。(《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鈔》)
(27)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史記·吳王劉濞傳》)
(28)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論衡·語增篇》)
(29)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太平經·斷金兵法》)
表充分條件“敢VP者,(皆)VP”句式也見于中古譯經中,且數量呈增加趨勢。例如:
(30)世間人民,不肯為善,欲作眾惡。敢有犯此諸惡事者,皆悉自然當更具歷入惡道中。(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無量清凈平等覺經》卷四)(3)此經舊題西晉竺法護譯,后來大正藏歸入東漢支讖譯,而日本學者辛嶋靜志主張是三國吳支謙譯(辛嶋靜志 2011),本文采納此觀點。
(31)敢有犯者,罪皆直死。(三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六)
(32)敢有乞者,皆受誅罰。(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三)
這類用于肯定句的“敢……皆”格式,其特點有二:
1)在語義上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理解為充分條件義,指“膽敢有這樣人,皆受處罰”,二是可以理解為全稱量化義,指“凡是這樣的人,皆受處罰”。例(28)既可指膽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都須前往守尉衙門集中燒毀,也可指凡是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都須前往守尉衙門集中燒毀。二者語義一致。
2)在句法上,“敢”用于條件復句,前小句“敢有……者”表充分條件,后小句表示在此條件下受處罰的結果,有副詞“皆、悉”配合前小句的充分條件。此時“敢VP”的語義范圍還只局限于膽敢做違背道義(的人),且“敢”后面只能跟動詞,故“敢”還應看作表意愿的情態動詞,相當于“膽敢”。“敢VP者,皆VP”結構在漢至晉這一時期是常式,表達“膽敢有……者,都受……處罰”的句式義,可將“敢……皆”看作新構式。需注意的是,“敢VP者,皆VP”構式中“敢”隱含有“凡”的語用義,且構式具有任指的意義,這為“敢……皆”進一步演變為全稱奠定了語義和句法基礎。但是在中土漢語中,“敢”的語義沒有再進一步演變為全稱用法。
3.2 佛經翻譯觸發“敢”產生全稱用法
東漢至南北朝時期漢譯佛經中,“敢……皆”迅速發展,其表現有四:
1)“敢……皆”使用語境擴大,可用于稱贊,多用來稱贊如來顯威、眾生成佛等,具體如用于指所有佛弟子說法都秉承佛祖威力,用于指所有能見到佛祖的人都能得辯才,用于指所有能見到佛光明的人都能得無為之法,用于指所有菩薩所求都令得愿,用于指所有眾生成佛都因戒立等等。
2)“敢……皆”構式產生新的構式義,表示全稱用法。“敢”用于名詞或名詞性成分前面,吸收并承載了“敢……皆”構式的全稱量化義,出現表全稱量化的用法。
3)“敢……皆”構式由原來的復句降級為單句,“敢”的句法環境由復句縮減為單句,用于“敢NP皆VP”構式,名詞性成分“敢NP”作主語,“皆VP”作謂語。此時“敢”緊臨名詞短語,表示該名詞的全稱。“敢NP皆VP”構式表達“凡NP,都VP”句式意義,可把“敢NP皆VP”看作全新的構式。
4)這類“敢……皆”構式不見于本土文獻,只見于中古漢譯佛經中,且使用頻率相對較高,達200多例。例如:
(33)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廩虛竭。”公時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即施與。”(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三)
(34)如我于諸天中而獨持坐,或時不在座上,敢有天人來到者,皆承事為座作禮,所受教處,便即而去。(前秦曇摩蜱共竺佛念譯《摩訶般若鈔經》卷二)
(35)我等凡劣欲有所問,不蒙如來神力加助不能發問,是故我今敢有所問,當知皆是如來神力。(東晉法顯譯《大般泥洹經》卷二)
(36)復能得入身諸支節毛孔定意,亦知十方眾生宿命,甚奇甚特不可思議,唯愿世尊,敢有所問,若見聽者,乃得陳說。(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經》卷七)(4)另有“佛所住處皆悉履行。不染法界去吾我想。即從座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欲有所問。若見聽者,敢有所陳。”(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經》卷九),可參照例(36),此段中的“欲有所問”宜為“敢有所問”,“敢有所陳”宜為“欲有所陳”。指佛法所有的問題,只要有聽的人,佛就會解答。
這類“敢”表示某一范圍內的全稱,與全稱詞“皆”相呼應。如例(33)“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即施與”理解為國王立即施舍所有來乞討的人;例(34)“敢有天人來到者,皆承事為座作禮”理解為所有來的天眾都會禮敬佛祖;例(35)“我今敢有所問,當知皆是如來神力”指我今一切所問的佛法都是因為如來的力量;例(36)“敢有所問,若見聽者,乃得陳說”指一切所問的佛法,若只要有眾生愿聽,如來就會宣講。“敢”這類用法不見于本土文獻,只見于中古漢譯佛經中,有可能是受梵文佛經翻譯影響。
下面論證表明用于全稱的“敢”受佛經翻譯影響,先看下面對勘。例如:(引自辛嶋靜志2011:2-3)
(37)a.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便語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東漢支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一)
c.現代漢語:此時須菩提知曉舍利弗心里的想法,便對舍利弗說:“所有佛弟子所解說的法、所成就的法,都要依靠佛的威力。”


4 全稱量化詞“敢”產生的動因
“敢”從意愿動詞發展為全稱量化詞,這是漢語一種比較特殊的語義演變模式。根據其產生的過程,“敢”這一演變模式產生的動因主要有語境吸收、語法復制和類比三個方面。
4.1 語境吸收
語境吸收是引發“敢”演變為全稱用法的動因。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是指詞匯所在結構式中的主體詞意義發生語法化以后,成分關系重新調整組合,吸收結構式意義,產生新的語法意義。(Bybee等 1994:230-235)這是由于在語法化的后期,主體詞的初始意義已經大大削弱,詞匯意義已經虛化,無力抵抗結構式意義,被聽話人重新認知。(Bybee等 1994:295—296)在“敢”演變的后期,“敢”從意愿義演變為全稱義,正是“語境吸收”這一動因在起作用的結果。我們發現,中古漢譯佛經中,“敢VP者,(皆)VP”構式擴大到符合社會道義倫理的范圍,開始表達全稱意義,“敢”字開始趨向虛化。只要此時廣泛地出現“敢NP,(皆)VP”表全稱的單句用法,那么該構式便會表現出全稱的功能。“敢”原有的“意愿”義已趨淡化,吸收并承載“敢……皆”構式的全稱量化義。為了便于表述,可用以下例句來表示“敢”語境吸收的演變過程:
(38)a.敢有乞者,皆受誅罰=膽敢有乞討者,皆受誅罰(膽敢)
b.敢來乞者,皆悉施與=凡敢來乞者,皆悉施與(膽敢,隱含有“全稱”義)
c.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教授,皆是佛力=凡佛弟子所說法,所教授,皆是佛力(全稱義)
例(38)a中,“敢”用于充分條件復句。該條件為不合乎道義的行為,結果受處罰,“敢”表意愿。例(38)b中,“敢”既可以認為用于單句也可以認為用于復句,因為充分條件義與全稱量化義邏輯關系緊密。條件介乎道義與非道義之間,結果受關注,既可理解為“膽敢來乞者都施與”又可理解為“凡來乞者都施與”,因此既表充分條件也表全稱量化。例(38)c中,“敢”用于單句“敢NP者(皆)VP”結構式,內容符合道義禮制,結果受到社會期待,“敢……皆”表全稱。該分析表明,一旦符合道義禮制行為的“全稱量化”構式意義出現,“敢”便會吸收表全稱的構式義,全稱量化功能就會隨之產生。
可以看出,“敢”的語境吸收這一動因需要考慮到的因素有三:其一,主體詞的詞義虛化作為前提。只有“敢”的詞義虛化,它才有可能吸收結構義,結構義也才會對“敢”的詞義變化造成影響。其二,“敢”進入這種句式,只是語境吸收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譬如,同樣的句法位置,同樣的意愿動詞“欲”雖然也進入過這種句法組合中,組成過“欲……者,皆”這樣的句法形式,但沒有演變為全稱用法。其三,結構義的作用至關重要,它對詞義的影響很大。“敢”字由于其自身無法虛化為全稱用法,因此需要對表全稱的結構義進行吸收,才能產生出全稱用法。
4.2 語法結構復制
“敢”在中土漢語中未能產生全稱用法,有可能是語言接觸對“敢”的影響。根據Heine 和Kutava(2005:47-60)的研究,兩種語言發生接觸,可以依據使用頻率、語境和意義三個方面的參數,判斷一個語言單位是否因為語言接觸而產生。即復制語中該語言單位的使用頻率是否增加、語境是否擴大、新的意義是否產生。佛經翻譯屬于語言接觸現象,下面檢討漢譯佛經中“敢”的三個使用參數是否發生變化。
1)“敢”使用頻率增加。
復制語中存在一種在過去很少或低頻的使用模式,說話者用來復制模型語中被認為意義等價的使用模式,因模型語的使用模式頻率高導致復制語中使用頻率迅速增加(Heine和Kutava 2005:47)。表1是“敢”用于充分條件“敢VP者,VP”構式和全稱量化“敢NP者,VP”構式時,與同期中土文獻中使用頻率的對比。

表1 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中“敢”用于充分條件句和全稱量化句的頻次
表1中“28部譯經”是指許理和(1977,1991)確定的東漢譯經。“竺法護和羅什譯經”是指二位有代表性口語性比較強的翻譯佛經,“南北朝譯經”是指元魏吉迦夜、蕭齊求那毗地、元魏慧覺、劉宋求那跋陀羅等。(6)竺法護譯經有《正法華經》《賢劫經》《持人菩薩經》《光贊般若經》《方等泥洹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生經》《六度集經》《摩訶般若鈔經》《光贊般若經》《方等泥洹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羅什譯經有《妙法蓮華經》《自在王菩薩經》《大莊嚴論經》《眾經撰雜譬喻》《十誦律》《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三昧經》《十住毗婆沙論》等。南北朝譯經: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蕭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元魏慧覺等集《賢愚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等。從表上統計的數目對照來看,在東漢、兩晉、南北朝、隋代各個時期,漢譯佛經與中土文獻比較,漢譯佛經中“敢”用于表全稱“敢NP者,VP”格式時,只見于譯經,所調查的語料中共有29例表全稱用法。而同期中土文獻一例也沒有。表全稱“敢NP者,VP”格式已經固定化為一種新的格式,相當于漢語中的“凡NP皆VP”。
2)“敢”語境擴大。
中土文獻中“敢”只用于違背君權和封建制度禮制會受到處罰的語言環境,佛經翻譯促成“敢”使用語境擴大,“敢”擴大到眾生修道成佛、贊美佛法力無邊的新語言環境,新的語境具體有以下諸多方面:“敢”用于指所有能見到佛祖的人都能得辯才,用于指所有能見到佛光明的人都能得無為之法,用于指所有菩薩所說的法、所成的法都是秉持佛的威力,用于指所有佛弟子所說的法都是憑借如來的佛法,用于指所有向大眾宣說的法、音聲和所教授的內容都在完成如來的任務,用于指所有來聽經的的人都可以解決心中之疑,用于指所有來聽法的人都會得到佛的授記等。我們調查,漢譯佛經中“敢”共有60余處用于新的語境,且都用在支讖、安世高、支謙、竺法護、鳩摩羅什、法顯、佛陀跋陀羅等一些漢語語言能力強的翻譯家作品之中,這說明“敢”的全稱用法得到當時翻譯家的普遍認同。
3)“敢”產生新的意義。
佛經翻譯觸發“敢”的使用頻率增加,頻率增加引發語境擴大,語境擴大又引發功能變化,產生新的意義,由意愿動詞擴大到全稱量化詞。“敢”的句法環境由充分條件“敢VP者,(皆)VP”擴大到全稱量化“敢NP者(皆)VP”,“敢”所在句法由復句降級為單句,“敢”后邊的修飾語由動詞性成分變成了名詞性成分,“敢NP”作句子的主語。“敢NP者(皆)VP”可看作新構式,其意義表示所有NP都是VP,表達一種全稱的概念。“敢”吸收并承載了“敢NP者(皆)VP”構式義,產生全稱量化義。
以上論證表明表全稱的“敢”受佛經翻譯的影響,那么佛經翻譯又是如何影響的。先看下面的對勘:
(39)a.敢有天人來至我所,承事我。我未及至座所,我不坐上時,諸天人皆為我坐。(東漢支讖譯《道行般若經》卷二)
c.現代漢語:所有天人來到我身邊供奉我。當我還沒有到達法座旁、沒有坐上法座時,所有天人就已為我準備了法座。

4.3 “凡……皆”結構的類比
朱慶之(1989:44-47)認為,“敢”有“凡”義的原因,還受“凡……皆”一類組合類比的影響。調查發現,戰國秦漢時期,表全稱的“凡……,(皆)……”格式大量使用,《莊子》18例,《荀子》57例,《墨子》23例。例如:
(40)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墨子·尚同中》)
(41)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訴,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致士》)
“敢……(皆)……”受到廣泛使用的“凡……(皆)……”的類比,產生表全稱的“敢……(皆)……”用法,使用頻率上升。
總之,“敢”表全稱用法產生的動因涉及內因外因兩個方面,內因主要是語境吸收,外因則是結構復制,同時語言使用環境中的類比也對其形成產生一定的影響。
5 結語
綜上所述,漢譯佛經中全稱量化詞“敢”是在“意愿”的單句“敢VP”的基礎上,為滿足語義表達復雜化的需要,向后延伸形成充分條件復句“敢VP者,(皆)VP”格式,強調所有違背社會道義的人都會受到處罰。在佛經翻譯中,因語境擴大,用于強調所有受教化者即得成佛的威力都在于佛,由此縮短成單句“敢NP者(皆)VP”。“敢”經歷了由單句到復句再到單句的發展過程,其中由單句到復句是為滿足語義表達明晰化的需求而增加了一個表結果的成分,然后由復句到單句即從松散結構到緊密結構的縮略過程,佛經翻譯對表全稱“敢”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