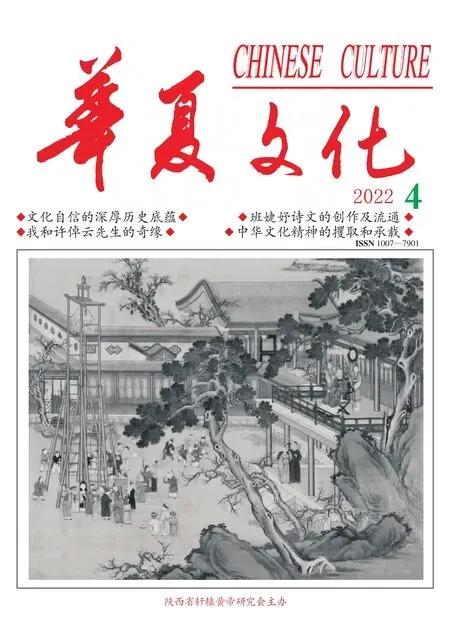文化自信的深厚歷史底蘊
□張豈之
2016年5月17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說:“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段論述是關(guān)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在精神的總概括,也是我們對待社會主義先進(jìn)文化的基本信念。
一、文化自信是對中華文明史深刻認(rèn)識的體現(xiàn)
中華文明有5000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這是我們關(guān)于文化自信的堅實立足點和出發(fā)點。眾所周知,陜西省黃陵縣有黃帝陵,歷代在這里祭祀人文初祖黃帝。2015年2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到陜西視察工作時指出:“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biāo)識。”對此加以闡發(fā),使更多的人了解,從而建立堅實的文化自信基石,這是十分必要的。
“文明”一詞不是外來語,《尚書·舜典》中的“睿哲文明”,指治國理政者應(yīng)當(dāng)具有文明的美德。唐代孔穎達(dá)疏解釋說:“經(jīng)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在中華歷史文獻(xiàn)中對“文明”的贊美詞很多。與“文明”相對的是愚昧野蠻,由此產(chǎn)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論,這一直是中華兒女熟記于心的箴言。
我國歷史學(xué)家和考古學(xué)家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有一種看法,認(rèn)為中國從原始社會進(jìn)入文明社會,建立國家的時候,保留了氏族血緣關(guān)系,形成了“家國一體”的模式,走了與西方古希臘不同的發(fā)展道路。
二、中國的文化血脈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產(chǎn)生了“諸子百家”,據(jù)漢代司馬談的看法,其中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漢代史學(xué)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諸子劃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nóng)、小說十家。
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百家爭鳴”,有其歷史條件。戰(zhàn)國時代,“士”這個階層活躍起來,他們中有些人是從貴族中分化出來的,有些人則出身于平民階層。“士”有參與政治的權(quán)利,其中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學(xué)術(shù)活動。這種古代社會的變動促進(jìn)了戰(zhàn)國時期學(xué)術(shù)的繁榮。
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著重論述關(guān)于“仁”的思想,將“仁”解釋為“愛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論語·衛(wèi)靈公》),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論語·雍也》)。孔子認(rèn)為,在“君子”(有道德修養(yǎng)的人)的生命中,恪守道義是必不可少的。君子為道義而活,非為富貴而生,這些才體現(xiàn)出君子的人生價值之所在。孔子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早論述人生價值觀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文化自信表現(xiàn)在他一生為實現(xiàn)人生價值而奮斗的事跡上。
秦漢之際有一部書,名《禮記》。《史記·孔子世家》說它是孟子的老師子思的著作。后來,《禮記》中的一篇《中庸》受到唐朝思想家、文學(xué)家韓愈的推崇。南宋時理學(xué)家朱熹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將《禮記》中的《大學(xué)》、《中庸》與《論語》、《孟子》編在一起,被稱之為“四書”。朱熹為“四書”作注,稱之為《四書章句集注》,對元明清三朝思想文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中庸》中的一個核心理念,稱之為“誠”。從自然界看,“誠”是四季、晝夜的更替,按天道規(guī)則運行,君子與此相應(yīng),按規(guī)矩做人辦事,不得妄為。這也就是說,君子在自尊、自信、自律、自省上應(yīng)有所建樹。為此,《中庸》強調(diào)君子應(yīng)“博學(xué)之”(廣博地學(xué)習(xí))、“審問之”(詳細(xì)地向人請教)、“慎思之”(周密地思考)、“明辨之”(明確地區(qū)別是非善惡)、“篤行之”(切實地身體力行,知行合一)。
孫中山先生贊賞《中庸》上述五種學(xué)習(xí)方法,曾經(jīng)手書贈給廣州中山大學(xué),希望師生們以此為學(xué)習(xí)的座右銘。
先秦諸子中對自然科學(xué)研究最廣泛、深入的是墨家。墨子是墨家的創(chuàng)立者,他和他的后學(xué)建立起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嬻w系,并將它應(yīng)用于自然科學(xué),對時空、光學(xué)、力學(xué)、幾何學(xué)等方面的問題,用邏輯語言加以分析、概括,體現(xiàn)了春秋末期科學(xué)家和能工巧匠們的創(chuàng)新思路。
墨子主張實行賢人政治,使社會上的賢良之士增多,辦法是“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墨子·尚賢上》),給賢良之士以豐厚的物質(zhì)待遇,高貴的社會地位,信任、敬重他們的才能,表彰他們的成績,形成鼓勵賢良之士成長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這樣賢人就會越來越多,用他們?nèi)ブ螄蜁@出成效來。
墨子的文化貢獻(xiàn)集中表現(xiàn)在他為中國古代自然科學(xué)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學(xué)派后來被中斷,未能傳承下去,但墨家的自然科學(xué)理論與“尚賢”的文化思想被后代繼承發(fā)揚。
哲學(xué)是時代的反映、民族文化的靈魂。關(guān)于“天道”與“人道”相互關(guān)系的研究,是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老子創(chuàng)立的道家學(xué)派深入研究“天道”與“人道”的相互關(guān)系,構(gòu)筑了完整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哲學(xué)開創(chuàng)研究的標(biāo)志性成果。
在老子哲學(xué)中,“天道”受到贊揚,而“人道”則遭到貶損。在他看來,“道”演化為天地萬物,沒有神力,沒有矯飾,自然而然。《老子》書(又名《道德經(jīng)》)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jīng)》第二十五章)“天道”不爭,不言,不驕,沒有制物之心,像無形的巨網(wǎng)廣大無邊,雖稀疏但沒有任何遺漏,將一切事物都囊括在其中。與此不同,“人道”便顯得自私、不公。于是問題便產(chǎn)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應(yīng)效法“天道”。
老子關(guān)于“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了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絢麗畫卷,反映出哲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毋庸諱言,老子哲學(xué)用自然的“天道”否定“人道”自身的特點,在理論上有其偏頗的一面。不過,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dāng)封建社會的治理者在一定范圍內(nèi)將老子哲學(xué)的某些方面加以實踐的時候,確實有過若干成效。
三、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特色
在中華文明中,政治文明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國歷史進(jìn)入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后,一種新的政治體制產(chǎn)生,這就是中央集權(quán)制。這反映在逐漸用郡縣制代替分封制上。春秋時期,秦、楚等國設(shè)立縣和郡,作為新的行政建制。縣在中心區(qū)域,郡在邊遠(yuǎn)地區(qū)。郡縣的官員不再是世襲領(lǐng)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員直接管理。
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在國家制度中由地域關(guān)系取代血緣關(guān)系,使早期的部族國家轉(zhuǎn)化為疆域國家;二是國家管理人員由職業(yè)官員取代了世襲領(lǐng)主。
戰(zhàn)國時另一個重大變化是:逐漸形成了區(qū)域性的集權(quán)制度,其中以秦國最為典型。從秦孝公到秦王嬴政,建立起由君主執(zhí)掌大權(quán)、卿士執(zhí)行的制度,實行“耕”“戰(zhàn)”并重的法家政策,為秦國統(tǒng)一六國奠定了基礎(chǔ)。
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大業(yè),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大一統(tǒng)國家,意義重大。
一個王朝,在治國理政的政治設(shè)施中,最主要之點是:如何選拔輔佐皇帝治國的百官臣僚。這在中國歷史上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漢代以察舉(即推薦官員)為主體的選官制度,解決了自戰(zhàn)國以來軍功制和養(yǎng)士制不適應(yīng)治理國家的問題,比較成功地實現(xiàn)了由奪天下到治天下的轉(zhuǎn)變。
隋、唐時期在官吏的選拔上有新的進(jìn)展,創(chuàng)建了科舉制。這種制度改變了前代選官制度中的權(quán)力下移之弊,適應(yīng)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需要。而且,科舉制力求將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結(jié)合為一個整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官員隊伍的知識化,使社會思想與統(tǒng)治思想相結(jié)合,在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方面有明顯的作用。因此,科舉制度不僅得到唐代統(tǒng)治者的重視,而且得到以后各個王朝的重視,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建設(shè)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中國古代的政治、法律、選官制度,經(jīng)過長期的歷史積淀,形成了有特色的內(nèi)容,反映了它們在歷史演變中能夠修復(fù)、完善并自我發(fā)展,這個問題值得進(jìn)一步研究。
四、文化自信不能離開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融合這兩個支柱
中國歷史上盡管有過戰(zhàn)亂和分裂,但統(tǒng)一始終是主流。在國家統(tǒng)一的大背景下,中華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團(tuán)聚和統(tǒng)一的過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各民族經(jīng)過遷徙、雜居、通婚和各種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學(xué)習(xí),在血統(tǒng)上互相融合,逐漸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別是近代,中華各民族共同反對外國侵略者,為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fù)興而奮斗,這個共同的政治信念極大地加強了民族間的團(tuán)結(jié)。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結(jié)果。早在先秦時期,我國有華夏、東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團(tuán)。華夏族是在夷夏融合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
漢族能夠在歷史上起主導(dǎo)作用,不僅是因為它人口眾多,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有比較先進(jìn)的生產(chǎn)方式、比較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和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進(jìn)行統(tǒng)治的時刻,比如有鮮卑(北魏)、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和滿(清)。他們在進(jìn)入中原以前,都處于比中原漢族較低的發(fā)展階段,因此當(dāng)他們進(jìn)入中原以后,不僅未能改變漢族原有的生產(chǎn)方式和文化積淀,反而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由此進(jìn)一步推動了漢族文化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fā)展。
中華文明有什么特點?中華文明是人文文明與政治文明的結(jié)合。這一點,英國史學(xué)家湯因比和日本學(xué)者池田大作的對話集《展望21世紀(jì)》一書中有這樣的評論:“(中國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tuán)結(jié)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上、文化上統(tǒng)一的本領(lǐng),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jīng)驗。”(〔日〕池田大作,〔英〕阿·湯因比著,荀春生、朱繼征、陳國梁譯:《展望21世紀(jì)——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第283-284頁)
戰(zhàn)國時代,在中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著差異。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有匯合地域文化的理想,沒有成功。漢并天下以后,到漢武帝執(zhí)政時期,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多次戰(zhàn)爭,地方分裂勢力基本被肅清,而地域文化大體上完成了匯合的歷史過程。與這個總的形勢相適應(yīng),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國策,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文化共同體才真正形成。這個文化共同體以儒學(xué)為主導(dǎo),并沒有阻礙其他學(xué)派思想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會通問題。在唐、宋時期,儒、道、釋的融合會通,將中華文化推進(jìn)到一個新的階段,于是產(chǎn)生了宋代理學(xué)。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如泉之水,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因為它形成了一條獨特的自我創(chuàng)新之路。它始終以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吸取域內(nèi)和域外的文化,能夠在會通的基礎(chǔ)上,消化、吸收各家的理論成果。這正如莊子在《天下篇》所說,諸子百家的觀點,都是宇宙真理某些方面的表現(xiàn)。雖然各家各派立論的側(cè)重點不同,表述的方式有別,但都是對于世界的探索,有助于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rèn)識。這也正是儒家“和而不同”文化觀的體現(xiàn)。
五、中華文明的傳承發(fā)展與文字
中華文明的形成、傳播、發(fā)展與文字有密切的關(guān)系。中國文字源遠(yuǎn)流長,起源于模仿自然、圖畫紀(jì)事、表情達(dá)意的需要,并誕生了別具特色的符號系統(tǒng)。以漢字為例,經(jīng)過長期的演變與實踐,逐漸形成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zhuǎn)注與假借六種造字法與用字法,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獨特的人文情懷。漢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為統(tǒng)一漢字書寫,采用小篆。各地鄉(xiāng)音不同,但書寫的文字相同,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fā)展才有了保證。
秦朝“書同文”的文字統(tǒng)一政策影響深遠(yuǎn),雖然后代又有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文字書寫的變化,但秦統(tǒng)一文字則是一個歷史性的轉(zhuǎn)折點。文字的統(tǒng)一有效地促進(jìn)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國家政令的暢通,對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和多民族的融合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統(tǒng)一,與各地方言鄉(xiāng)音并存,在同中保留有特色的差別,體現(xiàn)了文化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結(jié)合。
文字的相對穩(wěn)定,對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做出了獨特貢獻(xiàn)。因為文字(特別是漢字)具有象形與表意的特點,在表達(dá)人文精神以及人與萬物關(guān)系方面簡明扼要、形象生動,即使是時過境遷,后來者在閱讀古籍時也同樣可以由文辭而把握其道理與智慧,將世代積累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孔子對文字很重視,強調(diào)“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左傳·襄公二十年》),思想要傳播久遠(yuǎn),需要有文采的語言文字記載。古人所強調(diào)的“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見文字在文明承傳中的重要意義。古代有“文以載道”“文以化人”的傳統(tǒng),顯示了文化典籍和語言文字在傳承思想、培育人才與改善社會風(fēng)氣中的積極作用。
豐富的語言文字,需要有相關(guān)的工具書幫助人們掌握。東漢許慎撰寫的字書《說文解字》,通過剖析文字構(gòu)件(文)來解說字義,對規(guī)范字形、字音與字義做出了貢獻(xiàn)。清代研究《說文解字》甚至成為顯學(xué),代表性著作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漢之際的詞書《爾雅》,保留了大量多學(xué)科(特別是博物學(xué))知識,為豐富漢語詞匯的語言形式、融會溝通詞語的意義建立了基礎(chǔ),經(jīng)過魏晉學(xué)者的努力,成為閱讀“五經(jīng)”的重要準(zhǔn)備,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經(jīng)”中。
獨特的語言文字,風(fēng)格多樣的書寫形式,形成了符合人們審美需要和表達(dá)人們審美感受的書法藝術(shù),它與單純的具有社會實用功能的交際工具不同,是以藝術(shù)形式表達(dá)藝術(shù)家的思想、修養(yǎng)、愛好與情感,“籠天地于形內(nèi),挫萬般于毫端”(陸機:《文賦》)。因此,不同時期的書法本身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觀、歷史觀與人生觀,它既受到歷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又間接地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哲學(xué)的豐富內(nèi)涵,如易學(xué)的陰陽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學(xué)說、道家的相反相成觀念、禪宗的頓悟靜修主張等。書畫同源,中國書法的基本觀念和表現(xiàn)方式,對獨特的中國國畫(水墨畫)的形成影響很大,它們共同成為中華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寶。
在某種意義上,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tǒng),促進(jìn)了中華文化的古今傳承,也促進(jìn)了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和文化交流。
中華文化對域外文化的研究,不僅重視語言文字的翻譯,而且還側(cè)重于思想內(nèi)容的介紹與闡釋,注意從整體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為中華思想文化的有機構(gòu)成部分。比如,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是從整體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公元13世紀(jì)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許多教派和經(jīng)典仍然可以在中國找到它的源頭。這是中國佛教學(xué)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結(jié)果,對東方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貢獻(xiàn)。
六、中華典籍的重大文化意義
中國封建社會,一般說來,政教分離,沒有形成像西歐那樣的宗教黑暗時期。當(dāng)時占主導(dǎo)地位(即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是儒家的經(jīng)學(xué)。它為不平等社會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點。我們可以看到,皇權(quán)統(tǒng)治以經(jīng)學(xué)為武器,而民間亦以經(jīng)學(xué)作為維系社會關(guān)系(含宗法關(guān)系、人際關(guān)系等)的價值準(zhǔn)則。歷代的官方版刻經(jīng)籍、社會啟蒙讀本、民間鄉(xiāng)約村規(guī),在思想觀念上都同經(jīng)學(xué)有關(guān)。西漢時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東漢時“五經(jīng)”加《孝經(jīng)》、《論語》成“七經(jīng)”。唐時《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加上《周易》、《尚書》、《詩經(jīng)》,成為“九經(jīng)”;后又加《論語》、《孝經(jīng)》、《爾雅》,成為“十二經(jīng)”。宋代,“十二經(jīng)”加《孟子》,形成“十三經(jīng)”。
儒家的經(jīng)書從“五經(jīng)”到“十三經(jīng)”,是因為社會演進(jìn)的需要,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血脈,而不致發(fā)生敵對的沖突。儒家經(jīng)書既維護(hù)社會尊卑貴賤的分野,又調(diào)節(jié)個人的喜怒哀樂。儒家經(jīng)典所體現(xiàn)的包容性、倫理性,使它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適用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普及本,如《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等,其中的價值觀進(jìn)入當(dāng)時青少年的頭腦,使他們在立德立業(yè)上有所遵循。應(yīng)當(dāng)指出,這些觀念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需要,今天不能簡單照搬。
除去儒家經(jīng)書,中國還有史書,各個思想文化學(xué)派的代表作,以及個人的文集等。經(jīng)史子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
對文獻(xiàn)的整理,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清代產(chǎn)生了“專門漢學(xué)”,許多學(xué)者再次精心研究、整理中國古代的文獻(xiàn),糾正了許多錯誤。學(xué)者們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嚴(yán)密的搜集、排比、分類以及識別文獻(xiàn)資料的方法,對保護(hù)和傳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貢獻(xiàn)了智慧和心血。
習(xí)近平同志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座談會上對中華文獻(xiàn)作了這樣的評價:“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括著豐富的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內(nèi)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rèn)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jù),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nèi)容,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
結(jié) 語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jìn)文化相結(jié)合而形成的“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除上面論述外,還由于它滲透于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既有理念方面的指導(dǎo),又有實際行動的要求。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召開的紀(jì)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暨國際儒學(xué)聯(lián)合大會的講話中這樣說:“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斗,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根植于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沃土之中,同時又是隨著歷史和時代前進(jìn)而與日俱新、與時俱進(jìn)的。”這就是歷史與現(xiàn)實的統(tǒng)一,我們應(yīng)當(dāng)加以深入理解,在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chǔ)上,傳承和發(fā)展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