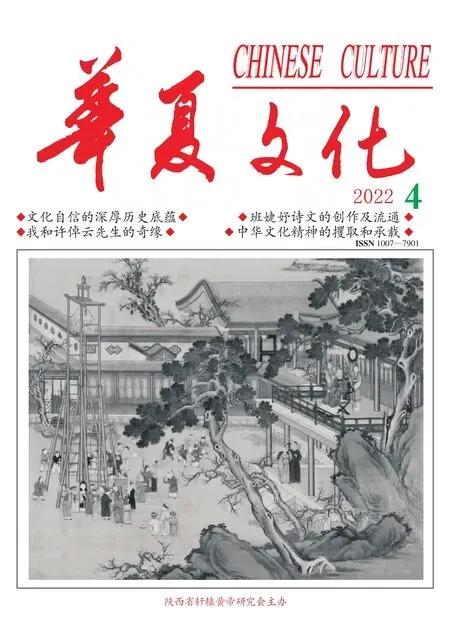海盜與亞歷山大、盜跖與孔子
——中西兩篇相似的對話
□程 旭
在中西方文化相遇之前,它們就獨自孕育出了兩個極為相似的故事。這兩個故事都以善者對不善者的發難或規勸開始,卻都以善者被指責為不善者而告終,并且都以國家產生于惡作為主題。它們就是亞歷山大大帝與海盜的對話和孔子與盜跖的對話。它們在歷史上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或許已無從考證,但它們都在經典文本中被留存至今,并成為作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見于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后者見于《莊子·盜跖》。在驚嘆二者的相似之余,我們更應深入比較文本的異同,揭示作者思想的特征。
一、海盜與亞歷山大的對話及其內涵
奧古斯丁關于亞歷山大與海盜的敘述只有寥寥幾句。盡管筆墨不多,但是奧古斯丁成功地道出了故事所必需的各種元素:作為皇帝、統帥以及審判者的亞歷山大,曾經侵擾海域而如今被俘虜的強盜,以及二人之間的對話。如果只從故事本身來看,這段對話至多只能算得上是一個以開放式結局結尾的故事。奧古斯丁對這一對話的描述是:“一個被俘獲的海盜對著名的亞歷山大大帝所作的答復是非常準確而且正確的。皇帝問那人,他侵擾海域算是怎么回事?他放肆地回答:‘同你在世界各處進行戰爭一樣。我在一艘小船上作戰,他們叫我海盜;你率領大艦隊作戰,他們稱你統帥。’”(奧古斯丁著,莊陶、陳維振譯:《上帝之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7頁)
如果只從對話本身來看,亞歷山大和海盜并沒有在辯論上分出勝負。一方面,就行為本身來看,人們確實無法否認戰爭和殺人放火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常識卻又使人們無法相信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與海盜沒有本質區別。然而最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亞歷山大與海盜也沒有進一步給出論證來證明或反駁這一觀點。整個故事雖然戛然而止,卻又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對話的語境在這里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作為審判者的亞歷山大與正在接受審判的海盜之間本來就沒有平等交流的必要,而海盜的回答也可以被視為答非所問。然而,最終保持故事完整性的是奧古斯丁本人。他是整個故事真正的法官。正是他宣判了海盜言論的正確性,也正是他解釋或賦予了這番言論唯一的意義。可以說,對話本身和對話語境所創造的開放性都只是為奧古斯丁本人的思想做鋪墊。
奧古斯丁直接宣判了海盜觀點的正確性,打消了人們出于常識考慮而產生的顧慮。他的理由如下:“在缺乏正義的情況下,主權不就是有組織的土匪幫嗎?因為土匪幫派不就是小型的王國嗎?他們同樣是一群人,在一個領袖統治下,由一個共同的協定相聯結,根據一個既定的原則進行分贓。如果這伙罪犯通過招募更多的罪犯獲得了足夠多的是勢力,去占領成片的區域,攻占城市,再制服所有人,然后它就更有資格采用王國的稱號。在公眾的評判中,它享有這個稱號,不是因為它棄絕了貪婪,而是由于它可以更加為所欲為。”(《上帝之城》,第46頁。)根據這一理由,奧古斯丁賦予了海盜言論以唯一的內涵:海盜和亞歷山大都是缺乏正義之徒,二人的靈魂最終無法得到上帝的救贖,只能接受無盡的懲罰。
然而,這一理由的問題在于:即使人們能夠輕易接受海盜缺乏正義的結論,但是斷定亞歷山大和海盜一樣缺乏正義卻需要更加有力的證據。僅靠亞歷山大所發動的戰爭和自己的海盜行為是一回事這一論點,難以令人信服。因為,人們可能會以戰爭和海盜行為的目的不同作為理由,拒絕接受這一觀點。
其實,奧古斯丁所說的正義,并非是指社會公平的現代術語。他根據愛的種類的不同將人分為兩類。一類人所懷有的是對上帝的愛,另一類人所懷有的是對俗世的愛,更準確地說是對自己的愛。世界上有且只有兩個社會,一個是公正的社會,另一個是缺乏公正的社會,它與前者完全對立。任何人必須屬于其中的一個社會。只有那些愛上帝的人,才能成為公正社會的公民。他們擁有一切真正美好的品德:注重公共利益、心靈寧靜、誠實、愛鄰如己等等,并且最終會和上帝同享至福。而那些只愛自己的人,也無法逃離那個缺乏公正的社會。他們只能在那個缺乏公正的社會中,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不斷地侵犯他人的利益,而等待他們的是絕望。正如艾蒂安·吉爾松在《上帝之城》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奧古斯丁根本沒有談到過人類能夠僅靠著對世俗的愛就構建出一個公正的社會,他把世俗和邪惡理所應當地結合在了一起。(《上帝之城》,第18頁。)
由此可見,奧古斯丁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把亞歷山大和海盜歸為同類,又是在什么意義上指責他們貪婪和為所欲為。在他看來,他們都忽視了靈魂的幸福,沉淪于世俗和肉體。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為最終目的。他們的本性都是利己主義者。他們與其他人所建立的協議和分贓原則不過是所有不義之人勾心斗角的產物,他們所建立的國家本身就是幻象,他們永遠都是孤身一人。倘若其中一人能夠獲得呂地之戒,那么他將完全漠視這些協議和原則,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為所欲為。他的一切行為僅以滿足自己的肉欲為唯一目的。那個被其他人稱為國王的人其實就是最接近呂地之戒的暴徒,他所具有的品質無非是更多的狡詐而已,而他最終得到的是將會比其他同類更嚴厲的懲罰。
以上便是海盜與亞歷山大的對話以及奧古斯丁所賦予該故事唯一內涵的全部內容。就對話本身而言,并不完整。而奧古斯丁則基于上帝之城和不義之城的思維模式,賦予了對話以唯一且明確的內涵。
二、孔子與盜跖的對話及其內涵
與奧古斯丁的寥寥數筆不同,《盜跖》篇用了兩千字左右的筆墨來描述故事。除了對話過程本身,它還交代了對話的前因后果。對話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孔子有意為之。孔子對好友柳下季說:“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莊子·盜跖》)由此可見,孔子此番造訪的目的就是說服盜跖停止燒殺搶掠的暴行。此外,孔子還向盜跖交代了具體方法:“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莊子·盜跖》)孔子說,只要盜跖愿意,那么自己就作為盜跖的外交官,替盜跖游說諸侯,使天下不但對盜跖曾經的暴行既往不咎,而且還封其為諸侯,贈與城池和百姓。然而,孔子的愿望并沒有實現。在被盜跖說教一番之后,他倉皇而逃,并向柳下季表明自己的所作所為無異于自尋死路。這些前因后果表明,孔子的愿望徹底落空。孔子與盜跖孰勝孰負見者自知,整個故事的完整性也因此大大超過了亞歷山大與海盜的對話。
然而,這種完整性并不能真正說明二人孰是孰非。就像亞歷山大和海盜的突然沉默造就的開放性結局一樣,孔子最后的狼狽不堪和懊悔也并不意味著盜跖的言論一定就是作者所認為的真理。事實上,這樣的結局至多只能說明孔子在盜跖的淫威之下被迫表示順從。然而,訴諸暴力并不是一種好的論證方式。因此,我們必須暫時懸置上述內容,關注盜跖的言說本身。
盜跖的言論大致可分為五個主題,非孔、非利、至德之世、非君王圣賢、論人之情。非利和非君王、非圣賢其實也是非孔的重要部分,但是就內容本身而言,它們與針對孔子本人的非難不同。本文所說的非孔特指后者。盜跖非孔,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認為孔子其人虛偽、其言不實。而非利和非君王、非圣賢就是這一點的重要論據。甚至可以說,非孔不是主題而是結論。非君王、非圣賢和其他三個主題之間的關系也是這樣。盜跖正是從君王、圣賢如何破壞至德,他們又是如何受利益的誘惑最終死于非命來論述為何非君王、非圣賢的。因此,本文將主要討論其余三個主題。
針對孔子提出的與天下和好的具體方案,盜跖表示:“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莊子·盜跖》)他認為,城池、領地、百姓都是會導致非命的外表鮮澤的毒果,只有蠢人才會認不清究竟什么樣的東西才是真正美好、具有價值的東西,才會傻傻地被這些東西誘惑,死于非命。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東西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呢。盜跖從人的本性出發,給出了結論。他說:“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莊子·盜跖》)在他看來,雖然人的壽命本身有限,與無窮的時間相比,猶如白駒過隙,不值一提。這有限的人生又可能常常被疾病、死喪和其他各種憂患所困擾,少有真正歡樂的時光。但是,聲色味觸等等身體的感覺、身體的動靜消息、精神的愉悅以及維持生命自身的存在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合理的、正當的欲求。不能追求并滿足于這些欲求的人,就與大道無緣。
在盜跖看來,這種欲求既不是毫無根據的空想,更不是死后上帝的恩賜,它是活生生的事實,是生活在至德之世中的人們共有的經驗。他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莊子·盜跖》)由此可見,盜跖認為,在黃帝之前,人們皆能找到與自然、與他人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既能使身體和精神的欲求得到滿足,保全性命,盡其天年,又能不侵害他人和自然萬物。
然而自黃帝以來,這種美好的人性就徹底被破壞了。盜跖說,“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莊子·盜跖》)他認為,自黃帝以來,人們就開始相互侵害,原本美好的品性丟失得越來越多,而國家也正是在人類墮落的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國家的產生與發展和人類的墮落實際上是一回事。那些被人們尊為天子的人,更是丟失了美好的品質。堯不把天下留給自己的兒子,所以不慈;舜總是遭到自己父親的厭恨,所以不孝;大禹因為治水,最終落了個半身癱瘓的下場;商湯放逐了自己的君主,武王對紂使用暴力,文王被紂關押了七年。而那些被世人稱為賢士的人,更是為了所謂的道德仁義死于非命。至德之厚的淪喪清晰可見。
由此可見,盜跖認為在同一個時代,人類只有一種生存狀態或者說社會關系。這種狀態或關系的差異只存在于以時代為尺度的縱向比較當中。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因為盜跖與孔子都處在一個僅憑個人力量無法逃避的墮落時代,所以,盜跖、孔子以及當時的所有人都是屬于惡的同類。然而,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事實上,盜跖從來沒有選擇要與孔子一同墮落。與之相反,他在非難孔子為文武布道、招搖撞騙、弄虛作假,看似教化實則戕害他人的同時,也宣布了自己與孔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在他看來,自己自始至終都處在至德的狀態。就言論的內容而言,我們與其說盜跖是一個善于詭辯的強盜頭子,不如說他是一個道德高尚、洞察秋毫的智者。他并沒有談及自己的暴行,更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護。他也沒有談及,在至德之世之后,人性淪喪的時代,個人又如何擺脫時代的桎梏,繼續保持獨善其身、通達大道的狀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回事。盡管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盜跖確實沒有談及。
或許《胠篋》篇中“盜亦有道”的命題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莊子·胠篋》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先入,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大盜必須具有五種品質,能夠從蛛絲馬跡中窺探出哪里有財寶,能夠率先士卒,能夠為小弟斷后,能夠判斷局勢知進知退,能夠公平地分贓。這五種品質分別就是圣、勇、義、知、仁。然而,本文認為這一命題與《盜跖》篇中盜跖的言論有很大出處。首先,《盜跖》篇所論述的偷盜行為與人情不符。前者仍是為利所誘,忽視了那些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其次,偷盜行為與至德之世相悖,與人人不相侵害的美好生活相矛盾。最后,在《盜跖》篇中,盜跖多次嘲諷那些篤行仁義的賢臣死于非命。既然如此,他決不會以仁義道德來規范自己,更不會標榜自己具體擁有哪些品質。
因此,本文認為,在《盜跖》篇中,是一位道家學者借盜跖之口闡述自己的觀點。《盜跖》篇中的盜跖其實是一位能洞察社會真相的道家智者,他不必為原來那個盜跖的殺人放火行為辯護。他本人能憑借對社會現實的敏銳觀察力,對歷史真相的了解以及獨立思考和懷疑的能力,免于沉淪,獨善其身。
總而言之,就對話而言,故事的完整性并沒有賦予故事以明確內涵。就對話內容而言,盜跖從非孔、非利、至德之世、非君王圣賢、論人之情這五個方面來論述自己的觀點。事實上,盜跖的言論并沒有為強盜行為作任何辯解,而盜跖本人也被偷換成了一位道德高尚的智者。
三、兩篇對話之異同
至此,關于兩則故事及其內涵本文均已說明。本文將根據以上內容,對二者的異同進行總結。
首先,就對話本身而言,海盜與亞歷山大的對話以二人的沉默告終,這導致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海盜與亞歷山大孰是孰非,海盜最后的話究竟意味著什么成為了懸而未決的問題。而最終解決這些問題,并賦予故事以唯一內涵的是奧古斯丁本人。盜跖與孔子的對話,由于交代了對話的前因后果,致使整個故事與前者相比更加完整。然而,這種完整性也不能說明故事的寓意或內涵究竟是什么。沉默和訴諸暴力都不是一種好的論證所應當采用的方式。二者雖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事實上都造成了同樣的未決狀態。
其次,就從未決狀態到明確內涵的過渡方式而言,奧古斯丁以審判的形式直接宣判了孰是孰非,并給出了明確的意義和理由。而在《盜跖》篇中,作者將本是強盜頭子的盜跖偷換成了道家智者,隱晦地表達了唯一的內涵。
再者,就內涵所表達的人物性質而言,海盜與亞歷山大都是不義之城的公民,是一同墮落的罪。而被偷換了的盜跖則成了始終保持著至德之厚的好人。他已不再是那個強盜頭子,也不必為殺人放火的行為辯護。孔子則是巧偽之人。
最后,就內涵本身而言,二者的思維模式在兩個方面有巨大差異。一方面,二者對事物進行善惡分類的標準不同。奧古斯丁基于精神與肉體、此岸與彼岸相對立的思維模式,將世俗的、肉體的欲望與惡絕對地聯系起來,而與之相對的是對上帝、靈魂、和來世幸福的愛,這種愛是圣潔的、美好的、真正值得追求的。盜跖則基于物己對立的思維模式,認為人類自身肉體的欲望、精神的欲望和自身的存在是一個整體,對于這個整體的欲求本身就是正當的,與之對立的則是外在于己的事物。具體而言,這類事物就是諸如城池、領地、百姓、名譽等等事物,盜跖將其統稱為“利”。在他看來,這類事物不但與人的本性實際上毫無關系,而且必然會導致那些被誘惑的人們最終失去真正具有價值的東西。
另一方面,二者對國家或社會的思維模式不同。在奧古斯丁的思維模式中,有兩個始終存在著的相互對立的社會。前者是以基督為王的正義之城。而后者則是利己之人匯聚而成的不義之城。后者與其說是社會,不如說是裝滿了蠱蟲的罐子。不同的是,那個裝滿蠱蟲的罐子中最終會有一個勝利者,而在不義之城中,所有人最終的結局都是不幸的。事實上,他們彼此之間根本沒有社會或國家可言,有的只是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而在對話中,奧古斯丁所論述的正是在不義之城中的虛假國家。就對話及其內涵而言,奧古斯丁并沒有談及上帝之城。然而,在《盜跖》篇中,作者則認為整個人類在同一時代只有一種生存狀態或社會關系,而國家正是在人類由美好時代向墮落時代過渡的過程中產生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國家。然而,個人也未必完全受時代的主宰,他可以憑借自身的修養在亂世中獨善其身,保持至德。
四、結語
總而言之,這兩篇對話并不像我們一開始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極高的相似性。首先,對話人物的身份與對話內容所要表達的內涵實際上并沒有直接關聯。其次,就奧古斯丁的國家思想而言,不義之城中的國家其實只是海市蜃樓,上帝之城究竟如何才是更為根本的問題。最后,如果說奧古斯丁沒有談論過人類能夠僅靠著對世俗的愛就構建出一個公正的社會,那么相較于奧古斯丁,《盜跖》篇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則更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和啟發意義,這一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