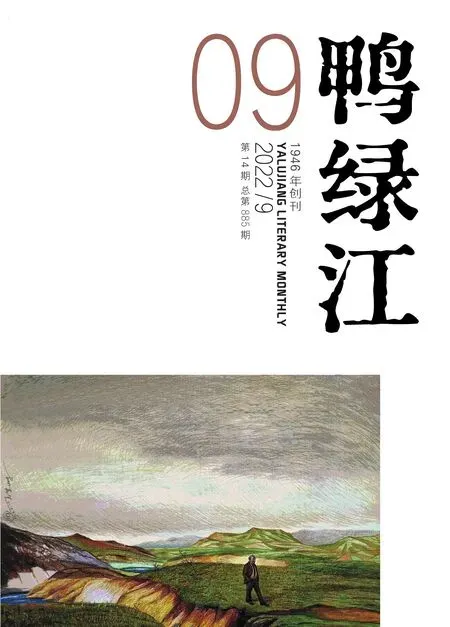別說
寧浩宇
別說無路可退,
別把逃避或順從叫作前進,
別說只是遇見,
只是一一把他們錯過。
光交融夜,
暈圈生于低空,
別一起模糊了
父親,母親。
雨水玲瓏,
迷離層紗
隔開廣播和天外世界,
巨雷霹靂和烏有橡樹。
別探知視光的反照
與睫毛相觸的距離。
哪怕勇敢,哪怕一步步踏出,
別說你沒有心動
別說你無法流淚,
別說詩歌怎能容下淚水。
未來前史
老頭的手藝來自八方
兒子在不遠處開了分店
小時候吃的米飯
白中點綴著黃
生意紅火后關門大吉
不會外語的男人去韓國打工
綠化帶的詩意復制粘貼
日光刺眼
男人,家務
女人,工作
贍養父母兒女爭吵彼此擁擠
高泳之魚鷹死于倒影
千萬里
千萬里土豆被挖起
學名:陽芋
老頭佝僂,不下后廚
只和客人聊天
保持背扛的姿態
船塢
房間在橋上掠過
看著
金魚撞魚缸仿佛看見窗外
橋墩和羅馬柱交錯
海霧遮遮掩掩爛尾樓
FM的精確數字
靠無主之地含糊其詞
我們如此懷舊:
每個當下的恍惚:
漁火隧越成超高功率的照明燈
巨輪無壽命
在亮如沙漠的夜檢修
他的無限瞬間
有別于蟻群的遲鈍于吊車
俯就涯間來路
小山東
小山東用刀子劃傷了手
老山東昨天撿了一條狗
用黑塑料袋提著
跟炒飯店老板炫耀
小山東牽著哥哥的手
多余的時間都在空地和陽臺
姐姐回家時帶電腦
那里豌豆也能殺死僵尸
我告訴他不要一個人玩刀
狗肉不干凈
看他玩游戲時心不在焉
誰也不該說這些話
煙臺渡輪7小時240元
新家具好老
租下沿街“商鋪”
賣五谷雜糧
血流得不多
哭聲倒不小
白泡沫還剩一半
才有劍的輪廓
小山東走了
半年后我再經過那條街
交通堵塞
鐵皮棚子都拆了
高溫
當陸地曬成白色。
夜的穿行
以蟒眼的速度
后來山青青水清清
青與輕,讓人喘不過氣。
海天之間水陸絲連
有大鯨以涂抹之清涼
欲除天下燥熱。
不甘于熱啊熱,熱來熱去
熱沒了熱帶。
云意
老松樹斜逸。
蜂群游梭紫槐,
枝頭僅剩的
松針云意遮住遠山黝微
高樓和工業建筑。
喜鵲窩不多不少懸置槐樹中心,
腦中卻絕無鳥跡,
可它翩翩然悠蕩入境,
帶來廢棄木板屋
或是倉庫之類的東西,
還有角落里
三個印著廣告的塑料桶
混搭出詞語
公交車環山行駛,
在一個清澄天
帶著每個昨夜的翅蹤
豐饒
情如水。
送江水逝流,
它卻記住所有的山色蒙翠
就這樣升格為萬物
看到
看到了塵沙漫漫的天空,
禿樹,樹枝上的喜鵲窩,
起重機沉默
背對丘陵白塔。
看到馬蜂看到的這一切,
低水平的神魂一陣恍惚。
還是要撲扇,要回去,
可惜沒有關于玻璃的概念。
看到這一切,你不會開窗。
很多時候只是一條道,
花樹滿天。
日產尼桑在前面馳行,
葉落花去,
公園的長椅上,先知
和穿風衣的老人拄杖而眠,
在夢里追月亮。
霧雪
被截斷身子,
高樓空空懸吊。
蛇鱗浮騰起若有若無
何時風滿?
大氣中到達也是離開。
對于流風回雪的小家子氣
和灰色世界的無氣可吐,
有誰在喧嘩雄壯的山洞里
浪浪流襟。什么也看不見,
可兩只白鳥略過濁玉的湖面,
卻看得明明白白
黃衫
黃衫豪客以流星身法
凌波踏雪,
千里行走人事成全。
木檐高翹風片,嘮嘮叨叨。
飛瀑觸古樹,盤根裸露,
反光佛像太高也太大了,
要低頭才能看見苦難眾生。
它嘴唇微啟,輕吐蓮花:
“度來度去,到頭來就鍍了我
一身假黃金。”
回頭望月是白日朗朗。
除雪機攪起文字游戲。
氣流古往今來,
又隔斷古意。
雪下到現在,下成流體,
透明輕盈卻顆粒干澀。
游成鯊魚繞環瀝青,
繞成指柔手托紗緞。
黃衫讓步黃毛衣,
豪氣絕霄,往來穿越
為自己刷上黃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