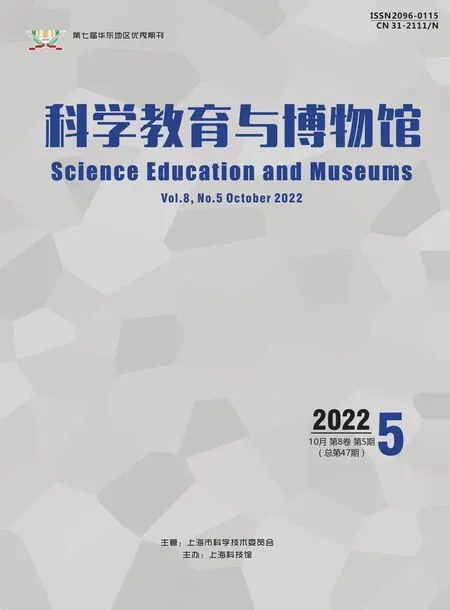懷舊與創(chuàng)新:景箱在自然博物館展示的實踐與反思
——以浙江自然博物院展陳為例
施波文
浙江自然博物院
0 引言
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影響著博物館各個方面,如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文化等,進而對博物館實體的形式、性質(zhì)、關(guān)系等產(chǎn)生影響。因為博物館主要是通過陳列展覽向觀眾進行知識傳播和公共教育,所以陳列展覽是博物館傳播先進文化、發(fā)揮社會教育作用的主要手段,是博物館為公眾提供公共文化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主要形式[1]。縱觀自然博物館發(fā)展歷程,其專門的陳列展示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多元,受到了社會發(fā)展、社會審美、社會教育、信息傳播、博物館與公眾關(guān)系等因素的影響,這在博物館展陳定位、內(nèi)容表述、視覺呈現(xiàn)、功能實現(xiàn)和評價體系等方面均有所體現(xiàn)。生境景箱作為國內(nèi)外自然博物館最為經(jīng)典的展陳方式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甚至與自然博物館的發(fā)展歷程息息相關(guān)。本文以浙江自然博物院三次館建陳列中的生境景箱展示為例,探析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景箱在新技術(shù)輔助下的展示新貌,以及在博物館公眾教育方面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1 Diorama 一詞的定義與釋義
Diorama 在博物館語境下的中文譯名,有“立體造景”[2]“全景模型”[3]“生態(tài)造景”[4]“生境景箱”“景箱”[5]等。英語詞典中的解釋是“用三維造型表現(xiàn)一個場景的模型,可以是微縮模型,也可以作為大型的博物館展品”[6]。Diorama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展示方式,在當(dāng)今博物館展示中可以經(jīng)常看到。普遍意義上的博物館Diorama,是一種將實物和非實物展品置于背景為畫面或構(gòu)筑物的環(huán)境中,以展現(xiàn)某個自然或歷史場景的三維組合裝置。其組合展示特征為“景”與“物”相結(jié)合,“物”是主體,“景”是基于科學(xué)性和真實性對動物棲息地進行還原,它包含了一定體積的模型搭建而成的前景以及通常是二維繪畫的背景,其背景一般巧妙利用透視法和弧形墻面以達到開闊景觀的效果,而前景和背景共同組成了主體物存在和活動的場所[7]。有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歐美國家語境下的Diorama,在大陸博物館學(xué)界,被賦予了符合中國博物館特色的本土化定義,即“情景再現(xiàn)”[8]。如嚴(yán)建強教授觀點,“復(fù)原”是陳列語言中最關(guān)鍵的概念,“通過對展品的復(fù)原性處理,消弭或縮小了展品與觀眾在時空上的距離,將觀眾象征性地置于‘現(xiàn)場’,從而理解了展品的意義及其相互間的關(guān)系”[9]。為了厘清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國內(nèi)學(xué)者張琰對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作了分析:情景再現(xiàn)實際上是實物展品與繪畫、模型、雕塑、多媒體、互動體驗設(shè)備等各類非實物展品的科學(xué)組合,它作為一種重要的展覽敘述形式,從陳列語言的角度被提出,涵蓋的形式范圍更廣。Diorama 是實現(xiàn)情景再現(xiàn)效果的其中一類構(gòu)成元素相對固定、本身具有顯著特征的展示裝置,是實現(xiàn)情景再現(xiàn)效果的手段之一[10]。英國倫敦大學(xué)著名的科學(xué)教育專家蘇·圖尼克利(Sue Dale Tunnicliffe)對Diorama 及其社會教育功能做過專門研究,認(rèn)為Diorama 既可以是玻璃櫥窗形式,也可以是無玻璃阻隔的開放式結(jié)構(gòu)[11]。原上海科技館副館長金杏寶博士在《博物館展覽——營造自主學(xué)習(xí)的開放空間》中,引用了蘇·圖尼克利的研究,將Diorama 和Panorama 分別譯為生境景箱(景箱)和全景箱,認(rèn)為這種展示方式揭示了特定地域內(nèi)和生境中的各種生命獨特的棲息狀態(tài)和生存策略,它們與環(huán)境之間真實的依存關(guān)系,以及動植物區(qū)系的變遷[12]。鑒于此,依據(jù)Diorama 的特征和功用,順應(yīng)大陸博物館語境下的表述習(xí)慣,本文采用了“生境景箱”(或簡稱“景箱”)為Diorama 的中文譯名。
但是,中文譯名“景箱”,亦給人們造成一些困惑,常常將其與“情景再現(xiàn)”混為一談,認(rèn)為Diorama僅限于三面或四面玻璃櫥窗的景觀箱,其實玻璃展柜只是Diorama 與博物館結(jié)合的早期形式,隨著國內(nèi)外博物館的長期實踐,Diorama 的規(guī)模、設(shè)計和形式早已變得復(fù)雜多樣,沒有玻璃阻隔的開放空間同樣可以表現(xiàn)Diorama。因此,采用玻璃展柜進行展示并不是判定博物館Diorama 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13]。
2 生境景箱在自然博物館發(fā)展歷程中應(yīng)運而生
2.1 景箱展示誕生的歷史背景
自然博物館的發(fā)展演變,其具有的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能受到社會思潮、文化變遷與歷史因素之深厚影響。16 至17 世紀(jì),自然博物館最為重視的是其研究功能,博物館的收藏在當(dāng)時主要為科學(xué)家提供研究物件。17 世紀(jì),隨著動物學(xué)標(biāo)本處理技術(shù)獲得新進展,博物館開始使用高濃度酒精將標(biāo)本以液體形式保留,運用火石玻璃便于觀眾觀看液體標(biāo)本,借助蜂蠟和水銀使干制標(biāo)本能夠被展覽[14]。到了18 世紀(jì),林奈分類法使自然博物館展覽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步入類型學(xué)(typology)[15]。19 世紀(jì)中后期,哈佛大學(xué)比較動物學(xué)博物館創(chuàng)始人阿凱西斯(Louis Agassiz)博士將一些標(biāo)本搬至另一處樓房進行教學(xué)和展示,這種做法將教育和展示空間從原來的收藏空間獨立開來[16],是博物館經(jīng)歷的第一次分化式發(fā)展,為博物館實施有目的、有計劃的教育活動提供了平臺。到1851 年,英國倫敦舉辦萬國博覽會后,開始融入設(shè)計理念,開創(chuàng)了展示的新紀(jì)元,博物館展示自此開始運用更多元的手法[17],包括對于展場的燈光、布置、裝飾等,展示也因而變得更為生動、有趣。在19世紀(jì)到20 世紀(jì)之間,由于受到透視及全景圖像的影響,背景畫與博物館中的生境展示密切結(jié)合,為呈現(xiàn)物件的脈絡(luò)與背景提供了更多可能。尤其在19 世紀(jì)末,隨著動物標(biāo)本剝制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使動物標(biāo)本可以在真實或虛擬的“自然”環(huán)境里進行展示,自然博物館逐漸發(fā)展出所謂的生境景箱(Diorama)的展示手法。到20 世紀(jì)中后期,新博物館學(xué)運動興起,盡管各國因歷史文化背景及綜合國力的差異,博物館建設(shè)不盡相同,但是人們對博物館教育功能的認(rèn)識日趨豐富,因生境景箱代表了展覽與教育的完美融合,逐漸被運用在自然史與民族學(xué)展示中,后來歷史類展示也常運用此展示手法[18]。
2.2 景箱展示應(yīng)運而生
早在19 世紀(jì)末,以“Diorama”命名的公共博物館展示形式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在這之前,歐美博物館中已多次出現(xiàn)了這種展示形式的雛形。博物館景箱中最常見、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類型是“棲息地立體模型”(habitat diorama),最初在歐美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中嶄露頭角,它以1:1 的比例在模擬的棲息地環(huán)境中展示動物標(biāo)本[19]。通常,生物組(biological group)、地理組(geographical group)、生境群(habitat group)等,都被看作是“棲息地立體模型”的早期形態(tài)。生物組和地理組大多用在歐洲早期博物館對于物種及自然史的展示當(dāng)中,生境群則較晚出現(xiàn),主要在美國博物館中保留了較為完整的發(fā)展脈絡(luò)[20]。生物組和地理組的共同問題在于對自然環(huán)境的詮釋很有限,而且缺乏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它們只是將標(biāo)本和少量的仿真物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生境群被認(rèn)為是棲息地立體模型的前身之一,它被定義為“按實物大小比例組合而成的三維裝置,目的是在背景畫所描繪的接近實際地理環(huán)境的場景中展示標(biāo)本”[21]。“生境群”一詞,由美國鳥類學(xué)家弗蘭克·查普曼提出,他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展廳展示了北美鳥類及其生存環(huán)境。此后,一些較大型的哺乳動物開始被陳列在更為復(fù)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觀眾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現(xiàn)在看來,生境群展示手法并不復(fù)雜,展出的動物標(biāo)本形態(tài)也比較呆板,呈現(xiàn)的環(huán)境也不具有明顯的典型性和可識別性,但它改變了標(biāo)本密集呆立于展柜中的情形。標(biāo)本不再是一件孤立的認(rèn)知對象,動物與自然界之間的關(guān)系被直觀地展現(xiàn)在觀眾眼前,沒有生命的標(biāo)本一旦與自然景觀擺放在一起,仿佛也煥發(fā)出一些生機。19 世紀(jì)末,隨著動物標(biāo)本剝制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動物可以在真實或虛擬的“自然”環(huán)境里進行展示,以期達到更好的教育意義。同時,受到當(dāng)時社會盛行的透視及全景圖像影響,在20 世紀(jì)初,生境群展示中的背景畫與博物館結(jié)合起來,自然博物館逐漸發(fā)展出更接近于現(xiàn)今人們理解的博物館生境景箱。但是,“Diorama”一詞具體在何時何地取代生物組、地理群、生境群等詞匯,并成為博物館展示形式的名稱,已經(jīng)難以考證[22]。
歷史上,被認(rèn)為第一個制作生境景箱的人,是沃德自然科學(xué)研究所(Ward’s Natural Science Establishment)的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他有著“現(xiàn)代標(biāo)本剝制術(shù)之父”美譽[23]。1889 年,他在密爾沃基公共博物館(Milwaukee Public Museum)制作的反映麝鼠的生活場景,現(xiàn)在依然還在。當(dāng)時,由科學(xué)家、標(biāo)本剝制師、畫家等組成的團隊遠出實地考察,以求證景箱設(shè)計的科學(xué)精準(zhǔn)。他將麝鼠標(biāo)本安置在栩栩如生的沼澤棲息地生境中,盡可能地還原其真實生存狀態(tài)。觀眾不僅可以看到姿態(tài)各異的麝鼠,還能從獨特視角看到河流的水下截面,了解麝鼠的棲息狀況。該景箱展示不僅展現(xiàn)了物種的外形,還清晰地呈現(xiàn)了麝鼠的生活方式與其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24]。1936 年,卡爾·艾克里(Carl Akeley)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精心打造的非洲哺乳動物展廳對外開放,成了博物館發(fā)展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
這些展示可以稱作是現(xiàn)存最早的立體透視生境景箱,包含了主體、前景和背景三大要素,前景和背景共同組成了主體存在和活動的場所。現(xiàn)今,國內(nèi)外自然博物館的景箱,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空間狹小的玻璃展柜,其規(guī)模、形式和設(shè)計變得更為靈活多樣,復(fù)雜精細,并逐漸被其他類型博物館所借鑒。
2.3 生境景箱的價值與意義
當(dāng)今自然博物館在履行其自然教育使命的內(nèi)容和方式手段上不斷追求創(chuàng)新突破,自然教育的本質(zhì)內(nèi)涵滲透進博物館工作的方方面面。博物館學(xué)研究和自然教育的目標(biāo),并不只是了解眾多與自然相關(guān)的知識,還包括積極的自然情感以及體驗探索自然的能力[25]。自然博物館中的景箱展示,作為發(fā)揮博物館教育潛力的重要工具,它的出現(xiàn)實際上代表了收藏、展示和教育使命的完美結(jié)合。
2.3.1 生境景箱是展示物件及物件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最佳方式,闡釋了主題的知識性、脈絡(luò)性和系統(tǒng)性。一方面,在真實的自然環(huán)境中,地理環(huán)境的多樣性和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共同構(gòu)成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多樣性。各種典型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系統(tǒng)內(nèi)的物種,有著緊密的依存關(guān)系,如生物之間的捕食、競爭、共生與共棲等。單獨的標(biāo)本陳列,無法說明這種自然界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而通過景箱,可以向觀眾直觀清晰地展示生物群落與地理環(huán)境的互動性與適應(yīng)性;另一方面,景箱既可以詮釋物件的生態(tài)性,又能說明生物的棲居環(huán)境(habitat)特點,讓展示的物件呈現(xiàn)出更為完整及脈絡(luò)性的全貌[26]。自然博物館中各種規(guī)格的生境景箱,使得展示物件的意義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意涵,而是與其他同一陳列展場的物件息息相關(guān),呈現(xiàn)了彼此互相輔助與串聯(lián)的展示脈絡(luò),有助于強化展示的教育目的,觀眾即使不具備相關(guān)背景知識,也可以通過觀察來理解展示之內(nèi)涵。
2.3.2 生境景箱有助于激發(fā)觀眾對話與思考,傳遞保護生態(tài)系統(tǒng)多樣性的理念。一方面,自然博物館生境景箱可以展示各種典型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包括珊瑚礁、紅樹林、針葉林、北美荒漠、稀樹草原等,讓觀眾不僅看到地球上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復(fù)雜多樣性,也讓人們發(fā)現(xiàn)不同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與系統(tǒng)內(nèi)的物種之間,存在著重要的依存關(guān)系,而我們?nèi)祟惐旧硪彩清e綜復(fù)雜的系統(tǒng)組成部分之一。各類主題的生境景箱展示,可以引發(fā)公眾對自然的依存和責(zé)任感,理解自然生態(tài)與人類文明的關(guān)系;另一方面,優(yōu)良的博物館陳列展示,實際上是為觀眾營造一個自主學(xué)習(xí)的環(huán)境或氛圍,觀眾可以通過多種感官體驗來獲取可靠的信息[27]。自然博物館中常見的各類生境景箱展示,不論是玻璃櫥窗式,還是無玻璃阻隔的開放式,通過逼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營造,能激發(fā)人們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天性,使之成為學(xué)習(xí)和獲取知識的內(nèi)在動力,為博物館參觀體驗帶來更多的自主探索與樂趣。
3 傳統(tǒng)景箱應(yīng)用的靈活與創(chuàng)新
20 世紀(jì)以來,新科技的進步與發(fā)展,為博物館展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博物館展示,從一開始單一的物件陳列,進展到重視物件知識性的分類、設(shè)計概念的加入,再到展品脈絡(luò)性的原始樣貌呈現(xiàn)、打破城墻的博物館環(huán)境營造,最后到多媒體數(shù)字技術(shù)、三維建模、物聯(lián)網(wǎng)等技術(shù)的融合應(yīng)用,展示趨向復(fù)雜化、互動化和虛擬化,為自然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注入活力。
浙江自然博物院有3 次大規(guī)模的場館籌建與陳列布展,從這幾十年的陳列展示發(fā)展來看,不論是20 世紀(jì)90 年代以標(biāo)本為核心的教工路館區(qū)陳列,還是新一代突出智性休閑的安吉館區(qū),都能見到生境景箱的應(yīng)用。傳統(tǒng)懷舊的景箱發(fā)展至今,隨著新材料、新技術(shù)的引入創(chuàng)新,在兼具科學(xué)性、邏輯性的同時,又融入了觀賞性、參與性和體驗性。
3.1 以標(biāo)本為核心的老館區(qū)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教工路老館區(qū),自1984 年從杭州西湖湖畔的浙江博物館的自然之部分出單獨建制后,囿于館舍、經(jīng)費等原因,無固定陳列場所,博物館的功能運作一度受到制約,影響了社會教育功能的有效釋放。后經(jīng)多方努力,館舍建設(shè)方面于1991 年建成庫房業(yè)務(wù)樓,1998 年建成陳列館,面積3 051 m2,基本陳列“恐龍與海洋動物陳列”榮獲了1998 年度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當(dāng)時,該陳列嘗試打破傳統(tǒng)的展柜標(biāo)本陳列手法:在海洋動物陳列單元中,背景設(shè)計成藍色海洋畫面,人造珊瑚礁附近,立體空間里穿插懸掛著各式魚類;恐龍陳列單元中,將恐龍骨架標(biāo)本陳設(shè)在簡易的古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增強可視性和吸引力。展覽推出后,頗受觀眾歡迎。教工路老館時代,仍處于博物館以物為核心的階段,還沒有系統(tǒng)完整建立起為觀眾闡釋的想法,陳列思路和模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dāng)時研究的成果。但是當(dāng)時能突破傳統(tǒng)的標(biāo)本陳列模式,將標(biāo)本及標(biāo)本生境信息一起展示,在今日看來,盡管細節(jié)制作略顯粗糙,卻也是陳列展示的一次重要提升。
3.2 以呈現(xiàn)科學(xué)、真實為核心的杭州館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西湖文化廣場的杭州館區(qū),于2009 年建成開放,展陳面積5 200 m2,陳列主題為“自然·生命·人”,由“地球生命故事”“豐富奇異的生物世界”“綠色浙江”三個單元組成,各單元都有一定比例的景箱展示。展覽將符合自然博物館定義的“自然”“自然史”“自然與人類”三重內(nèi)容融為一體,將觀眾引向?qū)ι锒鄻有约叭伺c自然和諧重要性的思考,體現(xiàn)了自然歷史的科學(xué)體系,也有助于增進人們對自然與生命的興趣和責(zé)任感。
3.2.1 注重科學(xué)提煉,景箱的生境展示科學(xué)嚴(yán)謹(jǐn),并適度引入簡易互動裝置。例如設(shè)計“浙江山地”展項,組織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赴浙江典型的丘陵山地考察,擇取與指定生態(tài)系統(tǒng)景觀相關(guān)的生境信息,包括生物的個體、種群或群落所在的具體地段環(huán)境及其他的生態(tài)因素,以及不同類型的景觀要素或生態(tài)系統(tǒng)構(gòu)成的景觀,在空間結(jié)構(gòu)、功能機制和時間動態(tài)方面的多樣化信息,并進行模擬設(shè)計、高仿真翻模制作。相較于傳統(tǒng)的靜態(tài)景箱展示,引入互動概念,在觀眾駐足參觀處,設(shè)有可旋轉(zhuǎn)的拋物線探測器,方便觀眾自主操作,當(dāng)瞄準(zhǔn)場景中的某只鳥類標(biāo)本后,可在設(shè)備中聽到該種鳥類的鳴叫聲。另外,立桿式攝像機讓觀眾可以自由選定想觀察的動物,在設(shè)備上便可觀看該動物的相關(guān)視頻。
3.2.2 采用新工藝,通過空間、色彩、造型等設(shè)計要素,在有限空間營造生動逼真且富有意境的立體生境。在各類輔助展品制作方面,如浙江山地的樹木脫脂、防腐、樹葉鋼模翻制工藝,呈現(xiàn)了山林枝葉繁茂的效果;以浙江下渚湖濕地為模板的景箱中,亞克力水面雕模工藝使得水域呈現(xiàn)出波光粼粼的效果,水域的截面展示,便于觀眾觀察該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魚蝦、貝類等物種,新技藝的引入確保了時空場景和生態(tài)系統(tǒng)景觀展示的質(zhì)量和效果;在制作浙江海島的巖石輔助展品中,應(yīng)用巖石造型翻模技術(shù),島嶼峭壁和背景畫中的海島連成一片,幾近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為珍稀的中華鳳頭燕鷗等鳥類標(biāo)本展示營造了良好的生境背景;浙江山地展示中,還應(yīng)用了燈效控制、影音播放及機電一體化互動展項技術(shù),觀眾可以感受晨曦光線變化中的山林,聽到山林中棲居動物的叫聲,看到各種動物身影,仿佛步入真實的大自然環(huán)境中。
3.3 注重主題闡釋多維度、脈絡(luò)性的安吉館景箱展示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館區(qū)于2018 年12 月試開館,后經(jīng)半年多的整改提升和調(diào)試完善,2019 年10月正式開館。作為亞洲單體建筑最大的自然博物館,安吉館區(qū)有地質(zhì)館、生態(tài)館、貝林館、恐龍館、海洋館和自然藝術(shù)館6 個獨立展館,因展示技術(shù)的進步與迭代更新,安吉館的展示形式多元豐富。除了藝術(shù)化的標(biāo)本陣列,安吉館設(shè)有51 個生境景箱,講述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涵蓋地球科學(xué)與生命科學(xué)的相關(guān)主題故事。貝林館、恐龍館、地質(zhì)館的景箱設(shè)計各有側(cè)重和特點,可以說是多維度地體現(xiàn)了景箱“自然之窗”的教育功能。
3.3.1 重視景箱中重要輔助展品的制作應(yīng)用。貝林館的景箱數(shù)目在6 個展館中屬最多。早在2016 年,肯尼斯·尤金·貝林(Kenneth E.Behring)先生捐贈了176 件標(biāo)本用于籌建安吉館區(qū)的貝林館,捐贈的標(biāo)本大部分來自非洲和北美洲。為了充分利用這批珍貴的標(biāo)本,貝林館設(shè)置了大小不一的各種生境景箱,其中最為主要的有北美沙漠、北美大草原、北美苔原、北美沼澤、浣熊、土撥鼠巢穴6 個主題故事景箱。貝林館的景箱特點在于,仿真獸類模型在完整科學(xué)敘事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貝林館的展覽內(nèi)容中,除了展示非洲和北美洲的標(biāo)本之外,還涉及很多澳洲、南美洲的有袋類標(biāo)本。一些景箱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相關(guān)獸類標(biāo)本無法獲得的問題,原因是部分標(biāo)本不在貝林先生的捐贈清單內(nèi),同時受到國際公約制約,或受到相關(guān)國家對動物標(biāo)本出口的限制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無法征集到,這些標(biāo)本的缺失將直接影響到展覽主題的完整性和典型性,甚至影響展覽的科學(xué)解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采用高仿真獸類模型來替代無法征集到的獸類標(biāo)本的方法,以完成景箱的完整敘事。獸類模型,就是應(yīng)用其他材料模仿獸類動物本身,并通過特定的工藝制作而成的仿制品。制作一般先對獸類進行3D 建模,其關(guān)鍵之處在于對動物形體科學(xué)性的把握,再利用3D 打印技術(shù)制作動物假體,定制人工皮毛,最后對人工皮毛進行整形并著色。雖然仿真模型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但與真實標(biāo)本不可相比,不具備研究價值,從這個角度而言,仿真標(biāo)本僅能在展覽展示方面替代獸類動物標(biāo)本[28]。例如北美沼澤濕地景箱中的星鼻鼴、美洲獾捕食的黑尾土撥鼠(美洲獾在洞口伺機捕食土撥鼠,土撥鼠被設(shè)計在洞穴內(nèi),光線較暗,觀眾無法看清細節(jié),因此很好地掩蓋了模型的不足,又不影響觀眾觀看)等。
3.3.2 多媒體數(shù)字技術(shù)融入傳統(tǒng)景箱展示。相較于杭州館的景箱展示,安吉館的景箱主題涵蓋面更為廣泛,不僅涵蓋了生物學(xué),在古生物、地質(zhì)學(xué)方面也得到大量應(yīng)用,并且輔之以新媒體數(shù)字技術(shù),讓景箱的敘事性與故事性更強。例如地質(zhì)館,既展示浙江的地質(zhì)史專題,又展現(xiàn)從前寒武紀(jì)到第四紀(jì)地球結(jié)構(gòu)、地質(zhì)年代、生物演化等共性的地質(zhì)學(xué)內(nèi)容。因為時間跨度達數(shù)十億年,信息量大且抽象,為將抽象的時間概念具象化,展廳中央設(shè)置了13 個微縮景箱,對應(yīng)從前寒武紀(jì)至第四紀(jì)的13 個地質(zhì)年代。在微縮景箱的背景畫中設(shè)置了投影播放三維動畫視頻,各種外形奇特的古生物模型、化石與投影動畫有機結(jié)合,生動地講述了各時期生物群的典型生命特征,仿佛時間被凝固于咫尺之間,讓人們在有限的展示空間中了解奇幻的遠古世界。
又如恐龍館,以三疊紀(jì)、侏羅紀(jì)和白堊紀(jì)的時間順序展出各種恐龍。其景箱展示大致分為兩種:恐龍骨架所展現(xiàn)的生態(tài)造景與恐龍復(fù)原模型的全景式生態(tài)造景,二者皆生動直觀且通俗易懂地讓觀眾了解恐龍時代的生命景象及與生存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等。在設(shè)計恐龍的生存環(huán)境時,在題材、情節(jié)的設(shè)定、表現(xiàn)形式的選擇、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等方面,都嚴(yán)格控制在科學(xué)研究的范疇之內(nèi)。在介紹浙江的恐龍時,背景畫都采用了傳統(tǒng)的繪畫形式,巨幅背景畫前延伸開來的真實生態(tài)環(huán)境里,展出了白堊紀(jì)的麗水浙江龍、縉云甲龍、越龍、天臺鐮刀龍等,輔以幻影成像、光電玻璃等,模擬并塑造出遠古時期恐龍的真實生活場景;而在早白堊世中國遼西地區(qū)的熱河生物群展示中,輔以燈控、投影裝置,對當(dāng)時植被繁茂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做了細致還原,為觀眾了解該生物群鋪墊了豐富的背景信息。
3.3.3 景箱制作材料考究、工藝精良。安吉館的生境景箱制作,在相關(guān)材料的擇選上緊隨技術(shù)發(fā)展,注重品質(zhì)。為達到良好的展示成效,豐富視覺效果,對細節(jié)的把控更為嚴(yán)格。對于一些封閉的玻璃櫥窗式景箱,根據(jù)需要選擇6 mm 至8 mm 的超白夾膠玻璃,透光率>97%,并精確計算傾斜角度以避免反光,降低環(huán)境光的干擾,讓參觀者擁有更舒適輕松的觀看體驗;對不同的景箱主題進行空間布局時,遵循科學(xué)研究的前提下注重藝術(shù)表現(xiàn)力,采用弧形結(jié)構(gòu)對背景畫和天頂進行搭建,例如恐龍館,考慮到總高度12 m,有限的展示分區(qū)限制了觀眾的視點,在景箱制作時,為避免視覺變形,特意將背景畫略微前傾15°,以減小透視變形;在繪制背景畫時,依據(jù)觀眾平均身高,把握視平線高度,增強現(xiàn)場感,讓背景畫展現(xiàn)真實的自然景觀無邊無際的效果;注重場景的燈光照明,設(shè)置隱蔽的燈光布局,模擬自然光線,盡量提供自然真實的觀看體驗。
4 結(jié)語
自然博物館屬于一般大眾能自主學(xué)習(xí)的場域,成為科學(xué)與一般大眾之間的重要媒介。有著悠久歷史的生境景箱,藉由背景的繪制與相關(guān)標(biāo)本的擺飾,營造出真實逼真的生態(tài)景觀,讓觀眾更能容易地了解物件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是說明及解釋展出物件的最佳方式之一。生境景箱有效結(jié)合了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使命,在激發(fā)觀眾思考、促成自主學(xué)習(xí)、促進智識發(fā)展等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優(yōu)越性。
從浙江自然博物院3 次館建陳列來看,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下,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生境景箱在自然史的陳列展示中,依然處于重要地位。面臨新技術(shù)、新材料的發(fā)展變革,傳統(tǒng)景箱并不是一成不變,能及時融入更多創(chuàng)新元素,應(yīng)用范圍逐漸拓展,設(shè)計制作也逐漸走向成熟。生境景箱在詮釋展示物件的原始環(huán)境樣貌時,既有科學(xué)研究的細致嚴(yán)謹(jǐn),又有藝術(shù)表現(xiàn)張力帶來的情感渲染力,它們通過景箱知識性、系統(tǒng)性、脈絡(luò)性的呈現(xiàn),讓觀眾得以深入觀察、檢視、欣賞、理解環(huán)境與該展示物件之間的各種主客觀群聚關(guān)系,成為觀眾學(xué)習(xí)與物件相關(guān)知識的重要途徑與方式。